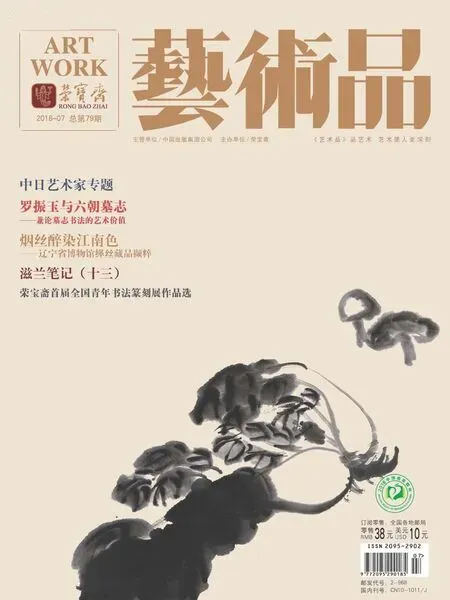清風如可托 終共白云飛—中日兩國間的文化交流以及日本的中國書畫文物收藏
文/馮朝輝
文人情愫,往事悠悠,從青春懵懂到不惑半百,人生十六載的黃金歲月,曾頻繁往來于中日兩國之間,近文從藝,道不盡的故事,說不完的感慨,時常滌蕩著我的胸懷,每每回首北宋政治家、詩人寇準一首描寫《紙鳶》的小詩總是不期而至:
碧落秋方靜,騰空力尚微。
清風如可托,終共白云飛。
紙鳶也即風箏,我時常感到那時的自己好像就是一只紙鳶,骨子里那份對中日兩國間類同傳統文化的不盡熱愛,牢牢地將我栓系,從中國到日本,又從日本到中國,一路托“傳統文化”之風,尋跡飛行。
20世紀90年代我自魯迅美術學院中國畫專業本科畢業后,欲走出國門,開闊視野,攻讀碩士學位,進一步謀求筆墨藝術上的造詣,日本成了我留學之地的不二選擇。當我熟練掌握了日本語,順利完成了學業目標,出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與專注,鑒于日本民間保有中國文物,尤其是書畫類文物量較大的緣故,我的腳步便一時難以離開。
十六年里中日兩國間的文化深深地滋養著我,讀過的書可謂汗牛充棟,過手的中國名家字畫不勝枚舉;十六年里的收藏故事太多太多,打眼刻骨銘心,“撿漏”更像傳奇;十六年里藝術市場的跌宕起伏早已裝在心底……當鄭板橋的《峭壁芝蘭》、吳昌碩的《竹石圖》、齊白石的《酒熟蟹肥》、傅抱石的《高山仰止》、徐悲鴻的《柳鵲》等件件記載、著錄清晰,流傳有序的華夏藝術瑰寶,經我之手回流祖國,帶著歷史的塵風,洗去貧窮的恥辱,讓我不經然地也帶上了一份自豪,畢竟“中國的文化屬于世界,但中國的文化遺產屬于中國”。

吳昌碩 瓜實圖 57cm×103.3cm
一、中日繪畫藝術的互滲
中國和日本隔海相望,地理位置相鄰,盡管近代以來,包括近些年間兩國政治立場相異,地緣爭端不斷,但于民間文化交流而言卻淵遠流長,這種長久交流的直接結果便導致了兩國文化的深度互融,于繪畫上表現得頗具代表性。
中國畫與日本畫兩個分別以國家之名命名的畫種先皆以筆墨等東方文化為基,合而后分,先后各自分別經歷了西方思潮的沖擊,形成了今天這兩個畫種“你中有我,我中融你”,然而又朝向追崇“意象”與“自然之象”兩個完全不同方面發展的局面。
1.日本畫家對中國畫藝術的學習
日本是一個“有著承認更為優越文化心理態度” 的民族,曾經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大陸文化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于是日本便全面學習之。隨著清政府的沒落,相反日本的崛起,日本人發現以自然科學理論為基礎的西方文化更具吸引力,于是他們就義無反顧地“脫亞入歐”,轉向了新的學習目標,與中國文化開始分道揚鑣。
這個轉折點便是日本的明治維新,即19世紀60年代日本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沖擊,國內由上而下進行了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全盤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使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走上工業化發展道路的國家,后逐漸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明治維新是日本近代的開端,也是日本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日本的繪畫藝術也不例外,自此開始轉向,拋棄中國,轉向西方學習。
(1)明治維新前日本繪畫界對中國藝術的師法
據日本史料記載,早在公元7世紀(中國唐朝時期)日本就曾向中國派“遣唐使”學習大唐文化,達19次之多;13—16世紀中國宋元水墨畫成為日本室町時代畫家們的追求目標,出現了以日本畫家雪舟為代表的一批水墨畫家,中國南宋畫家梁楷、牧溪影響了日本的禪宗畫派,如當時日本派遣來中國學習佛法,歸國后被尊為國師的圣一,曾同牧溪一同拜在中國無準禪師門下學法,其歸國前牧溪以所畫觀音、猿、鶴三幅作品相贈,后這三幅作品被日本人視為國寶,現珍藏在日本大德寺中,南宋畫院馬遠的“一角”與夏圭的“半邊”式構圖亦深受當時日本畫界追捧;18世紀(中國清中期)日本出現了以中國文人畫為楷模的南畫運動,并涌現出以日本池大雅、與謝蕪村為代表的南畫領袖,1748年日本翻刻出版中國《芥子園畫傳》;19世紀以后(中國清晚期)隨著中國的沒落,日本的南畫運動隨之衰落,但其遺風尚存,富岡鐵齋成為日本繪畫步入近代后的最后一位文人畫大師。

八大山人 古松圖 182.5cm×49cm

齊白石 酒熟蟹肥68cm×34cm

馮朝輝 松鼠 30cm×50cm 2017年
(2)明治維新后日本繪畫界對中國藝術的師法
近代日本,國家發展方向的調整,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直接作用于藝術,洋畫為日本畫提供了新的美學參照標準,日本畫家們從洋畫中汲取營養,與本民族先前自中國學習、沉積、化合后的繪畫技法、觀念相融合,經過不斷地探索與實踐,進而發展、確立了新的美學認識,并相應地創造出了新的繪畫材料與技法,如選用巖彩、膠等,他們弱化甚至放棄了中國傳統繪畫中“線”與“水墨”兩個基本構成要素,轉以強調對色彩的應用取而代之,為日本畫的變革送來一股新風,完成了日本畫從古典向現代、從舊傳統向新時代的轉變。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清朝末期至民國初年)雖然日本主流思想轉向學習西方文化,但一種文化的轉型并非一代人能完成的,有時需要幾代人,甚至十幾代人,老輩日本學者、文人骨子里遺留下來的對中國文化的喜愛仍然在持續,故而中日間的文化交流并未中斷。1864年日本人安田老山到中國上海師從中國畫家胡公壽習畫,歸國后成為日本畫界泰斗;1893年、1906年、1912年日本畫家岡倉天心奉日本官方之命三次赴華,調查中國古代美術,調查內容主要集中在中國寺廟等古代建筑;1895年日本近代油畫大家中村不折作為隨軍記者來到中國,收集并運走了大批中國文物,歸國后于日本東京成立了“書道博物館”,館內藏有大量中國文物,據推測其規模與質量不遜于中國很多的省級博物館;1900—1914年間日本學者河井荃廬以及長尾甲頻繁往返或久居中國,拜中國海派藝術巨匠吳昌碩為師,習畫制印,并加入中國杭州西泠印社,成為其首界社員,歸國后前者成為日本印學宗師,后者成為日本一代文人領袖,同時他們又致力于吳昌碩、王震書畫藝術在日本的推廣,這一時期來華拜會吳昌碩的還有日本書法家日下部鳴鶴;1910年在獲知中國官府已將敦煌藏經洞所剩文書全部運抵北京后,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教授、講授東洋史(日本稱法,即中國史)的日本中國文化研究專家內藤湖南,奉命到北京調查敦煌文書,翌年寫出《清國派遣教授學術視察報告》,并將所獲資料在日本展出;1913年日本人有賀長雄以中華民國法律顧問的身份居北京7年,在此期間雖無其美術活動記載,但歸國后有賀長雄即撰寫了《東亞美術史綱》;1913—1928年日本南畫名家橋本關雪數次來華,與中國畫家吳昌碩、王震、劉海粟、潘天壽等深度交往,并邀錢瘦鐵赴日本講授中國篆刻;繼橋本關雪來華之后,日本美術史論家長廣敏雄于20世紀30、40年代多次來華,開展對云岡石窟的相關調查,后期值中日兩國戰爭之際,但長廣敏雄的謙卑卻并不讓中國藝術家們排斥,1944年他在北京訪問了很多中國畫家,回國后即寫成了《北京的畫家們》,書中記錄了當時他對北京最有名的大畫家蔣兆和、黃賓虹、陳半丁、齊白石等人的訪問。

趙之謙 逍遙堂 27.5cm×124cm
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后,兩國民間的畫界交流遂中斷。
2.中國畫家同日本繪畫的交流與學習
如前文所言兩國政治經濟狀況的逆轉,造成日本畫家向中國藝術家學習,從積極攝取到慣性前行的前后兩個分階段狀況,反過來也造成了中國畫家學習日本文化、開展文化交流的前后兩個不同階段。中國這兩個階段的分水嶺應當以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劃界,這比日本的明治維新晚了30年。如果說明治維新讓日本畫家們發現了西方藝術的魅力,轉而棄中學西,那么中日甲午戰爭則讓中國畫家,以至中國人認識到了日本的先進與強大,進而由授業轉為向其學習。
(1)以傳教與布道為主的中國學者東渡
古代因為中國的強大,中國學者到日本多以傳教、布道為目的,如唐朝鑒真和尚先后六次東渡日本,弘傳佛法,成為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開山祖師,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傳播;明末清初隱元禪師應邀率30位知名僧俗赴日本,成為日本黃檗宗的開山鼻祖,隱元禪師知識廣博,詩文書法均佳,他為日本帶去了中國書法、印刻、建筑、雕塑、雕版印刷、醫藥學和音樂等作品和書典,日本稱之為“黃檗文化”;1731年中國清代畫家沈銓應日本天皇之聘,偕弟子鄭培、高鈞等東渡日本傳藝,深受日本人推崇,從習畫者頗多,日本江戶時代長崎畫派即在其影響下形成。
清末至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中國金石文字家、書法家楊守敬曾出使日本,期間與日本漢學書法家論碑,被稱為“楊守敬旋風”;中國畫家蒲華、陳曼壽、戴以恒、顧沄、胡鐵梅、羅雪谷、王冶梅、葉松石皆曾旅日鬻畫,這一時期中日雙方畫界間的交流是分散的,且仍以中國畫家的藝術“輸出”為主。
(2)以交流、學習為主的中國畫家東渡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一向自以為老大的中華泱泱大國卻敗在鄰家區區彈丸島國手上,并接受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讓中國的有識之士自省,于是康有為等人效仿日本的明治維新,提出“維新”主張,同時奏請皇帝變法,但以失敗告終。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可它讓國人警醒,中國并不強大,必須通過走出國門去學習,以求變法圖強。在大批中國外派留學生當中,東渡赴日本的人數絲毫不遜于赴西方國家的人數,這其中既包括諸多政治家,也包括了許多文人、學者和畫家。
至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前這一時期,中國畫家到日本雙方間的交流已由先前的以中方文化輸出為主,漸漸轉變為相互間的學習和借鑒。上海地區先是王震(畫家,同時是日清汽船會社中方經理),繼而是錢瘦鐵(旅日畫家、篆刻家),北京地區以陳師曾(畫家,曾在日本留學8年)為主,頻繁往返于中日間,從事書畫交流活動,積極參與推動成立畫會(社),有規模、有組織地推介中國藝術家以及其作品到日本,與日本藝術家作品一同展出,從而也令吳昌碩、齊白石雖未出國門,其作品卻風靡東瀛。這期間陳師曾翻譯了日本大村西崖《文人畫之復興》,且合并自撰成《中國文人畫之研究》,同時潘天壽參照日本中村不折、小鹿青云的《支那繪畫史》譯著了《中國繪畫史》,代表著中日兩國間的藝術交流由實踐走向了理論,并由相互間的對等交流開始向以日本方的文化輸出為主轉變。

馮朝輝 煙林清曠 65cm×33.5cm 2017 年
1906年高劍父赴日本東京帝國美術學校學畫,第二年又帶其弟高奇峰再赴日本學畫,吸收日本畫風后在中國形成了“嶺南畫派”;1907年陳樹人赴日本,1909年入京都市立美術工藝學校繪畫科學習;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中國考古學家羅振玉攜眷逃亡日本京都,1919年回國,在日期間漢學著述頗豐,并成為當時旅居日本的漢文化、文物專家;1908年何香凝到東京本鄉女子美術學校學習;1917年徐悲鴻得友人贊助赴日本學習;1917年張大千赴日本京都公平學校學習染織與繪畫;1916年汪亞塵赴日本,1917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學習;1918年朱屺瞻赴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學習繪畫;1919年陳之佛赴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學習圖案設計;1921年豐子愷赴日本游學,晚年翻譯出日本古典文化巨著《源氏物語》;1929年方人定赴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學習繪畫;1932年黎雄才赴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學習繪畫;1932年傅抱石赴日學習,專攻美術史論,歸國后翻譯了日本梅澤和軒的《王摩詰》、金原省吾的《唐宋之繪畫》,并參考日本人著作,編著了《中國繪畫理論》《中國美術年表》等。

吳昌碩 宜齡多子 116.5cm×54cm
抗日戰爭爆發,中國畫家們到日本留學交流中斷。
日本近代百年藝術史實質上是對西方文化消化與吸收的歷史,自上而下意識形態的全面轉變,已經讓曾經取法中國畫的日本畫與西畫完美地融合,與中國畫面貌漸行漸遠,但其骨子里最初建立起來的中國審美觀在畫面中依然存在,比如日本畫的畫面構圖審美還是中國式的,對雅致、柔和色彩的崇尚仍印有深刻的中國烙印。同時近代中國畫家通過對日本畫的學習與吸收,也在中國畫的發展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嶺南畫派自不必說,學術界一直有聲音言其照抄日本畫風;王震的人物畫風受到日本禪宗畫的影響;豐子愷的漫畫、汪亞塵的花鳥畫、陳樹人、傅抱石的山水畫中均明顯帶有日本畫的影子,即作品中大多弱化了對“線”和“筆墨”的運用,強化了色彩效果,畫面視覺感受趨于干凈、柔和。
展望未來,傳統中國畫與日本畫勢必沿著各自的方向繼續發展下去,二者的趨同性會越來越少,傳統中國畫將以“神”“意”作為其追求目標,從而達到氣韻生動的境界,而日本畫仿效西畫,早已貼近了自然。二者不必再趨同,但依然可以相互借鑒。
二、日本的中國書畫藝術品收藏
正是因為有著在這種包含大量漢民族傳統元素的文化,老輩日本人普遍對中國文化有著較為深刻的理解與喜愛,對中國藝術品收藏十分熱衷,很多中國知名畫家在日本同樣家喻戶曉,如宋代牧溪、明代的王鐸、張瑞圖,清代的朱耷、沈銓,近現代的吳昌碩、齊白石、傅抱石,當代的范曾,等等,對其作品日本民眾也是趨之若鶩,珍視有佳的,只不過在20世紀之前,日本藏的中國畫還是相當空缺的,僅是一些民間包括宗教界人士交往攜帶過去而已,一些充滿禪意如南宋馬遠、夏圭、牧溪等的作品,受到喜愛,并被日本寺廟和幕府等權貴階層收藏。

馮朝輝 阿壩所見 30cm×50cm 2017年
到20世紀初,隨著兩國政治、經濟形勢的改變,日本藏中國畫空缺的狀況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時中國正經歷著帝國主義入侵,辛亥革命武裝起義,清朝封建統治土崩瓦解,國內各路軍閥混戰,直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這段時間相對于日本國內則是大正時期(1912—1926),在經歷明治維新后,國家、國民正逐步走向富強、富裕,一些深研,或是喜愛中國傳統文化的實業家、銀行家、政治家、文物經營商以及收藏愛好者,其中比較有名氣的收藏家有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山本悌二郎、原田悟朗、住友寬一、黑川幸七、藤井善助、橋本末吉、小川為次郎、菊池惺堂、須磨彌吉郎、林宗毅、矢代幸雄、岡村商石、池部政次等,面對中國文物大量外流的現狀,私機借助天時、地利和頻繁兩國民間往來,憑借其對中國文化全面了解與掌握的優勢,又請當時的漢學研究專家,如內藤湖南、長尾雨山以及旅居日本的羅振玉等充當顧問與中介,站在中國人對中國美術史評價的角度上,大肆收購不僅止于滿含禪意畫作的大范圍中國文物,一時間興起了中國書畫搜集、研究的熱潮,這在日本輸入史上是空前絕后的,也是令人嘆為觀止的。
現在我們回顧那段令無數中國人為之心痛的歷史,我們說日本人當時是圖謀不軌,乘人之危,以至后來發展成侵華戰爭期間對中國文物肆意的偷盜與掠奪,日本人則說是搶救亞洲文物,面對中國文物流向海外求售的狀況不能坐視不管,比如內藤湖南就曾說“中國在那樣的狀態下,貴重文物接二連三流出海外,我們得設法將它們保存在同屬東亞的文化圈,并且是很久以前就有著深厚關系的日本才是”。這種狀況在侵華戰爭爆發前,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破四舊”期間是存在的,如20世紀初日本紡織業巨頭阿部房次郎在當時中國舉辦的“天津賑災展”上就收購了不少,后來其在所著《爽籟館欣賞》(第一輯)序言中寫到“東亞古美術中又以中國美術的成就最高。這樣的中國美術品在兵亂中散佚毀壞,著實令人難以忍受”。山本修之助撰寫的收藏家《山本悌二郎先生》一書中記戰前“其在上海書畫商店打聽到數包貨物都是打算運往美國的古畫時,便在未查看內容的情況下將之全數買下”。日本收藏家矢代幸雄在倫敦演講中國美術史時說到“美術是全人類的現象,其本質具有普世性”。收藏家林宗毅在其編輯出版的《定靜堂藏中國明清書畫圖錄》跋文中說到收藏的目的“防止書畫之散佚損毀,固守傳統念愿之發露也”等,中日雙方評價不一,各自站在本國的立場上講話也是必然的,但如果說是日本人是以投資增值為目的,筆者首先不完全贊成,因為這些流往日本的中國書畫文物,尤其是一些古代重量級的,如今絕大多數都保存在日本公、私博物館里,被日本國列為“重要文化財”,予以保護,日本的公、私博物館也成為了我們中國人現今去日本旅游、考察、參觀的重要到訪地。而一些我國近代名家,如吳昌碩、王震、張大千、齊白石、王雪濤等人的作品,自然都是通過購買的形式流通到日本的,完全是出于對中國文化、中國書畫的喜愛,因為這些畫作在當時看來尚屬當代作品,還算不上文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曾將其作為銷售創匯的來源之一,于國有文物商店或中國的“廣交會”上公開銷售,張大千在其年譜中曾記載其觀日本藏家原田觀峰收藏,多有中國海關封蠟、火漆、鈐印,時間推算應為中國“廣交會”所購, 1967年5月(“文革”期間)中國公布了《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一部分囤于國內各地,一部分則以換取外匯為目的,通過廣交會出售”。在此,我們說文化暫不評政治與歷史,透過這些珍貴的文物,我們感受的是兩國人民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對漢民族文化、文物的無限喜愛與珍視。
由此亦可見,日本文物收藏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廣泛的民間性,文物收藏公、私并存,私人藏家、博物館為數眾多,據不完全統計有大數百家之多,這在世界范圍內應當也是一大特色,藏品存量之巨、質量之高(有的即便拿回中國也是孤品)、跨越年代之久,絕對可以與國有博物館一爭高下。國民對文化的喜愛,對文物的欣賞和保護意識是普遍的,如在日式的住宅里一般都設有專門掛畫的區域,下邊擺放文玩,一年四季定期更換。公、私博物館間相互也并不封閉,彼此交流得比較多,私人藏家或博物館的珍貴藏品常常會被借展或寄藏于國有博物館中,短期地參加一次展覽活動,為期一兩個月,長期的也可以幾年。借展或寄藏結束后,仍歸其原主人,原主人有權決定這件文物的去留,包括予以買賣等商業行為。日本公、私博物館文物收藏間的這種互補性,不僅豐富了藏品內容,傳播了文化,也極大地激發了民眾的收藏熱情,推動了民間文物收藏業的繁榮。

馮朝輝 仁者樂山 30cm×50cm 2017年
日本書畫收藏的另一大特點是榮譽、責任與保護意識,當藏家的藏品質量和數量達到一定規模后(有時需要一代人,有時是幾代人),他們大都愿將其捐贈或象征性地收取一定資金出售給國有博物館,或是由家族企業出資興建私人博物館收藏,做進一步的出書、展覽、整理、研究、保護與文化傳播,如上野理一、須磨彌吉郎的收藏后捐贈給了京都博物館,阿部房次郎的收藏后捐贈給了大阪市立美術館,成為該館的核心收藏,池部政次的收藏后捐贈給了早稻田大學的會津八一紀念博物館;國有博物館優先出資購買的,如岡村商石的大部分收藏由大阪市立美術館購得;收藏在家族企業或個人出資興建的私有博物館的更多,如山本悌二郎的收藏如今保存在澄懷堂美術館,并出版有《澄懷堂書畫目錄》,黑川幸七的收藏如今保存在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矢代幸雄的收藏如今保存在奈良大和文華館,原田觀峰的收藏如今保存在東近江市的信樂觀峰館,橋本末吉的收藏如今寄存在東京的松濤美術館,林宗毅的收藏則分為幾處保存,一部分捐贈給了京都博物館,一部分捐贈給了“臺北故宮博物院”,大部分則保存在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等等。
從某種意義上講日本這種文物管理機制,對于保護人類文化遺產,促進文化研究與交流,包括日本本國的,也包括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可以說是一個貢獻。為此日本也成為當下中國經濟繁榮、藝術品市場一定程度放開后,回流中國書畫類文物最多、也是最為集中的貨源地之一。
文化演進至今,現在日本的新生代已經徹底西化,當下日本人對中國文物收藏顯然已經沒有多大的興趣,所以中國人去“掏”日本人就“賣”,他們寧可去花上億美元購買西方油畫大師凡高的《向日葵》,也不會再為購買一件中國文物不擇手段,或是在海外的拍賣行上用錢與中國人拼爭得“你死我活”,除非其以拿到中國拍賣,投資增值賺取利潤為前提,即便如此也是寥寥無幾,只有那些早年不管通過什么手段流傳到日本的,如今已靜靜地存放在日本公、私博物館中的中國文物,還在向這個民族昭示著他們民族的文化淵源,訴說著他們祖輩的文化審美,也傳播著中華文化。
三、中國書畫藝術學習感悟
清代畫家范璣有言:“學畫須得鑒古之法。鑒古不明,猶如行遠而不識道路之東西,鮮有不錯者。”當年從國內藝術高校中國畫專業本科畢業的我,若說對此藝術認識有著多么深刻的理解,確實不敢言,但無心插柳,16年的海外中國書畫文物鑒定歷程,讓我的經歷恰好貼合了這一藝術成長規律,走上了一條和大多數藝術工作者成長所不同的道路,中國畫收藏、鑒定與中國畫創作同時成為了我當下所從事和研究的專業領域,兩個專業相輔相承,相互滋養,相得益彰。

黃賓虹 山靜日長 150cm×46cm

馮朝輝 仙草 30cm×50cm 2017年
首先書畫鑒定滋養了我的藝術創作,其所帶給我的“師古營養”是巨大的,它不是十幾幅、幾十幅名畫臨摹所能比擬的,常年累月的真、假、優、劣辨識,日日的知識浸潤、沖擊、洗禮,每一位名家的不同畫風、筆性、設色特點,甚至同一位畫家不同時期的風格演變都要了然于心,試于筆端,這對畫者認知上的錘煉作用是巨大的,對作品格調的提升作用也是顯著的。
作品是一個人十幾年、幾十年的文化沉積、精神素養和藝術品性的集中體現,書畫鑒定開闊了我的視野,讓我更為深刻地理解了中國畫的傳統筆墨精神、個性風格和師承關系,從藝術的本源上將繪畫、鑒賞、詮次、批評有機地聯系起來,在繼承中求發展,一路沿傳統文脈走行,反映在我的繪畫作品中,由金石畫風而生發,講法畫面整體布局,骨法用筆,意蘊淡遠,筆墨簡練,但不想簡單,面對浮躁、功利、迅捷、多變的當下社會,力圖于作品中展現出寧靜、空靈,參以禪意的精神氣質與追求,努力為自己也為觀者搭建一座可以休憩與深呼吸的心靈家園。
其次中國畫創作加深了我對中國書畫鑒定領域知識的理解與掌握,書畫鑒定不是純理論的學科,它是理論與實踐并重,甚至偏向于實踐更多一些的學科,一方面是鑒定者自身的筆墨實踐,即要能書善畫,它可以讓我們對筆墨的理解入木三分;另一方面是藝術品市場實踐,它不但可以讓我們知其真,知其假,更可以知其何以真,知其何以假。伴隨著藝術品市場的興起與繁榮,人們越發地認識到中國書畫鑒定市場實踐環節于書畫鑒定專業成長中的重要意義,同時市場也呼喚著更多鑒定專業知識人才的出現,然而客觀成長條件的限制,一是大家接觸真跡的機會太少,二是鑒定真偽難以形成責任意識,如博物館里的東西大都不需要鑒定,需要的是研究;藝術品拍賣市場中的鑒定又需要個人較大的財力支持,并非人人具備條件,所以無壓力、無責任之下的學習,人才是難以成長的,從而造成了我國目前鑒定理論與實踐兼而能之的人才缺乏的局面,同時這也是當下國內高校這一專業的教育現狀。
我的書畫鑒定專業即沿著理論到實踐再到理論的發生發展過程走來,國內的本科學習為中國畫專業,多年旅居日本的歲月,客觀上優厚的條件(中國藝術品市場崛起,中國名家書畫在日本民間的保有量大),攻取碩士學位的同時,對中國書畫鑒定進行了尤為深入且廣泛的實踐,回流了大量的中國名家書畫作品。
對利益的追求無止境,只有對知識文化的傳播才可以放大人生。2013年應國家的召喚我自日本歸國,任教于魯迅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講授傳統中國畫和中國書畫鑒定兩門課程,并招收傳統中國畫研究與實踐方向研究生。成為一名教育工作者,開展積極的藝術創作與學術研究始終是我的職業夢想,校內外教學和高校、藝術研究機構間學術交流的需要,結合自身特殊的成長經歷,近幾年我將自己于海外中國畫鑒定、藝術創作領域的認知進行了全面、深入地梳理,撰寫了大量的理論研究文章,5年來已有近五十余萬字發表,其中十余萬字發表于全國核心期刊、專業學術文集上,并受聘擔任遼寧省可移動文物普查書畫類專家,多次受邀參加國內專業研究機構學術會議,參與國家重點藝術項目等研究工作,參編史上名家畫集出版,開展學術講座、交流等。
喜愛民族傳統文化,回報社會各界,通過教學、著述無償地將我這十幾年于海外學習研究、書畫鑒定回流、中國畫創作中的所知、所思、所悟、所得傳播出去,讓更多的繼學者能夠站在我的肩上實現人生理想,是我回國任教的唯一目的。
幾年來,從行業到專業,從行家到專家,從教學到教研,從實踐到理論,我深感話語權多了、重了,但肩負的責任也更大了,時不我待,未來要學、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不問所得,但求有益”是我人生一以貫之的基調,因為奉獻與傳播總是使我充實并給予我快樂。
謹以此文祝賀《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愿兩國人民的友誼萬古長青。
(本文作者為魯迅美術學院副教授、鑒藏家)

八大山人 蘭蕙圖 32cm×34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