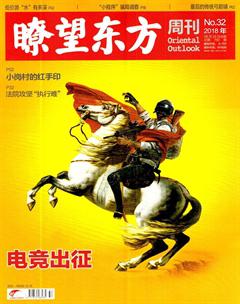泮池的興與廢
在古人看來,這口塘之于文廟的風(fēng)水至關(guān)重要
站在歷史長河中看事物,就像看一個又一個的故事,或有頭有尾,或有始無終。考古發(fā)掘工作,也就是講述一個地方、一個地點(diǎn)興廢沿革的故事。
這個發(fā)掘地點(diǎn),是明清金華府文廟正前方的泮池所在.距離金華府衙以西約150米。府署衙門占據(jù)金華子城相對中心的位置,子城本來是唐代以前的金華城,五代吳越國王錢槿在子城外加筑了一圈城墻,形成內(nèi)、外城的結(jié)構(gòu),外城稱“羅城”,內(nèi)城便是“子城”。
明朝人開鑿泮池。大概發(fā)生在明洪武年間或稍晚。據(jù)說,宋代的文廟也在附近。只是規(guī)模不及明清,可能還沒有泮池,更不像明清文廟那么制度化,全國各地套用一張“藍(lán)圖”,無論發(fā)不發(fā)掘,我們都能把金華文廟的平面布局猜測到八九不離十。
掘地三尺的明朝人,肯定已經(jīng)挖穿了六朝時(shí)期的地層、根據(jù)我們的考古發(fā)掘,泮池地下出土有若干兩晉南朝的磚瓦和瓷片。所以,我常說,城市考古除了“平面找布局”,更要“縱向找沿革”——我們腳下這一塊土地的歷史沿革。這說明,文廟的地下正是六朝舊郡的遺址。不過,明朝人恐怕不會關(guān)心這些,他們只是要在大成殿的正前方,挖掘一口半月形的池塘。
在古人看來,這口池塘之于文廟的風(fēng)水至關(guān)重要。江南地區(qū)的明代墓地,前端通常也開鑿有半月形池塘,比如大畫家吳昌碩在老家安吉鄣昊的明代祖墳、今日溫州的椅子墳都有類似的“風(fēng)水池”。據(jù)說天地之間的“生氣”“乘風(fēng)而散,界水而止”等,會在遇水的地方聚集起來。文廟的泮池,造型既與墓地類同,功能亦當(dāng)近似。基地風(fēng)水只關(guān)乎一族一姓的命運(yùn),而文廟之于城市風(fēng)水至關(guān)重要,左右一地的文運(yùn)興衰。只要條件允許,明朝人一定會把文廟安排在城市的東南。金華子城,正是城內(nèi)東南區(qū)域一塊規(guī)整的臺地。
在考古工作者看來,這塊臺地的形成和拓建過程,是認(rèn)識金華城市早期歷史的重點(diǎn)當(dāng)然,古人一定不會有類似的問題意識,他們更關(guān)心衙署和文廟的風(fēng)水,保佑本人升官發(fā)財(cái),冀望本土的進(jìn)士老爺,多多益善。
1905年,滿清廢除科舉,文廟喪失了象征的或現(xiàn)實(shí)的功能。民國時(shí)期,文廟改建為新式的金華中學(xué)。我們在泮池遺址以東發(fā)現(xiàn)的校舍遺址,以巨大的條石作臺基。不知何故,新式校舍偏離了泮池所在的中軸線,疊壓在東側(cè)的另一條軸線上。
廟學(xué)合一的“文廟學(xué)宮”,既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也是官辦的學(xué)校,通常設(shè)置“左學(xué)右廟”兩條軸線:廟的主體是大成殿和殿前的東西兩廡,供奉孔子和先賢先儒;學(xué)的主體是明倫堂或講舍,為學(xué)官講學(xué)和生活之所。民國校舍的地基下,疊壓著三個不同時(shí)期的“學(xué)宮”道路年代最晚的道路位于最上層,路面最寬,以塊石鋪設(shè),甚至砸碎學(xué)宮中的碑刻,用以鋪路。有一通殘碑可辨“乾隆五年”等字;另一通的碑額上鐫刻有“重修明倫堂碑記”字樣。
根據(jù)地層疊壓的早晚關(guān)系判斷,“毀碑鋪路”發(fā)生在上世紀(jì)二十年代大規(guī)模建設(shè)中學(xué)校舍前夕,即在科舉制度廢除后不久。何謂“斯文掃地”?這就是。
1975年拆毀大成殿,撬除泮池石板,并填平了這口半月形的池塘。文廟的地面建筑,至此蕩然。
我們重新挖掘開來的泮池,里頭填滿了垃圾,煤渣、磚塊、玻璃瓶,應(yīng)有盡有。畢竟距今不遠(yuǎn),見證人尚多,在我工作期間,他們跑來現(xiàn)場講故事,描述拆毀泮池的場景,多與遺跡現(xiàn)象吻合。比如,泮池的欄板拆卸后,做了教學(xué)樓地下的排水溝。
如此掩埋四十年,忽如一夜春風(fēng)來。如今,“國學(xué)”復(fù)興,弘揚(yáng)中華傳統(tǒng)文化正當(dāng)其時(shí),大家認(rèn)為,再也不會有比重建文廟更具有象征意義的工程了。因此,我奉命前來工作,考古發(fā)掘揭示的泮池遺跡,據(jù)說將會成為日后重建文廟的依據(jù)。假以時(shí)日,全新的泮池必將重新崛起于新文廟前端的這個地點(diǎn)
這就是城市東南區(qū)域、方圓兩三千平方米的地點(diǎn),最近六七百年來發(fā)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