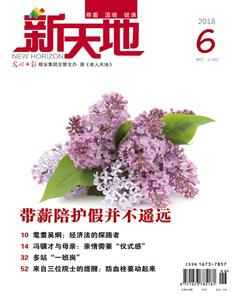多站“一班崗”
莊電一
“站好最后一班崗!”人們常常用這句話來形容在退伍、退役、退休或調離時仍然不忘初心、毫不懈怠、有始有終地履行職責、堅守崗位的表現。在現實生活中,也確實有許多人不計個人得失,不折不扣地站好了最后一班崗,表現出良好的敬業精神和令人敬佩的精神境界。
對于我來說,雖然不敢說“站好了最后一班崗”,但卻可以說“多”站了“一班崗”:因為在退休之后我仍然在一段時間里堅守在工作崗位上,我沒有計較個人得失,沒有耽誤正常工作,沒有妨礙新人,也沒有給他人和單位“添亂”。
只為守候一方熱土
2016年,是我在記者站工作的最后一年,實際在職時間只有5個月,但我依然故我,一如既往地投入工作,如饑似渴地捕捉新聞線索。年初,我仍然像往年一樣參加了“新春走基層”采訪活動,深入到位于毛烏素沙漠邊緣的鹽池縣大水坑鎮新泉井村等地與當地農民“面對面”,一口氣寫出了《貧困村里談脫貧——訪寧夏鹽池縣大水坑鎮新泉井村》《沙邊子村“龍頭”龍治普的精準扶貧》《一場值得期待的演出》等文。在往返路上,我留心觀察路旁的景物,醞釀、構思了在發表后引起廣泛好評并獲獎的特寫《銀川平原鳥巢多》。聽說一位民間收藏家投入上億元資金收藏民俗文物,我驅車400公里趕到位于六盤山下的隆德縣進行實地采訪,寫出長篇報道《民間收藏之路,如何越走越寬》。那次,我還在縣城散步時發現了一個新聞素材,隨后寫出通訊《隆德縣有個古柳公園》。
一轉眼,就到了5月,我按通知回報社開會。會議期間,人事部門的同志找到我,讓我辦理退休手續。對此,我毫無精神準備:怎么,我要退休了?我的職業生涯就此結束了?辦完手續,我若有所失。但因為沒有人接班,我回到駐地仍自覺自愿地堅守在工作崗位上。
再訪黎明村看脫貧
從北京回到銀川,我感到要做的事、要采寫的題材都有很多,而最讓我念念不忘的是對黎明村的采訪。自1998年以來,我已經對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荒村進行過9次采訪、發表了幾萬字的報道,所寫報道在全國曾引起廣泛關注,但我感到還缺少一篇“收官之作”,十訪黎明村變成了我最想完成的任務。5月30日,是我職業生涯的倒數第二天,我在這一天踏上了黎明村的大地,用兩天時間完成了這個期待已久的采訪。
可是,我會不會在職業生涯結束時放“啞炮”、留下遺憾?老實說,在動身之前,我并沒有信心。我跟人開玩笑:“我這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自己給自己出難題啊!”我坐在采訪車里自嘲:年屆花甲了,這是何苦啊!
好在,我的這次采訪頗有收獲,一篇題為《物換星移幾度秋——十訪曾被風沙逼得四分五裂的黎明村》的長篇通訊,非常破例地、占據了四分之三版、以5000多字的篇幅、配發3幅圖片和“記者手記”與讀者見面,且很快被一些網站轉載、被微信轉發。至此,我原來那顆懸著的心才放下了。更讓我沒有想到的是,這篇通訊,還獲得了光明日報月評好稿一等獎。
尤其讓我感動的是,經過協商,報社不僅與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在銀川為我聯合舉辦了新聞作品研討會,而且派李春林副總編輯和周立文、鄧海云、馬興宇3位部主任及高平站長、編輯彭景輝到會,還特意將這篇超長的通訊安排在研討會的前一天刊出。這張被帶到研討會現場的報紙,引起與會者的關注。
退休手續辦了,作品研討會也開完了,我完全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但我并沒有這樣做,因為新記者還沒有到任呢,我還負有推薦、協助考察等任務。對新聞采訪,我也沒有松懈。
筆耕人生馬不停蹄
2016年8月,我又接到報社通知到北京參加了年中工作會議,一切都好像和在職時一樣。記得9月下旬,報社在幾天之內向我接連布置了中宣部和報社的5個采訪任務。我半開玩笑地提醒記者部的同志:我已經退休了啊,這么多采訪任務,讓我如何在這么短的時間完成啊?但我爭分奪秒、連夜趕稿,在規定時間內保質保量地交了稿。期間,中宣部組織“重走長征路”大型采訪活動,報社在征求我的意見后也報了我的名。在完成各項工作的同時,我還協調、配合報社完成了對新記者的考察。
2016年9月27日,新記者到任。我又幫助新記者熟悉情況、配合新記者做下一年的報紙發行工作。在“重走長征路”的采訪團即將到寧夏之前,我參加了采訪活動并寫出多篇報道。那些天,我除了完成規定的采訪任務之外,還“順手牽羊”采訪了兩篇同樣主題的通訊,也算是“超額”完成了采訪任務。此后,我又寫了《清平樂·六盤山究竟幾易其稿》,刊登在光明日報專刊上。
當年11月,我以自治區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政協調研活動,發現北方民族大學在大學生自主創業方面很有成績,就“一身二用”,又當了一回“本報記者”相關的新聞報道也以較長篇幅出現在光明日報的版面上。為了讓新記者“露臉”,我在沒有告知的情況下“擅自”在自己獨自采訪的兩篇稿件中加上了新記者的名字。
這一年,我幾乎沒有停止采訪的腳步,所以在各類報刊上發表的稿件仍有100多篇,其中大部分還是我退休后采寫的。這一年,我在職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5個月,但自治區和銀川市還是對我進行了表彰,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還授予我年度優秀新聞工作者稱號,為我的職業生涯劃上了最后一個“符號”。
2017年,我徹底告別了職業生涯,但我仍然在包括光明日報在內的全國各類報刊發稿40余篇。2018年前兩個月,我又發出了十余篇稿件,雖然沒有“站崗”的責任了,但我還不想、也無法停下手中的筆。一些讀者的鼓勵、一些刊物的約稿、一種難以擺脫的職業習慣、一個無法割舍的志趣愛好,驅使我一次次拿起筆,也讓我一次次在報刊上與讀者見面。
(責編: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