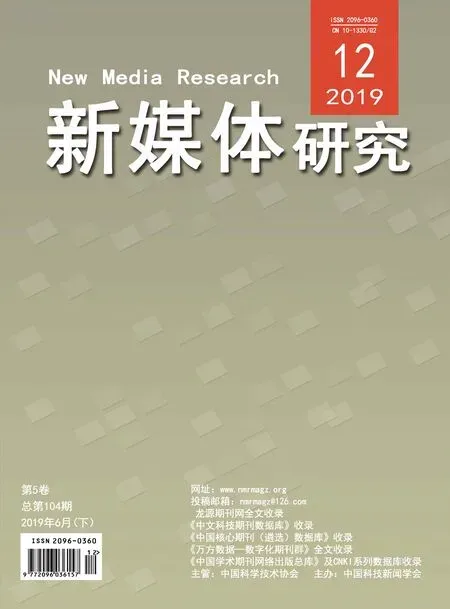消費主義視域下新媒體藝術的現狀解讀
楊瑞銘
摘 要 網絡游戲伴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發展而逐漸興起,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呈現出了消費主義注重享樂、符號化消費的特征。借助消費主義的視角解讀了網絡游戲《絕地求生:大逃殺》的風行是因為其滿足了玩家的娛樂欲望、張揚了消費觀念,而大眾傳媒也在游戲風行的過程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消費主義的影響下該游戲也出現了游戲者倫理失當、精神迷失、網絡沉迷以及游戲內容媚俗的問題,在文化繁榮發展的今天,需要對作為新媒體藝術的電子網絡游戲加強合理的制約與引導,為大眾提煉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娛樂產品。
關鍵詞 消費主義;網絡游戲;新媒體藝術;文化消費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8)12-0133-03
網絡數字游戲伴隨著計算機的產生而出現,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而逐漸興起,其作為一種新媒體藝術形式,集合了商業性與文化性于一體,已成為一項大眾休閑娛樂消費的重要內容,并引發社會文化領域的新變革。據市場分析公司SuperData Research報告顯示,2017年游戲以及游戲相關內容將在全球創造1 046億美元的收入,到2020年預計全球游戲和互動媒體收入將達到1 688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1 340億)[1],電子游戲已經成為當之無愧的文化產業“巨頭”。
網絡游戲在內容上不斷豐富,其所蘊含的信息涉及社會領域的方方面面,伴隨著現代數字化技術和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網絡游戲逐步被大眾熟悉和接受,游戲中的劇情、畫面、場景、人物等都能體現出一種文化特質,甚至引領起一股風潮。但網絡游戲在營銷和傳播過程中,伴隨著市場化的固有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卷入消費社會的浪潮中去,出現了一些問題。本文就以時下正熱的網絡游戲《絕地求生:大逃殺》為例,分析消費主義視域下的網絡游戲的發展現狀和風行的原因。
1 消費社會與消費主義的表現
1.1 消費社會與消費主義
“消費”是現代商品社會的一個概念,其實質是利用、消耗自然資源和人工物質以滿足需要的過程。馬克思認為,消費作為一種需要,同時也是生產活動的一個內在要素,人們通過生產和消費某種對象來實現自身、完成自我再生產,而生產則是在其中起到支配作用的要素。但是隨著19世紀資本主義和工業生產的飛速發展,生產與消費的矛盾開始凸顯,消費不足日益成為制約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因素,經濟學家開始重視消費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到了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物質條件前所未有的豐盛,消費社會最終形成,“消費”已經融入為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并成為了一種價值體系和生活方式。
消費主義是隨著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不斷發展,產品日益豐富,從生產社會進入消費社會而不斷興起和發展的,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它的消費目的不是滿足實際需要,而是滿足不斷被生產出的刺激欲望。換言之,人們消費的不是商品和服務的使用價值,而是符號的象征意義[2]。在消費主義的影響和支配下,消費成為了一種激發人們幻想的滿足,一種和我們具體、實在的自我相離異的幻想行為[3],人們不再把消費作為滿足日常生活的必要環節,而是把消費看作是生活的根本
意義。
1.2 消費主義的表現
消費主義的核心是消費至上的價值理念,其特征為:
1)消費主義著重對產品的符號價值和象征意義的消費,即“符號消費”。
2)消費者消費的是快樂體驗和享樂價值,且這種體驗具有短暫性、享受性和易變性。
3)無盡的消費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對理性、終極價值和生命本質的精神追求,導致人性的異化,帶來信仰和道德危機。
2 《絕地逃生:大逃殺》中的消費主義表征
消費主義介入到網絡游戲之中,作用于網絡游戲的傳播與風行,并同大眾傳媒一道對消費文化的建構起到了助推作用,與此同時,網絡游戲作為消費主義的文化載體,其本身也呈現出明顯的消費主義表征。
2.1 視聽狂歡和“媚俗化”的迎合
在網絡時代,感官刺激激發了人們強烈的消費欲望,欲望的増長也使得游戲玩家愈發追求視覺刺激的強烈沖擊力和快感,游戲廠商將狂歡和欲望的釋放作為游戲的營銷手段,是一種有意識引導下的人類潛意識中的無意行為。在游戲中,玩家從統治的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從而獲取一種約翰·費斯克所言的“自由的、能動的、游牧式的”的主體快感。《絕地求生:大逃殺》中新游戲引擎的使用使得游戲世界十分廣闊,擁有高山、平地、叢林、谷地、樹林、草原、河流、橋梁等眾多元素,擬真度高;游戲中爬行、跳躍等動作豐富,人機互動流暢;擊殺、爆炸、飆車等環節緊張刺激,在百人混戰中取得生存的規則設定也增強了玩家的浸入感,這樣的視聽體驗都使游戲玩家達到“迷醉”的狀態,玩家的欲望得到了徹底釋放;當下趨于完善的電競和直播產業鏈為《絕地求生》的風行促成了口碑的推廣,主播與粉絲的互動最終形成了一種共同的“想象空間”。精致的游戲畫面也使游戲對電腦硬件有了更高的要求,為了更加流暢的運行游戲,玩家不得不升級自己的游戲顯卡、內存、顯示器等配件,市場上一批所謂的“吃雞本”銷售火熱。對于游戲視聽刺激追求的影響從虛擬的消費領域延伸到實體經濟領域,這不僅是玩家的狂歡,更是一場整個消費市場的“吃雞”盛宴。
隨著網絡空間的發展和擴大,大眾話語權得到解放,在消費主義市場的邏輯支配下,網絡游戲作為一種文化藝術產品不斷屈服于物質利益,既關注了玩家的基本娛樂消費的需求,更迎合了玩家進行炫耀性消費的需求,通過分析大眾審美觀念與消費需求的世俗化,調整游戲作品的設計策略。在《絕地求生:大逃殺》游戲中,玩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而對自己的游戲人物進行裝扮,玩家可以利用“游戲積分”開啟游戲寶箱獲得服裝和飾品,但是這樣所獲得的飾品是隨機的,如果玩家想對自己的游戲人物進行個性化的驚艷裝扮,必須通過延長自己的游戲時間或者花費大約17元人民幣購買開箱鑰匙。無論玩家的消費水平如何,網絡游戲廠商都不斷引入這種虛擬消費品以滿足玩家的炫耀心理,反映了網絡游戲對玩家媚俗性需求的迎合。
2.2 網絡沉迷與娛樂的異化
游戲空間是一個巨大的虛擬世界,玩家可以選擇其他一種與現實社會完全不同的虛擬生活方式,而正是這種虛擬性給予了玩家創造另一個自我的機會。玩家在網絡游戲這樣的平臺中體會到愉悅和滿足,游戲中結局的未知與機會的無限吸引著玩家不斷游戲,這樣無節制的消遣甚至成為了玩家生活的目的和依戀的對象。“成癮性”消費是消費主義的特征之一,網絡成癮是網絡消費主義發展對于個體造成重要表現和必然結果。但是與一般的消費不同,網絡游戲的沉迷會對玩家和社會產生更為嚴重的影響。作為一款國外游戲廠商制作并通過國際游戲平臺Steam發售的游戲,國內相關部門對《絕地求生:大逃殺》的監管尚為空白,缺少防沉迷的有效機制,對未成年玩家的限制也相當有限,這就使得玩家在游戲中毫無限制的投入大量時間。這樣過度網絡消費擠占了玩家的學習、生活及其他休閑活動,并干擾了對于社會的認知和判斷,對個人的成長產生不良的影響。
由于《絕地求生:大逃殺》的獨特規則設定,在每一局20多分鐘的游戲時間里,玩家需要時刻精神緊張,接受刺激感官的轟炸,由“吃雞”而癲狂,因未能“吃雞”而沮喪。網絡游戲原本作為一種娛樂手段而滿足玩家的心理需求,但在消費主義的建構下逐漸背離了娛樂消費者的初衷,網絡游戲反而開始對玩家進行了控制,玩家成為了游戲的奴隸。
2.3 身份建構與精神的迷失
與傳統的藝術形式相比,玩家可以在網絡游戲中建構自己的人物形象與身份,從性別、種族、容貌等外在條件到學識、心情等內在品質,都可以通過社會互動或者形象建模加以建構。當玩家建立一個游戲人物時,其人物形象往往承載著玩家對自己的某種寄托,隨著網絡消費主義文化的發展,人們對于自身體態的期望也越來越多樣化,也許在現實生活中身材瘦弱,但是在網絡游戲中的形象卻是高大威猛,虎背熊腰,或是成了一個較弱風情的弱女子形象。
在虛擬身份的諸多要素中,性別最能引發別人的好奇,幾乎所有在游戲中交談的玩家都會忍不住詢問對方的性別,語音變聲器的出現又足以使“驗身”的語音以假亂真。很多時候,以女性形象進行游戲的男性玩家會得到其他男性玩家的殷勤幫助,但若一旦被發現了真實的性別,很快就會變得無人問津,甚至遭到指責。在《絕地求生:大逃殺》游戲中,一些男性玩家有時會刻意的對女玩家進行保護并無償的分享物資,部分男性玩家選擇女性形象進行游戲,一些在游戲中對性別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態度,但還有一些選擇使用變聲器模擬女性音色假扮女性玩家,以此在游戲中獲取便利。
網絡空間中虛擬身份的流動性導致了自我的多重化,你既可以接近你的真實自我,也可以憑借個人意愿做出自己的選擇。玩家在網絡游戲中進行身份建構,發現自己未曾被探索的心理角落或是希望通過游戲扮演重新創造自我。但無論如何,網絡空間中的身份與現實生活中的身份都是相關聯的,現實的物質世界總是基礎的,在網絡中扮演與現實生活中差別過大的角色,比如刻意構建的一個異性形象并加以維護,那么必將耗費大量的“精神能量”[1],導致現實與虛擬的同一性混亂,鏡中之“我”與現實之“我”的鴻溝越來越大,引發精神的迷失。
2.4 規則的邊緣化和倫理失當
赫伊津哈等人將游戲看作一種文化現象,認為游戲是“特定時空展開的人類活動,具有明顯的秩序性,遵循被玩家廣泛接受的游戲規則,沒有時勢造和物質的影響。”[5]規則和平衡是游戲的重要特征,缺乏公平性規則的游戲難以長期吸引玩家的時間投入,必然會失去市場。這樣的規則由電腦程序固定并伴有強制的懲罰措施,比如在《絕地求生:大逃殺》中,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隨機劃分安全區,在安全區外就會因為中毒而失去游戲機會,這樣的規則不以玩家意志為轉移,具有絕對性。對于玩家而言,在游戲世界中能夠獲取到現實生活中感受不到的公平性規則和個性的自我展示機會,在游戲社會中彌補現實社會的心理落差,如此加深了對游戲的沉浸。而在消費主義觀念的影響下,人們對于理性、生命價值等的精神追求遭到消解,在游戲中,網絡暴力、網絡性騷擾和利用程序漏洞的不當獲利的行為頻頻出現,帶來了規則危機和倫理危機。
網絡游戲作為一種電子計算機程序,其本身由代碼和相匹配的龐大數據庫所構成。作為一種程序,網絡游戲就不可避免的會由于疏忽等因素出現一些漏洞。一部分懂得編程的玩家會針對這些網絡游戲的程序漏洞來制作一些“外掛”,通過改變游戲的部分代碼進行作弊,增加玩家個人的游戲滿足感并以此牟利。在《絕地求生:大逃殺》游戲中,游戲廠商的“外掛”監控長期處于缺失地位,在游戲大廳甚至出現了通過公共廣告播放“外掛”廣告的現象,一些高端“外掛”甚至賣出了6 000元1個月的價格。一系列諸如“自動瞄準”“透視”“鎖定生命值”等功能破壞了游戲規則和平衡感,嚴重影響了一般玩家的游戲體驗。有玩家估計,每一場游戲至少有1/10到1/5的“開掛”玩家,“絕地求生”也因此被戲稱為“神仙打架”。
虛擬的網絡社區放大了人們對于性的開放程度,在《絕地求生:大逃殺》中主要直接體現在粗暴的語言上,很多游戲玩家都未能回避過粗俗言語的騷擾。例如在游戲中一些玩家打著“帶小姐姐吃雞”的旗號,要求女玩家發語音,如果反復糾纏未果便一口咬定對方是由男性玩家假扮的,若發了語音,又免不了評頭論足一番。而在日常的交流中,一些玩家的用語也離性的話題,在組局過程中“來一發”“約嗎”這樣的語言極易引發他人的不適。由于此類行為只在游戲中發生,并沒有在現實生活中造成實質的影響,很多人對這樣的性騷擾行為不以為意,如果進行斥責則被認為是開不起玩笑。當前關于性騷擾的法律界定仍舊比較模糊,也缺乏有效的救濟措施,作為一種網絡惡習,網絡性騷擾的泛濫可能會形成一個長期的問題。
3 總結
生活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互聯網空間的迅速發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消費主義的影響,而網絡游戲本身作為一個以娛樂為目的的新媒體藝術形式,更是帶有諸多消費主義的特點,這樣的特點既推動了網絡游戲的傳播和風行,為玩家帶來了心理的愉悅和滿足,但同時也使網絡游戲帶有了消費主義的負面色彩,對玩家產生了不良的影響,產生了諸如網絡沉迷、精神迷失以及內容庸俗暴力等問題。《絕地逃生:大逃殺》游戲自上線以來既頗得非議但也廣受喜愛,對于消費主義影響下的網絡游戲,我們不能全盤否定也不應照單全收,網絡游戲并不是洪水猛獸,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優秀的網絡游戲產品作為新媒介時代的一種藝術形式也必將在大浪淘沙中最終留下大眾喜聞樂見的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參考文獻
[1]上方網.2017年與游戲內容相關產值將突破7 000億[EB/OL].[2017-08-07].http://www.sohu.com/a/162861859_166488.
[2]黃平.生活方式與消費文化[J].天涯,2003(6):
23-29.
[3]弗洛姆.健全的社會[M].孫愷祥,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105.
[4]李康化.虛擬游戲、身份認同與倫理建構——文化消費主義研究之二[J].中國文化產業評論,2004(1):132-143.
[5]赫伊津哈.游戲的人:文化中的游戲成分的研究[M].何道寬,譯.廣州:花城出版社,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