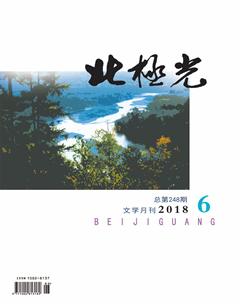埋藏在鄉村的情感
伍欣欣
接到張羽中這組《黃土村莊》詩后,我說:你可以再修改一下,修改到最滿意時給我。
他說:不想改了,這組詩是十多年前寫的,十多年過去了,只在我們縣小網站上發過,別的地方沒發過。
我說:你感覺怎么樣。
他說:我是很滿意的。
我說:現在好稿件也不一定好發表。
他說:這我知道。
我收到稿件在第一時間閱讀了。我有著迫切感。因為張羽中那句“十多年前寫的”話在我耳邊持續縈繞。一位作者把十多年前寫的稿交給我,這是多么大的信任,而在信任里又埋藏著多少希望與期待呢?我沒有理由不認真閱讀,我沒有理由不盡快給他回復處理結果。我晚一點回復他,他就會多一份煎熬與無奈的等待。
我沒細讀,粗略掃閱了一遍就知道稿件能否刊用了。這組詩在質量方面發表是沒問題的,如能細改一改,在思想上深挖掘一下,那會更好。我跟張羽中說:你再改一改可能會更好。
他說:真不想改了。
我說:那就這么發吧。
我在沒收到張羽中《黃土村莊》這組詩時,在他介紹時,憑著感覺判斷就知道是寫鄉村的。文學作品中不論是小說、散文,還是詩,寫鄉村的都很多。寫的多無關緊要,主要是看能否寫出亮點與新意。別人寫過的素材也可以寫,但要寫出不同的思想與文學色彩。
寫鄉村的作品多了,如想寫出特點與新意就更難了。
我在想作家,或詩人,為什么愿意寫鄉村呢?可能因為鄉村是生活的基色吧。不管是在城市生活的人,還是從鄉村走出去的人,大家幾乎對鄉村都是了解的,也是熟知的。因為城市從前沒這么大,也沒這么繁華,更沒這么擁擠,城市的繁華與擴建全部來自鄉村基礎上的。城市的生活也是由鄉村來保證的。我們生活中不住高樓,沒有工廠,不開轎車,不去商場,依然可以生活,人類依然可以一代又一代繁衍下去。如果我們不吃飯,沒有糧食,沒有肉、沒有蔬菜就生活不下去,人類就得滅亡。城市是長不出糧食的,鄉村是糧食的來源。這就是鄉村跟城市的最根本差別。然而這種差別被城市的繁華遮掩了,好像沒了鄉村人們還能生活下去,人類還能生存,這是觀念上的一種悲哀與錯誤。
可是張羽中寫的《黃土村莊》這組詩沒有直來直去的寫鄉村,也沒寫鄉村是糧食的來源地,更沒寫人生存的前提是需要吃飯,以食為天,而他寫的是土地,老人、村莊……這正是人類生存所需要的環境,這也是作者對鄉村感情的記載與抒發。
鄉村是作者的家,也是作者生活的地方,從而能體現出他對村莊的感情是深厚的,對土地有著無限依戀,沉浸在這種生活的氣息里。
張羽中在《泥土》這首詩中寫著:
杏子黃了的季節
故鄉,便呈現出一種
赤橙黃綠的色彩
這種時候
回到山里
有一種讓人說不出的親切感覺
而在山里
泥土沉默的聲音
最讓你覺得激動
一只綠蟈蟈在山坡上叫著
一片山丹丹在山坡上開著
山里人的孩子
光著腳丫走在
不遠的砂石地里
任遠方屬于他們的泉水
在大山腳下流過
山里人
他們年復一年
泥里來泥里去的活著
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
也就是莊稼們
在山嶺之上
整齊生長的日子
而七月流火,七月豐收
七月的陽光
讓人想起
所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痛苦
讓人想起
農人們對土地的
無限深情
于是
泥土
這種很普通的物質
自然而然地
變得生動起來
與陽光一起
成為我們
吃飯之余,所議論的
主要話題
作者這首詩主要是反映人們在鄉村生活的狀態、快樂的生活場景。鄉村生活原本要比城市生活單調的多,失色的多。作者曾經去過許多大城市旅行,是見過世面的鄉村人,對城市不乏了解,所以他避開了鄉村與城市的差距,在自然環境中尋找詩的突破點,展現獨特的詩風。這樣把詩句寫得生動而形象了。
作者在詩中把人、自然環境、融入在一起,形成生動的畫面。
詩與小說和散文不同,小說和散文篇幅長,思想容量大,是經常有場景出現的,但詩不是,詩容量小,受篇幅制約,很少有這么寫的。詩主要是以抒情,傾訴、哲理、隱喻寫法為主。如果詩寫出了生活的場景,要么是成功的詩,要么是失敗的詩,應該說用這種寫法創作詩多數是失敗的。因為詩的容量小,限制了描寫,想展示全景比較難。如果詩想跟小說和散文在描寫場景這方面一爭高下,應該是沒有優勢的,處在下風。沒有優勢不等于不能寫。這就要看作者對寫作技巧的運用和對生活的感悟能力了。
張羽中在這方面運用的相對比較好。我從《山村》這首詩中就能發現作者在這方面的長處和見解了。他這么寫著:
下雨的時候
山村
沉浸于一種
無以言傳的靜謐里
雨絲朦朧,天空朦朧
莊稼
這種山村最得意的風景
也朦朦朧朧的
為雨而立
因為雨
我想起詩歌般的歌謠
很多鳥
飛旋而起
占據所有空間
而水
這種莊稼的靈性
在心頭緩緩流動
讓昨天圍繞我們
淹沒世界的盡頭
在山村
炊煙總是很多
于天空與土地之間
升起
日子又過了一天
鳥雀啼聲依舊
農人們在瑣事中
站起而又倒下
憑著跟祖先相同的姿態
回到土里
關于山村
我想起父親
種莊稼的姿態
在長滿了陽光的土地上
揮動雙臂
年年歲歲
土地
這種很簡單的東西
因為我們
才顯得生動
而我們
也因為土地
才活得悠然
活得不緊不慢
這首詩把鄉村寫得非常深沉,寫的感情那么真。他寫得飽滿,情中有物,物中有情,能看出來他對鄉村的熱愛與深情。這是不難理解的情感。作者生活在黃土地的村莊里,在這種自然環境中一年又一年的生活,所以這里的人與物都進入他的視野中。作者熱愛這里的人,愛這里的一草一木,情感埋藏在普通的生活中,如果有機會展示時,便能如清泉一樣輕易流露出來,滋潤著生活的土地。
他在《老人》這首詩中就是這樣寫的:
我要以莊稼的名義寫你
老人
你站在莊稼地里
你的雙手沾滿泥土
而在你的身后
莊稼們都在快樂生長
莊稼們是一種風景
一年一茬的生長
一年一茬的美麗
如果不種莊稼
還能干什么呢
老人一年一年的老去
雙肩常常疼痛不止
臉上的皺紋
記載著我們的過去
也記載著
我們的無限深情
老人在城里
陽光總是跟我
保持著垂直距離
我周圍人聲沸騰
常常因為貨幣而廝殺
可是
在靜謐的山村
你知道這些嗎
你站成了一種莊稼的姿態
你在想什么呢
老人
你的童年是否和我一樣
是一路圓形的鵝卵石
老人
我在城里
常想著你在地里的時候
老人不只是鄉村有,在城市也有,城市是人群集中的地方,老人相對要比鄉村多。這么一來應該寫城市的老人更好。可是張羽中是生活在鄉村的作者,他的視野中是鄉村生活。所以他的詩句落在了鄉村老人的生活上。
作者在這首詩中主要是體現老人一生的勤勞,辛苦與責任。這是有著懷舊與感恩的詩。作者在詩的結尾寫著:老人/我在城里/常想著你在地里的時候。這是深情的詩句。
從張羽中這組《黃土村莊》詩中我們能了解到作者對鄉村的感情是深厚而真摯的。
作者生活在甘肅的鄉下。我對甘肅鄉下的生活并不陌生。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在黑龍江北大荒國營農場讀小學,當時學校號召學生采集草種,支援甘肅、新疆造林,防沙。那時甘肅給我留下了貧窮的印象。
2017年10月我被邀請去甘肅參加文學活動,有機會了解那里的生活與人文。那里的經濟不算好,相對屬于落后地區。可是張羽中生活的好,無憂無慮,很舒心。這證明他會經營生活,懂得生活,屬于會謀生的人。
我想既然作者會經營生活,有謀生策略,那么在寫詩的路上也應該走點捷徑,用點技巧為好。靠寫詩掙錢是維持不了生計的,是無法生活的。可生活好了,經濟寬裕了,運用經濟方式是可以幫助提升在詩界影響力的。比如現在的詩集幾乎全部是自費出版的,如果沒有經濟做后盾,詩集是無法出版的。詩人開作品研討會也是需要花錢的,這就是錢對寫作與生活的作用。
作者生活在鄉鎮上,生活在鄉村,并且是西北鄉村,這對發表詩,對進入文學界是不利的。雖然寫詩的素材可以來源鄉村,但在鄉村生活的人很少有讀詩的,不利于詩的傳播。如果想把寫出的詩讓更多人讀到,就得想辦法運用信息,媒介等途徑把詩傳開。
如果把一瓶茅臺酒,或五糧液及法國紅酒放在深山里,誰又能聞到好酒的醇香呢。寫詩也是如此。
也許有人會說余秀華不是在鄉村寫詩嗎,不也成為家喻戶曉的知名詩人了嗎,那是她的幸運,放眼看去在中國詩界有幾個余秀華?可能第二個都沒有。余秀華的成功是一種偶然與機遇的結合,適應了某時期的文風,這種現象是罕見的。
俗語說:酒香還怕巷子深呢。何況寫詩呢,并且是剛起步的詩人。
羽中,我想你對鄉村那么有感情,既然你能把生活經營的那么好,相信用些心思,加上勤奮,也會在詩界有所建樹。遠的不說,在你們縣,或在你們市及省內的詩群中,想有一席之地是應該能做到的。
我說的話別當真,只供你參考。
祝你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