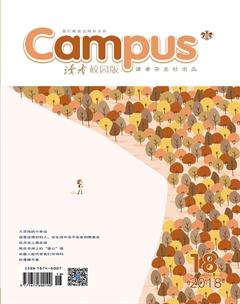同桌那些事
張亞凌
如今想來,我灰色的青春源于沒有遇到一個有趣的同桌。同桌雖然換了一個又一個,奇怪的是他們像從同一個模具里倒出來的:沉默、好靜,還都是學霸。
那時的我,看著同桌心里就堵得慌,就慨嘆:一個孩子的快樂程度真的取決于她的同桌啊。
35年前,男孩女孩輕易不說話,一說話就是吵架。老師為了教室的安靜,就偏偏讓男女生坐同桌。
看看別人的同桌吧:
桌子上都有條三八線,經常因為誰越了線,先是撞胳膊,而后爭吵;也會為了做值日時誰掃多了、該誰擦黑板而吵吵鬧鬧;還會因為后來的想坐里面的座位,外面的不起來讓空兒,擠不進去而摔書斗氣……
算了算了,給你這樣說吧,人家的同桌,至少都是會出氣的“活物”。而我的同桌,不論哪一任,都一個“德行”:
趴桌子從不理會我占了多少桌面,有時我趕到教室時人家把地都快掃完了,我還沒靠近座位人家就站起來給我留出空兒……
沒有任何糾紛與摩擦,倒讓人覺得無趣至極,好像我就多么讓人生厭,不愿意與我有一丁點的牽扯。
一直不知道為什么,一進入初中我就被指定為班長。或許是因為我是個傻大個兒,或許是因為我看起來像個女漢子,或許因為老師真的沒有合適的人選就把麻稈頂旗桿。反正我一進入初中就是班長,一做就是一年半,還是6個班長里唯一的女班長。
我掌握著全班學生的“生殺大權”,初一時的班主任是體育老師,一直以我的匯報來處理班務,處理的方式也很“體育”:不是揪著耳朵扇,就是踹幾腳。而我又是認真過度的孩子,專門有個本子,會形象地描繪班里某件事的詳細過程,也能生動地記錄整個事件中牽扯到的學生的言行,順帶還揣測其心理。
扯遠了,回到同桌。
我初中時的第一個同桌,姓田。我任何時候無意間與他的目光相撞,他都立馬調整成一種很無辜的表情,清澈的大眼睛里盡是不安,似乎很膽怯、很可憐地在問我“我又怎么了”。他這個表情卻讓我很受傷,讓我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感覺,好像我瞅他一眼都是在欺負他,以至于他犯了錯我竟然不忍心記下來。多年后我才想明白了,那小子賊精,示弱其實是以退為進。
田同桌的安靜表現在下課很少出去玩,總是拿起下節課要用的課本,該背的背,該念的念。只是,他是邊瞅著外面邊預習的。我曾悄悄側視,感覺他的安靜是那種壓抑著沸騰的安靜,他的目光里似乎跑出了無數雙腳在外面撒歡。
初中三年里,他的考試成績一直是我們班前5名。
我的第二個同桌姓秦。他是期中考試后從城里轉到我們小鎮中學的。就是在那個時候,我覺得詞語其實都是有生命的,只是單單等著一個人或一件事來激活它。比如,“鶴立雞群”這個詞兒,就是見到秦同桌后才活泛在我腦海里的。
秦同桌皮膚白皙,身上似乎總有一股淡淡的清香。不像別的男生說話像放炮,他做任何事情幅度都很小,輕輕地,像是盡可能隱藏自己一般。可他自帶光環,來之后考試成績穩居全班第一,就像珠峰覆蓋著白雪想隱去自己,結果卻變得更高一樣。
我寫作業經常會占去多半桌子,秦同桌可以挪至桌面的1/3處甚至只用桌面的一角,這并不影響他書寫的漂亮,可我的字依然比我的人還難看。我也曾記下秦同桌上地理課做數學題的事,可班主任連他的衣領都沒拽一下,只是提醒他要注意。看來別人對你的態度取決于你的狀態。有時在我絞盡腦汁毫無頭緒時,秦同桌會將完整的演算過程推到桌子中間,我便飛快抄寫。
秦同桌下課也不大出去,喜歡用鉛筆畫畫。畫著畫著,臉上就有了淺淺的笑。
我沒有聽過秦同桌一聲響亮的笑,沒有見過秦同桌一次夸張的表情變化,沒有見識過秦同桌跟任何人有過矛盾或者來往密切……還是覺得哪里不對勁,秦同桌咋看都像教室里掛的一幅畫,好像完美到失真。不知他回憶起初中生活,會不會覺得我們都很小兒科、很幼稚?
我的第三個同桌姓盧。盧同桌很奇怪,好像隨時裝滿火藥,跟誰說話不超過3句,就豎眉瞪眼起了高聲,甚至還拍桌子,似乎他處處都有不允許別人碰觸的區域,卻從未跟任何人真動過手。
除了高聲,他是絕對安靜的。
不管誰問他題,他只需看一眼題干,就拿起筆,一步一步做出來,而后將本子推到你面前,從不講解。是自卑怕自己說不清,還是高傲得懶得開口?天知道。
他的數學超級好,作文極其差。每每寫作文,就趴在桌子上直轉筆,簡直就是找不到出口的困獸,給了數學一塌糊涂的我些許安慰。
第四個同桌姓徐,徐同桌成績一直是緊咬秦同桌的。插一句,我們班女生性格活潑,卻不爭強好勝,成績大多普通。頂尖的,也只是勉強擠進班級前10名。
徐同桌的安靜,是那種陽光般的安靜。他明明沒動,周圍人都像為了取暖般簇擁而來,他人緣極好,也是女生宿舍晚上談論最多的人。有段時間,徐同桌喜歡上了看詩集。我偷偷瞥了一眼,詩句旁邊配的插圖都是怪怪的外國人。
坐在我前面的是甄靜,一點都沒辜負名字,她是女生里最文靜的一個。甄靜也是女生里最好看的一個,只是學習成績很一般。
一天,從甄靜書里掉下來一頁紙,被她那唯恐天下不亂的“二貨”同桌飛快撿起。“我愿意是激流,是山里的小河,在崎嶇的路上,在巖石上經過。只要我的愛人,是一條小魚,在我的浪花中,快樂地游來游去……”甄靜的“二貨”同桌扯著公鴨嗓子陰陽怪氣地讀了起來。大家都看著甄靜,她倒一臉茫然。
“甄靜給男生寫情書”的流言因此事開了口子……我是從這件事上明白,凡事不能開口子,一開,就泛濫了。班主任找了甄靜,又叫來了她的父親,讓她父親把她領回家好好反思一下。幾天后,甄靜的父親到宿舍搬走了她的鋪蓋。那個叫甄靜的女生,從我的初中生活里徹底消失了。那時輟學的孩子比較多,每個學期開學時都有幾個不來的。
記得在那件事發酵時,我曾在宿舍里暗示說徐同桌在看詩。可別的女生都說,就算是徐同桌寫,也不會寫給甄靜,她有啥了不起的。一定是甄靜寫給別人還沒送出去被發現了,竟然還想到用不同的字跡寫……沒有人愿意相信是徐同桌寫的,即便她們親眼看到徐同桌寫,都會認為是被迫的。徐同桌是大家的白馬王子,怎么能屬于某個人呢?
或許只有我察覺到,徐同桌有幾天情緒不對勁,后來還請了幾天病假。
我因此開始反感徐同桌,認為他是敢做不敢當的縮頭烏龜。只可惜那時我不再擔任班長,只是學習委員了。長大后才發現,由不得自己的事越來越多,該自己負責的,做到不推諉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還有賀同桌、金同桌……每每想起中學生活,最先醒來的,還是關于同桌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