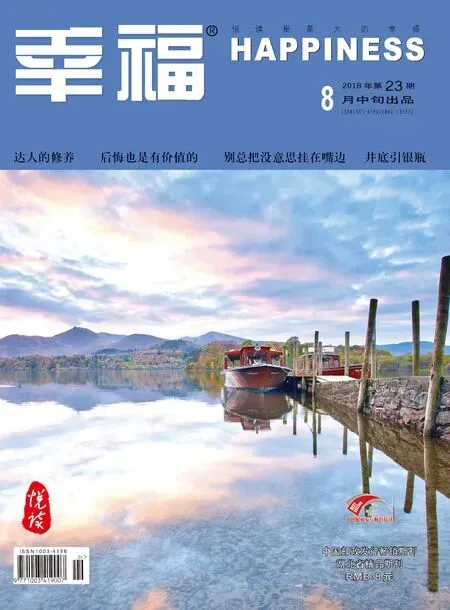劉勇:贛江風情散文四題
妹子我生崽養女樣樣強咦喲
夫妻船
古往今來,夫妻船是水上最秀美的一道風景。
贛江舟船形狀多達百余種,只要男人和女人牽手上得船來,任何一種都可以稱為夫妻船。
夫妻船,披星戴月,風雨兼程。
有水的地方就有情,有愛,有溫暖的家。
四十年前,贛江上的舟船幾乎都沒有機械動力,一色小噸位的木帆船裝載著走水路的貨物,扯帆、搖櫓、撐篙、拉纖都是兩口子干的活計,長年累月,往返在江上的大都是夫妻船。遇到逆風上水,一條條的夫妻船便在避風灣口停泊,然后每家派出一個勞動力,喊著號子,拉動纖繩把船只拖到上游,一條也不會落下,等到來了好風向,所有的船只舉帆并進,再去迎接下一段的旅程。
夫妻船,夫妻們同心協力,撼動江魂。
據史料記載,商周時期的贛江,就有“刳木為舟”之說,十八灘水道,有舟船行走。原始勞作的夫妻船,穿越了幾千年的時空距離,承載著歷史不可磨滅的記憶,它們是船的太祖太宗,功不可沒。
解放前贛江一帶碼頭,每當夕陽西下,便可以看到成群結隊的船只錨泊港灣,呼啦啦地降下帆來,就像天頂落下一片片五彩云霞,那景致煞是壯觀。這當口,老公船頭點燃著竹煙袋,老婆船尾扇亮了爐膛火;精力過甚的后生仔俚爬上木桅唱情歌,水汪汪的細妹子洗衣棒槌打得浪花樂。
高高的木桅就好似一把江上的大胡琴,纏在上頭的后生仔俚是扯長脖子唱:
十八灘頭波滾波
十八男人歌連歌
昨日唱得胸口直發慌
今日唱得心里直冒火
妹子妹子你應一聲
哥哥我口干舌燥好難過喲嗬

天上有云云不飛
水里有魚魚不走
葉綠花紅你不著急
春來秋去你白了頭
妹子妹子你望一眼
哥哥我手粗腳粗一身粗喲嗬
水邊洗衣裳的妹子若是看中了那個唱歌的后生仔俚,禁不住就要回唱起來:
十八灘頭浪壓浪
十八女子忙又忙
東頭忙得扯腳落了鞋
西頭忙得理衣脫了妝
情哥情哥你等一等
妹子我腰酸肚痛急得慌咦喲
山邊有水水不鬧
路旁有草草不黃
三三九九年年旺
七七八八日日長
情哥情哥你聽一聽
只要歌子對上心頭,就會有媒婆鉆進艙牽紅線,男要娶,女要嫁,皆大歡喜。待到結婚的那一天,可謂是水上一家親,前來助興道喜的船兒多達上百條,浩浩蕩蕩,嗩吶鑼鼓一響就是好幾十里。遠遠望去,江上呈現出一塊浮動的活土地,天不見黑,已是萬家漁火。結親三天無大小,天王老子也管不了。大碗喝酒,大聲劃拳,這邊船頭邁上那邊船尾,一小刻功夫,便串完百家的門庭。如此親近,僅有夫妻船上才有。
打這一日起,江上又會多出一條夫妻船。
那年頭的走船人家,岸上沒有一寸土,一片瓦,無怪乎江上人說,“世間有三苦,撐船打鐵磨豆腐。”既然命中注定與水結緣,與水為生,船家人照樣能活出今生今世的風采。
贛江一瀉千里,是夫妻船給了它勃勃生機。
沒有這些傳宗接代的夫妻船,江是死江,河是枯河,即使唐代大詩人王勃再登滕王高閣,面對贛江之水也描繪不出:“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舳。云銷雨霽,彩徹區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
夫妻船,一輩子夫唱妻隨守著江,不分不離,不棄不舍,頭枕碧浪,腳踏激流,岸上的人家比不得。
夫妻船,贛江里漂動的生命,贛江里不沉之魂!

纖夫
早年的贛江纖夫,大都集中在萬安鎮碼頭一帶。船往贛州縣府,必在此地請好纖夫,渡過上游的十八灘兇險水路。
駕船的人一般稱纖夫為“小工”,根據船舶的大小噸位,請到一定數量的纖夫,三人、五人、八人不等。船老板在青石板臺階的碼頭上一聲吆喝,“這里來幾個小工!”立馬便有幾十名纖夫蜂擁而來。
纖夫是男人的活兒。
這些聚集在碼頭上的纖夫,他們都是來自萬安鎮周邊一帶四里八鄉的窮苦村民,長年累月為生計行走于十八灘航道,守著這份露宿風餐、嘔心瀝血的固定職業。這些男人的普遍特征是,頭戴一頂草帽,肩背一根纖板,腰插一雙草鞋。他們的年齡結構從少年、青年、中年到老漢,好體格好身板是最大的本錢。纖夫分有“頭纖”和“二纖”,這兩名纖夫必需要有過人的力量和膽氣,尤其“頭纖”,還得有相當的探路經驗。上一趟走過的纖路,因為水位的變化,到了下一趟又得找出新的纖路來。船老板上岸挑選纖夫,最重視的就是“頭纖”和“二纖”這兩個人物,一旦航道上發生險情,到時船毀人亡,老天爺也伸不出援手。“頭纖”和“二纖”還得要有一付好嗓門,船老板會拍著他們寬厚的肩膀說,“伙計,喊一嗓門看看啰!”于是,那個敢做頭纖的漢子扯長脖子撕開喉嚨“么喲嗬……”的一聲喊響,其聲音的穿透力在江面上經久不息。
船頭上拋出一根長長的粗麻繩索,纖夫們將身上的纖板掛在繩索上,這就上路了。這是一個力量和智慧的群體組合,這一趟纖路他們將生死與共,同舟共濟,面朝河灘背朝天,二百華里的十八灘水路上,幾乎是要用性命換回他們應得的糧食和錢財。
江上人說,二四八月亂穿衣,指的是江南的天氣變化。江上人說,四月的天,鬼變的臉,熱時光屁股,冷時套布棉。烈日當頭的灘路上,水流湍急,沿岸的纖夫們都脫去上衣,光亮寬大的脊背上冒著白白的霧氣,滾出晶亮的汗油,全身的各個部位都有一種最原始的火力在振動。那根粗粗的纖纜在他隆起的皮肉里深深地陷下,赤紅的皮肉發不出絲毫的響音,那樣種彈性、韌性有如最優質的黑橡膠,可以承受于它千倍的體積。
遠遠望去,他們黑黑的身體就像是趴在地面上的甲殼蟲,挪動得十分的緩慢,然而帆船卻在破浪前行。那是一群閃亮的雕塑,他們如猿猴一般攀懸在峭壁上,他們如巨蟒一般游走在灘水邊,他們如餓狼一般穿梭在灌木叢中。他們驃悍,粗獷,雄渾,他們擺動著頭顱,他們的吼叫聲,吶喊聲,氣吞山河。
依羅,依羅羅嗬
依羅,依羅羅嗬
嗬嘿嗬嘿扯起纜羅
嗬嘿嗬嘿打住腳羅
天上的雷公爺羅
地下的土地婆羅
求得你一個好風向哩羅
請出你一個好水流哩羅
哈羅羅嗬
依羅羅嗬
船老板在船尾把牢舵柄,看到自家的船走得順順當當,一開心,會喊出船艙里做飯的老板娘。老板娘來到船頭,手上打著竹篙子,亮開清麗的嗓門唱歌子,她唱一句,纖夫們便和一聲,快活得不得了。
一繡荷包才起頭喲
嗨喲嗨
五色絲線要郎挑喲
嗨喲嗨
根根絲線連情義喲
嗨喲嗨
情深意長永不丟喲
嗨喲嗨
二繡荷包二朵花喲
嗨喲嗨
芙蓉牡丹兩不差喲
嗨喲嗨
郎是芙蓉剛開口喲
嗨喲嗨
妹是牡丹才爆芽喲
嗨喲嗨
……
苦也罷,樂也罷,纖夫們為征服腳下的河道,煥發出了人類最本質最原始最浪漫的男兒豪情。今日江面,早已不見纖夫的蹤影,然而,他們的精氣神在,他們的豪邁在,一如滔滔贛江恒久、永存。
灘師

灘師,引水領航之人。
贛江上游十八灘水道,便有灘師為南來北往的舟船引航。他們終年累月同險灘惡水打交道,生存的依靠,就是水上這些星羅棋布、暗藏殺機的灘頭。
憑記載,宋代大詩人蘇東坡,舟行至贛江十八灘的第一個灘頭黃公灘,船撞礁石,險些送了性命,詩人感嘆不已,賦詩一首:“十八灘頭十八名,一為恐惶更縹神。人生俗子為名利,誰敢踩舟在此行。”因此詩之后,江上人將此黃公灘改為恐惶灘。水上船家流傳民謠有:“贛江十八灘,好似鬼門關。十有九舟險,關關心膽寒。”、“十八灘上灘鎖灘,二百水路彎打彎,往前路口哭聲切,天柱門前尸難還。”
沒有灘師領航,外來的船只,休想過得十八大灘。
灘師把守著灘頭,似乎有點像江洋大盜,要打此路過,留下賣路錢。正因為有灘師的存在,贛江之水行船過渡才有生機,才現活力。
“往前灘”又稱“往前路”,它是十八灘航道最為險要的灘頭。灘的尾端座落著陳家村,此村是解放前灘師們居住的集中點。陳家村的周圍除了石頭就是沙土,草木稀少,不長林,不出糧,村上人都是靠走船放排為生,門前屋后的水路就像自家的菜園那般熟悉,洪水走哪條路,枯水行哪條溝,都攔不倒他們。起初外地來的船只上贛州,要請當地的船民幫助過灘,年月一久,村上的人就明白了,只有他們陳家村的人才識得這條水路,漸漸的大家就干上了這個引渡領航的職業。最早的灘師,也就這樣形成了。
灘師對河道上的水流、暗礁、險灘了如指掌,何時轉舵,何時點篙,何時打錨,他們駕輕就熟,得心應手。如此精粹嫻熟的撐船功夫并非一日之寒,他們大都是子承父業,世代相傳。
據說陳家村有一名綽號叫“二棍子”的灘師,3歲時,父親就將一根繩子栓在他的腰上,扔進水流里隨船拖動,灌飽一肚子水被提上船來嘔吐干凈,接著又扔進水里去,一直到他能夠在水面上跟著船一樣自由自在的浮起方才罷休。6歲時,他還被父親用這法子扔在浪水里,那一堆堆暗藏在江底的礁石,碰撞得他全身青一塊紫一處的,只要還有一口氣,父親絕不允許他上船來歇口氣。13歲時,滿腦子都是水路圖的二棍子就能獨自操船過灘了,再兇險的水路都不在話下。二棍子到18歲那年,已經是聞名十八灘水道的灘師了。凡有舟船到此,點著名要請陳家村的二棍子領航,全部的家當和性命押到這樣的灘師身上才能放心。
暗礁林立,漩渦湍急的灘道,船一入水流,便像一條受傷瘋狂的野牛,咆哮的惡水浪尖之上難以駕馭,每一處彎口都驚心動魄。這種時刻,灘師就如身陷千軍萬馬的廝殺戰場,吼叫聲中,尸橫遍野,浪水飛濺,盡顯英雄本色。
灘師要吃上這碗灘飯又談何容易,每一回領航都是腦袋拴在腰間,命懸一線,幾經生死。送過一趟船,就得翻山越嶺徒步返回,接著又再送下一趟船。春夏秋冬,酷暑嚴寒,他們在領航的途中,人都似一根繃在弦上的箭,掌舵撐篙啟帆打錨,半點不得分心,一旦觸礁破船,說不定就得傾家蕩產,還有可能要遭到船民幫會的追殺。
灘師,稱得上是這條江上最神勇的好漢。
新中國成立,政府為疏通治理贛江上游航道,50年代中期,先后派出幾批工程隊伍,利用幾年的時間,徹底炸開了十八灘。
百余年來,曾經以兇險灘路為驕傲為榮耀的灘師,從此告別故鄉的水土,他們與暢通無阻的贛江一樣劃上了新時代的句號,成為今日江上之傳奇,而那古老的灘師號子也將成為那一段歷史的寫照:
咦喲嗬,嘿喲嗬
打起篙喲
掌起舵喲
纜索一根心頭鎖
灘頭數里難得活
咦喲嗬,嘿喲嗬
三九四九不見日
三伏四伏不見風
走起來喲
喊起來喲
江面飄出一條船
灘師背上一座山
……
船民號子
號子,其實就是歌。
船民號子,那就是船民的歌。如江河一般奔放,如湖水一般清澈,如土地一般芬芳,如天空一般晴朗。
最原生態的歌,應該是號子。
我甚至以為,盤古開天地的第一首歌,是從號子開始的。號子詮釋了人類最古樸最原始的聲音,一個音節“嘿”,兩個音節“嘿喲”,到三個音節“嘿喲嘿”,多么富有磁性,富有質感。是勞動激發了號子,是號子創造了歌。
試問,宇宙間還有什么歌曲能比號子更加壯美呢?
號子,不用譜曲,不用奏樂,它是用人體的力量去彈奏的,足可彈奏得地動山搖,倒海翻江。
孩提時代,我就被號子的聲音所震撼。那時候我家居住在九江赤湖水產場,一邊是浩渺百里的赤湖,一邊是洶涌澎湃的長江,中間隔著一座高高的堤壩,親眼見到幾十名上身赤裸的船民呼喊著震天的號子聲,抬動著一條幾丈長的大船,從湖水的這邊越過山一樣的大堤,推向長江。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聽見的號子聲,船民們喊唱了些什么,我一字都沒有記清,但是“嘿喲嘿喲”的聲音至今難忘,現在想起,體內還都熱血沸騰。
號子,是勵志的篇章。
而船民號子,后來成為我的至愛。
80年代中期,我在航運部門當宣傳干事,因為寫通訊報道,打交道的對象經常都是駕船的人。一次隨船采訪去贛州,結識了幾位船老大,他們都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人,我就問起了船民號子是怎么喊的,尤其我想知道開頭的號子。幾位船老大說法不一,他們試著喊了幾嗓子,其“哎喲”、“咦呀”之類的喊聲也各有區別。到底誰是正宗的贛江船民號子,有一種說法我認為還是有點靠譜兒。
其說法的來源是百年前的一則江上小故事。曾有駕船的父子倆,一次船上裝載了往贛州府里送的布匹綢緞,壓船的一個主顧,一路上小心翼翼,生怕半路被惡人劫了貨去,對駕船的父子倆是照應得千好萬好,只求船走得快,行得穩,早日到達縣府。誰知船上的那個兒子起了貪財之心,要謀害主顧。這是一個無風的夜晚,船泊在一塊沙洲上,兒子悄悄起身,貼著船舷往主顧睡的后艙去。剛到后艙口,但見一個人影迎面出艙門,兒子當即一刀捅去。那人慘叫一聲栽進江里。兒子正喜之時,艙門又出來一人,這人卻是主顧。兒子方才明白所殺的人竟然是自己的父親,立時大哭大喊起來:“哎喲嘞喂!哎喲嘞喂”!就這樣,這一聲“哎喲嘞喂”的哭喊相傳下來,便成為江上號子的開口腔了。走船人家都聽過這則故事,都相信真有其事,用上這個哭腔,或許是一時的開心快活,或許是提示和警告那些貪財而遭到報應的人吧。
大凡贛江船民的號子開口多用“哎喲嘞喂”為引子,而江西一些古老的民歌中也多有出現。由此推斷,此號音是有一定的來歷了。
開船號子,“哎喲嘞喂——起頭啰——”。拉纖號了,“哎喲嘞喂——扯起來啰——”。撐船號子,“哎喲嘞喂——著把力啰——”。下灘號子,“哎喲嘞喂——打牢舵啰——”。搖櫓號子,“哎喲嘞喂——頂足了勁啰——”。類似走船的號子音在那一段歷史的贛江兩岸此起彼伏、遙相呼應,撼動著久遠的水上運輸。勞動的號子音并發出激情,激情中產生無限的假想,因而贛江流域的民間歌謠在船民們不同的情緒中滲透到號子中去,使得船民號子更加豐富多彩,繽紛奇麗。

遇上大船隊過江,桅帆高舉,浪花飛濺,那番情景就像是個盛大的節日了。男人們撐篙搖櫓,女人們唱號子助興。若是到了船過激流險灘,男人們一身的沖天豪氣:
哎喲嘞喂,哎喲嘞喂
水上萬把力啰,船上力一把
捉緊一條粗粗咯纜啰
打牢兩根圓圓咯腳啰
面朝黃土頭頂天
閻王殿里我走前
下得灘頭七七八八九九十十
求得蒼生四四三三二二一一
哎喲嘞喂,哎喲嘞喂
土里長啰,水里埋啰
快活一生,一生快活走起來啰
如此逍遙亢奮、如此悲烈粗獷的號子聲,無處不都在抒發著走江人的思想情感,無處不都在展現出那一幅幅船民們搏擊風浪的雄偉畫面。
“哎喲嘞喂——”那是絕對的贛江味。
(作者介紹見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