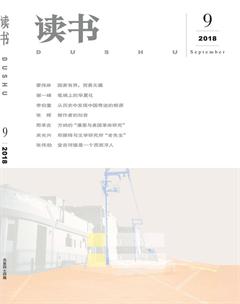往而復來
黨晟
一
如果說,一般意義上的翻譯是 “由彼及此 ”或“由此及彼 ”的語際轉換(interlingual transformation),那么,翻譯西方學者的漢學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則可視為 “往而復來 ”的信息交流。因為漢學著作討論的是中國的歷史文化,所以其中必然包含大量源于漢語的概念及譯自漢文典籍的專名、引文,此類內容的 “回譯 ”是翻譯的難點之一。
其中,引用文字通常不必另行翻譯,但需查明出處,核對無誤,照錄漢文原文即可。另有涉及中國文化習俗、名物制度的內容,若無現成的 “出典 ”可資參照,翻譯難度當然更大。不求甚解,生搬硬套,很可能會犯專業人士眼中的常識性錯誤。
為了闡明上述問題,不妨分析以下實例。
A cousin of Wang Hsi-chihs father, Wang Tao, took the leading role in founding the new dynasty and served as its first chancellor.
直譯:王羲之之父的堂兄王導在建立新王朝的過程中發揮了領導作用并擔任第一位宰相。
所謂 “某某之父的堂兄 ”,實屬典型的歐化譯文。因為英語沒有指稱這一親屬關系的名詞,所以只能 “拐彎抹角 ”地加以說明。如同將 father-in-law(岳父、公公)譯為 “法定的父親 ”一樣,“父親的堂兄 ”只是用漢語的字詞 “轉抄 ”英語,而“從伯 ”“從叔 ”才是 “acousin of ones father ”的恰當對譯(《晉書》即稱王導為王羲之 “從伯 ”),故此句可譯為:王羲之從伯王導在新朝建立之際領袖群倫,居功至偉,曾拜為東晉首任丞相。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中,aristocratic families(貴族家庭),應謂“閥閱之家 ”;noble expatriates(高貴的移民),當指 “流徙士族 ”; the southern intelligentsia(南方知識分子),也就是所謂的 “江左名士 ”; mystic(神秘主義者),說的是道教的 “通靈代言者 ”。
按照漢語固有的名稱,collection of rubbings(拓片集),應作 “叢帖”;epigraphy(題銘研究),應作 “金石學 ”;pyramidal roof(金字塔形的屋頂),即“攢尖頂 ”;TLV mirror(TLV鏡),即“規矩鏡 ”。
某些重要概念,必須查閱漢文典籍,才能找到恰切譯名。例如,在論述道教早期傳播的英語著作中,經常見到 “revelation”一詞,或譯為 “神啟 ”“示現 ”,總覺勉強。其實此語出自陶弘景(四五六至五三六)編纂的《真誥》,對照原典,可知 “revelation”為“旨”(仙人所授旨意)的對譯。因此,從施與者和接受者的不同角度出發,該詞可以譯作 “授旨 ”“受旨 ”或“仙真降誥 ”。
如果說文學翻譯的難處在于譯者必須 “體驗他人的體驗 ”,那么學術著作的翻譯則要求譯者熟悉相關學術背景,甚至重復作者做過的基礎研究,包括通覽其所列具的主要參考文獻。假定原文存在某些疏誤,也應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以適當的方式予以補正。如此,則所完成的譯文方得稱為 “譯著 ”,而不僅僅是用漢語轉抄原文拼湊成的一份文字材料。
二
正如建筑在西方享有 “諸藝之母 ”(mother of the arts)的崇高地位,漢魏以降,書翰手札在中國就被視為最具價值的藝術作品,地位居于繪畫、雕塑之上。中國歷代書論篇帙浩繁,早已形成獨特的批評體系,并且擁有一套精妙、豐富的專門術語。用英語論說中國書法,難免因詞匯貧乏而時有 “捉襟見肘 ”之感,比如漢語的 “結字 ”“章法”,英語多譯為 “composition of characters”(字符的構成)和“overall composition”(整體的構圖),不僅用語重復,而且易于混淆。再看一段關于王羲之《喪亂帖》的完整描述:
The strokes are slightly more abbreviated than in the Lan-ting hsü , and several of them are connected in a continuous movement. There is more freedom in the handling of the brush without, however, sacrificing precision. The compositional balance in the characters is sophisticated and delicate, and they follow each other in an easy flow.
直譯:筆畫比《蘭亭序》略有簡化,其中的幾處在連續的運動中相互聯結。毛筆的駕馭更為自由,但沒有犧牲精確性。字符結構的平衡既成熟又微妙,它們在順暢的流動中前后跟隨。如此蹩腳的譯文,令人實難卒讀。同樣的意思,稍加潤色,結果會大不相同:
比之于《蘭亭序》,此帖點畫略顯簡率,且有筋脈相通、勾連不斷之處。其用筆收放自如而不失精謹,結字欹正得體而益見淳熟,且字字相承,上下映帶,氣韻舒暢。西方的字體設計,注重字幅寬狹、筆畫粗細的調整,借助數學方法以求均衡;中國書法(尤其是行草)則講究正斜、低昂、避讓、穿插,在動態中形成穩定的效果,故曰 “欹正得體 ”。前者可比建筑,具有嚴密的結構;后者妙似音樂,體現自然的韻律。此外,用筆的灑脫流便,亦非 “自由 ”可以概括,故曰 “收放自如 ”。“字字 ”對應“they”;“相承 ”對應 “follow each other”;“上下映帶,氣韻舒暢 ”對應 “follow each other in an easy flow”。譯文并不存在 “過度翻譯 ”的問題,卻將原文頗顯生澀的表達轉換成了中國書論的成熟語言。
三
翻譯也是一門專業,當然需要專門的方法和技巧。如果不能合理解決譯出語和譯入語的轉換問題,即便具備分別使用兩門語言的能力,也難以勝任翻譯的工作。限于篇幅,此處僅僅討論英語文章中長句的翻譯問題。因為漢語無法通過詞形變化體現詞語的語法功能,也沒有關系代詞、關系副詞表明句子成分之間的邏輯關聯,倘若譯文語句冗長,勢必給讀者造成閱讀和理解的困難。
在英語文章中,下面的句子并不算太長,但主語 bibliography(文獻)和賓語 titles(美稱)均附有多重定語,依照原文句式翻譯,也會讓人有 “一口氣讀不下來 ”的窘迫之感:
A bibliography on Wang Hsi-chih compiled in 1973 by Uno Sesson and Nishibayashi Shōich lists more than 200 Chinese and Japanese titles about the Lan-ting hsü.
由宇野雪村和西林昭一于一九七三年編撰的王羲之研究資料列出了二百多個中文和日文的《蘭亭序》之美名。遇到此類情況,就需要調整譯文的句子結構,將原文用作定語或狀語的成分 “提取 ”出來,譯為獨立的分句,從而使復雜的單句變為簡單的復句。沒有了堆砌拖沓的毛病,讀來自然明白曉暢:一九七三年,宇野雪村、西林昭一輯王羲之史料,所列《蘭亭》之嘉名,兼采漢和,總計二百有余。
另如:
A typical po-shan hsiang-lu of the Han period consists of a bowl resting on a stand that emerges from a basin filled with water. The bowl is covered by a cone in mountain form with several outlets for the smoke from the incense which is burned in the bowl.
直譯:一件典型的漢代博山香爐有一個安置在從裝滿水的盆子里伸出的支架上的碗。這只碗被帶有供碗內燃燒香料的煙散發出來的幾個出口的山形蓋子所覆蓋。
對照以下譯文:
典型的漢代博山爐有爐盤,置座上,下設貯水之盞形托,爐盤加蓋,呈山形,鏤孔,以便爐內所燃香煙散出。雖然意思相同,但前者照搬英語 “疊加 ”的表述方式,語句冗長,結構復雜,所以讀來拗口而且費解;后者采取漢語 “遞進 ”的敘說方式,也就是把相關事項分開來講,不僅條理清晰,而且言簡意賅。
總之,從事翻譯的人必須有清醒的母語意識。西方語言之間的相互翻譯是同一語系內不同語種的語際轉換;將西文文本譯為漢語文本是印歐語系(綜合語)與漢藏語系(分析語)之間的跨語系溝通。內在性質的區別決定了漢語譯文與西文原文很難形成表層的同構關系。
四
西方人名的翻譯,向有 “漢化 ”(sinicization)和“洋化 ”(foreignization)兩條途徑。據說第一位 “變歐羅巴姓名為中華姓名 ”的西方人是大名鼎鼎的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在進呈萬歷皇帝的奏折中,這位意大利傳教士自稱 “姓利,名瑪竇,字西泰 ”,儼然一副 “恂恂有道君子 ”的口吻。從明、清兩朝直至今日,大凡寓居華土的歐美人士和研究中國文化的西方學者,差不多都要為自己取一個像模像樣的漢文名字。與此相反,中國的語言學者和翻譯家大都抵制 “漢化 ”的人名譯法。林語堂明知瑞典漢學家 Bernhard Karlgren自取漢名 “高本漢 ”,然著書為文,始終稱其為 “珂羅倔倫 ”,那種 “絕不改口 ”的執拗態度,仿佛是一方強要入伙,另一方則拒之再三,閉門不納。既為音譯,就該盡量淡化其字面意義,以規避譯名的 “義溢出 ”(meaning overflow)現象。有鑒于此,“漢化 ”譯名之不可取,固無須多言,但遇到 “高本漢 ”之類的特例,愚見以為還是 “照樣拿來 ”為好。舉其理由,約有數端:
其一,人名為本人所認可,理應得到他人尊重;其二,許多西方學者的漢名已為中國讀者所熟知,如法國的石泰安(Rolf Stein)、德國的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荷蘭的許理和(Erik Zürcher)、美國的高居翰 (James Cahill ),其著作均有中文版出版發行并曾產生廣泛影響,舍棄國人熟知的譯名不用而遵循 “洋化 ”的原則另行翻譯,比如將 “石泰安 ”改為 “羅爾夫 ·斯坦因 ”,會給讀者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其三,西人而取漢名,也是某種文化心理的反映。前輩漢學家如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 1865-1918)、羅樾(Max Loehr 1903-1988),所取漢名皆雅馴不俗;繼之活躍于國際學界的尉遲酣(Holmes Welch)、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諸人,聞其大名,即可知為“世外高人、學林泰斗 ”。從中西文化比較的角度而言,此類人名也有值得關注的特殊意義。
因此,翻譯西文文獻時,倘若見到一位專精 “中國學 ”的學者的名字,且慢,先查查此人是否有一個漢文的別名雅號。比如 Edward Schafer,漢名 “薛愛華 ”,貿然譯為 “愛德華 ·謝弗 ”,豈不辜負了人家 “熱愛中華 ”的一番美意?
西文文獻中出現中國人名、地名及其他專有名詞的音譯,其“回譯”更是一件不可馬虎的事情。欠缺知識而又疏于查證,固然是造成紕繆的主要原因,但下列幾條,似乎應該引起特別的注意:
(一)具有拉丁語源而為現代歐洲語言所承襲的漢文譯名
如 Confuci、Menci,分別是 “孔夫子 ”和“孟子 ”的拉丁語音譯,加上陽性名詞詞尾 -us是為適應拉丁語名詞變格的需要,如“孔門弟子 ”,譯為拉丁語應作 “discipulī Confuciī”,-us要變 -ī,否則該詞無法進入拉丁語的語言體系。若是將此類后綴與詞干連讀而一并加以音譯,則后果可想而知。
(二)拼寫錯誤及威氏拼音法
西方學者拼寫漢字讀音,多用英國人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首創的威氏拼音法(Wade-Giles Romanization),偶或采取國內通行的漢語拼音,一般不標四聲調號,拼寫亦難免小有差錯,如 Guchanwei quanyishu cunmu jieti,原為《古讖緯全佚書存目解題》音譯,因將 “Guchenwei”誤拼為 “Guchanwei”,故令人頗費猜測。至于采用威氏拼音法者,如 Tu-yang tsa-pien,即唐人蘇鶚所撰《杜陽雜編》; Chin-tai pi-shu,即明代毛晉所輯《津逮秘書》。
還有讀來十分拗口的 “Han-Chin chih chi shi chih hsin tzu-chüeh yü hsin ssu-chao”,應為《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音譯。諸如此類,不暇例舉。若有疑難,可參看威氏拼音與漢語拼音對照表,而諳熟漢文文獻篇目,所占便宜,自當不少。
(三)根據方言音譯的詞語
近譯德國漢學家雷德侯大作 “Some Taoist Elements in the Calligraphy of the Six Dynasties”(《六朝書法的道教因素》),參考文獻有: Henry Doré, Researches into Chinese Superstitions , 15vols, Shanghai: Tusewei, 1914。多方查證,才曉得 “Tusewei”為“土山灣 ”音譯,全稱當作 “Tusewei Press”,是上海徐家匯天主堂在清末民初開辦的出版機構,Henry Doré系供職于該教堂的一名法國傳教士,漢名 “祿是遒 ”,故上文應譯為:
祿是遒 ,《中國迷信研究》,十五卷本,上海,土山灣印書館一九一四年版。好一個 “Tusewei”,原來竟是吳語(上海話)的譯音。
五
在同一文本中使用多種語言,是西方現代文學興起之后出現的一種潮流。這種 “雜合文本 ”(hybrid text)對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都提出了全新的挑戰。同樣,歐美當代學術著作也存在顯著的 “多語現象 ”(multilingualism)。西方學者引用古希臘語、拉丁語的名言警句,往往直錄原文而不加翻譯,至于文中涉及不同語言的專名、術語,尤其是所列參考書目,照抄原文已經成為學界公認的通例。應對這一問題,除了必備的語言知識,了解相關學術背景至為重要。茲以西方漢學著作中常見的日文名詞為例,略述筆者對上述問題的認識。
西文文獻中出現日文名詞的羅馬字拼寫,在漢語譯文中例應轉寫為漢字。但是,由于日語漢字讀音自成體系,且一字多音現象較之漢語更為普遍,所以此項工作也頗為繁難。例如,在英語文獻中遇見一個日本人名 Seiichi Mizuno,應該如何轉寫為漢字? Mizuno為日本常見姓氏,應作 “水野 ”;但 Seiichi就有可能是 “誠一 ”“精一”“清一 ”,等等,“圣一 ”令人無所適從。唯一的辦法便是翻檢資料,查明了這位 “水野 ”先生的研究成果,例如他的代表作 Chūgoku no Bukkyō-Bijutsu,即《中國の仏教美術》(《中國佛教美術》),就可以得出明確結論:水野清一(一九○五至一九七一)。
類似的情況尚多,期刊名如 Hōun(《寶云》)、Gasetsu(《畫說》),文章篇目如 “Chōkin kainu hon nitsuite”(《關于 “張金界奴本 ”》),不諳日語漢字音、訓兩類讀法和日語羅馬字拼寫規則,自然無從措手;即使精通日語,對相關學術背景缺乏了解,照樣難以知其端底。
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翻譯界也有一句老話,說:“翻譯像女人,忠實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實。”其實,如果譯者具備較高文化素養又不憚費時勞力,“忠實 ”與“通達 ”并非不可兼得。劣質譯文,問題多多,但大而別之,不外三種弊病:一是沒有讀懂原文,理解偏差,表述錯誤;二是缺乏相關知識,措辭不當,有違學理;三是漢語表達能力有限,造語生硬,文義不通。常聽人說西方學術著作的漢譯本晦澀難讀,恐怕不是作者故作高深,而是譯者詞不達意。
時至今日,釋彥琮(五五七至六一○)論翻譯所謂 “不墜彼學 ”“不昧此文 ”,仍然值得從事翻譯的人士作為箴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