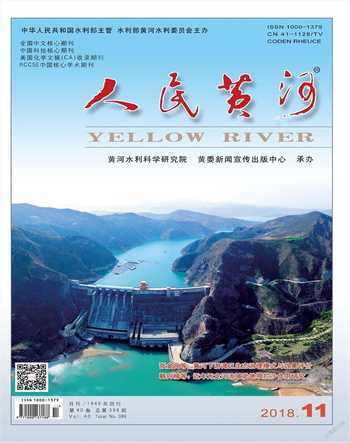小理河流域下墊面變化對產洪產沙的影響分析
狄艷艷 許坷艷 劉龍慶



摘要:分析了小理河李家河站1980年以來次洪水量、次洪沙量、徑流系數等要素的變化,并采用次洪對比分析法和統計法,對“20170726”與“19940810”兩場暴雨洪水以及歷史暴雨洪水進行了對比分析。結果表明:小理河流域經過多年的治理,下墊面條件改善,流域調蓄能力增強,在一般降雨條件下,減水減沙效果明顯;若遇類似2017年“7·26”那樣的大范圍強降雨,雖然削峰減沙作用明顯,但是仍可能產生較大洪水。
關鍵詞:暴雨洪水;流域調蓄;減水減沙;下墊面;小理河流域
中圖分類號:S157.1 文獻標志碼:A
1 流域概況
小理河發源于陜西省橫山縣艾好峁村,由西向東流經高鎮、水地灣、殿市等鄉鎮,在陜西省子洲縣殿市鎮李家河村匯入大理河,屬山溪性河流[1]。小理河全長69km,河道平均比降為0.55%,流域面積820.8km2,河網密度為0.116km/km2,流域不均勻系數為0.053,流域形狀系數為0.00312[2]。該流域屬大陸性季風氣候區,冬春干寒、雨量稀少,夏季炎熱、雨量較多且多為短歷時暴雨[3]。
小理河控制水文站為李家河站,控制面積為807km2,本文采用雨量資料涉及6個雨量站,分別為艾好峁、大路峁臺、高鎮、李家坬、石窯溝、李孝河,平均權重面積為134.5km2。站網分布見圖1。
2 歷史洪水分析
1980-2016年,李家河站洪峰流量大于200m3/s的洪水共有19場,20世紀80年代洪水最少(僅1989年發生一次,洪峰流量只有208m3/s);90年代發生洪水9次,占洪水總次數的47%;2000-2010年發生洪水7次,占洪水總次數的37%。
2.1 次洪水量和次洪沙量變化情況
按照面積包圍法計算次洪水量和沙量,19場洪水平均次洪水量為483萬m3,次洪沙量為348萬t。圖2和圖3分別為李家河站次洪水量、次洪沙量歷年變化情況,可以看出次洪水量和次洪沙量減少趨勢明顯,特別是2007年以來發生的5場洪水(編號為15~19),平均次洪水量和次洪沙量分別僅為231萬m3、150萬t。
2.2 徑流系數
徑流系數是指某一流域任意時段內的徑流深度(或徑流總量)與同時段內的降水深度(或降水總量)的比值。徑流系數反映在降水量中有多少水變成了徑流,也綜合反映流域內自然地理要素對徑流的影響,此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水利水保措施的有效攔蓄能力。徑流系數年際和年代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水利水保措施在減洪減沙方面的作用。
李家河站19場洪水中,次洪徑流系數變化范圍為0.04~0.30,平均為0.16,其中1995年洪水最大,為0.30,而2009年洪水最小,僅為0.04(見圖4)。從洪水分期來看,1980-1999年10次洪水的次洪徑流系數平均為0.18,2000年以來9次洪水的次洪徑流系數平均為0.12。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次洪水量、次洪沙量以及徑流系數的年代和年際變化均呈減小趨勢,說明小理河流域經過多年的治理,下墊面產流產沙條件發生了較大改變,特別是一般降雨情況下的減水減沙效果更為明顯。
3 洪水對比分析
通過次洪對比分析法,對次洪過程中降雨量、降雨強度、暴雨中心位置以及洪峰流量、次洪水量、最大含沙量、次洪輸沙量、次洪產流系數等要素的對比分析,也可發現下墊面變化及對刁、理河流域暴雨產洪產沙的影響。
3.1 “20170726”洪水與“19940810”洪水
2017年7月25-26日,小理河流域發生大范圍強降雨。受暴雨影響,李家河站發生洪峰流量為997m3/s的洪水,稱為“20170726”暴雨洪水,為1994年以來最大洪水。1994年8月10日,該流域也發生過一次暴雨洪水,稱為“19940810”暴雨洪水,洪峰流量為1310m3/s,為1980年以來最大洪水。
3.1.1 降雨方面
“20170726”暴雨的暴雨中心位于流域下游,降雨量大于100mm的籠罩面積約為450km2o其中李家河站累計降雨218.9mm、李家坬站218.4mm、李孝河站179.8mm,流域面平均降雨量118.0mm。主雨時段在26日0-2時,歷時2h,降雨強度達30mm/h。
“19940810”暴雨的暴雨中心位于流域中上游,降雨量大于100mm的籠罩面積約400km2,其中李家圾站累計降雨143.2mm、艾好峁站累計降雨139.3mm、高鎮站累計降雨116.3mm,流域面平均降雨量93.2mm。主雨歷時6h,降雨強度為10mm/h左右(見表1和圖5)。
總體來講,“20170726”暴雨與“19940810”暴雨相比,降雨量偏大約47.5%,暴雨強度更大,暴雨中心更靠近下游,在下墊面不變的情況下,更利于產洪產沙。
3.1.2 洪水方面
根據現有資料統計計算,“20170726”洪水和“19940810”洪水的特征值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20170726”洪水與"19940810"洪水相比,洪峰流量減小了23.9%,次洪水量增加了25%,最大含沙量減小了70.3%,次洪沙量減少了76.1%,產流系數略偏小。
從兩次雨洪過程線(見圖6)來看,“20170726”洪水和“19940810"洪水相比,雖然前者較后者降雨強度明顯偏大,而后者洪水過程線卻更為尖瘦,說明流域下墊面條件的變化影響了流域的調蓄作用。
通過對以上兩次洪水的降雨、降雨強度以及洪峰流量、次洪水量、最大含沙量、次洪沙量等特征值的對比分析不難發現,經過長期的流域治理,小理河流域下墊面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流域調蓄能力增強,減沙效果明顯,降雨的侵蝕能力減弱。在“20170726”暴雨這種強降雨情況下,雖然減水效果不甚明顯,卻削減了洪峰,特別是大大減少了次洪產沙量。
3.2 “20170726”洪水與與歷史洪水相比
應用統計法對“20170726”洪水與1980年以來19場洪峰流量大于200m3/s的洪水進行比較,結果同樣顯示次洪最大含沙量顯著減小,次洪產沙量明顯減少。
3.2.1 次洪最大含沙量變化情況
根據歷史資料統計,1980年以來的19次暴雨洪水過程中,李家河站最大含沙量一般都在400kg/m3以上,有的甚至超過800kg/m3,平均為732kg/m3。而“20170726”洪水中最大含沙量卻僅為260kg/m3,較歷次洪水平均最大含沙量偏小64.5%,明顯偏離平均情況(見圖7),說明流域產沙能力顯著降低。
3.2.2 次洪沙量變化情況
1980-2016年,李家河站歷次洪水的次洪水量與次洪沙量具有較好的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95。按此計算,“20170726”洪水次洪沙量應在1400萬t左右,而實際僅為366萬t,偏少70%以上(見圖8)。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小理河流域經過多年的治理,下墊面產流產沙條件有很大變化,即便在“20170726”暴雨這種強降雨情況下,由暴雨引起的產沙量也大幅減少,流域內土壤侵蝕程度明顯減輕。
4 結論
通過對小理河李家河站1980年以來次洪水量、次洪沙量、徑流系數等要素變化情況的分析,并將“20170726”暴雨洪水與“19940810”暴雨洪水以及歷史暴雨洪水對比分析,認為小理河流域經過多年的治理,下墊面條件改善,流域調蓄能力增強,在一般降雨條件下,減水減沙效果明顯。但是,若遇類似2017年“7·26”那樣的大范圍強降雨,則雖然削峰減沙作用明顯,但是仍可能產生較大洪水。建議進一步加強對黃河流域黃土高原地區下墊面變化條件下暴雨產洪產沙規律的分析。
參考文獻:
[1]許珂艷,王秀蘭.趙書華,等.小理河流域產匯流特征變化[J].水資源與水工程學報,2004,15(3):24-27.
[2]趙衛民,王慶齋,劉曉偉,等.黃河流域典型水文分區產流研究[M].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2006:77-78.
[3]史輔成,易元俊,高治定.黃河流域暴雨與洪水[M].鄭州:黃河水利出版社,199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