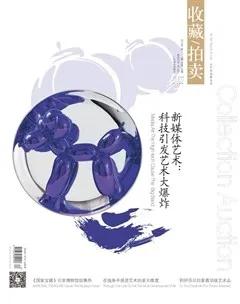對話學術圈:科技進步將把藝術帶向何方
雨葭
新媒體藝術已從肇始初期的單一發展向各領域逐漸蔓延,不斷介入到更多的空間創作與市場合作。在賦予藝術家更多表達和創作手法的同時,也在逐步刷新大眾對于藝術的理解和定義;另外,也為滿足整個市場對于藝術文化的不同需求,更緊密地與個人、企業、文娛、學術等大市場的不同板塊聯系在一起,提供更多的可能和價值。今次本刊對話學術圈內活躍于一線的藝術家、策展人,與他們一同觸碰新媒體藝術的邊界與未來。
車健全
視覺藝術家和策展人,現為廣州美術學院教授、天津美術學院特聘教授
管懷賓
中國美術學院教授、博士課程導師、跨媒體藝術學院院長
黃篤
策展人和評論家。任今日美術館學術總監,四川美術學院中國藝術社會學研究所和美術學系特聘教授
胡介鳴
當今中國數字媒體和錄像裝置的先驅藝術家之一,多次參加國內外當代藝術展覽
邱志杰
現為中央美術學院實驗藝術學院院長,教授,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教授。
(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名)
《收藏·拍賣》:新媒體藝術早已在各個藝術院校的教學體系中占據了席之地,但是大家對前衛的新媒體藝術的邊界限定卻依然不清晰。
車健全:新媒體藝術的特征就是每天都有新的可能發生,它是無法用概念來定義的,因為它可以與任何學科和領域相交的屬性決定了它可以有任何形態,并隨著技術的更新而更新。相較傳統意義的藝術門類的固化釋義和清晰的邊界,新媒體藝術自身的顛覆性和開放性決定了它有能力涵蓋世界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同時,場域和受眾的改變也在逐漸改變傳統空間對作品的約束,使它真正成為大眾化傳播的新型藝術方式。國內的新媒體藝術教學起步于10多年前,作為成長最快的專業,目前正在納入體制化的學科系統當中。
管懷賓:學科的跨界交叉和多媒體學術互動已成為當代藝術教育新的議題。在當代,新媒體藝術教育已經不只是個單純專業領域內部知識傳遞的問題,它與社會整體的意識形態、美學支撐及價值觀念的發展相關聯。一方面,當代媒體藝術教育既與傳統藝術學科之間,存在著根脈傳承上的關聯和不同的針對性,同時自身也交叉著各種新興媒體技術的實驗。另一方面,技術媒介迭代更新的周期短暫。所以,作為新媒體教育體系,如何通過基礎底盤設置,推進符合視覺藝術規律的系統建構,確立獨到的辦學思想與人才培養目標,它需要整體上的權衡與動態中的探索,否則很難通盤聚焦媒體藝術教育的實質性問題,也缺乏相應的社會性干預和參照系統。
黃篤:新媒體藝術是科技發展的必然結果。從媒介上看,傳統藝術如裝置、雕塑、繪畫等都是一種物質性的存在,而新媒體藝術更多是建立在數字化技術上的,非物質性的。在語言和呈現方式上,新媒體藝術更多是通過電腦、數字化來呈現,含有人工智能化的成分。新媒體一直在生長和變化,也許我們今天所說的新媒體過幾年就成了老媒體,技術在不斷進步,我們很難去把它固定化。但不管是傳統藝術還是新媒體藝術都離不開人,因為是人賦予它觀念、技術和美學,這個才是核心。
胡介鳴:新媒體藝術首先是在當代語境下的,當代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跨界融合的,學科門類之間是相互轉換,所以邊界就變得非常模糊,很難在學術上給它明確定位和界線。以前我把它定義為插電藝術,作品是需要供電的,其實這個定義是經不起追問的,表面上似乎順理成章的,但難道不插電的東西就沒有資格稱為新媒體了?現在的生物藝術、細胞基因工程都是非常新的領域,當把這個知識運用到藝術上面,未必是需要插電的。所以我認為去定義新媒體的邊界幾乎是不可能、徒勞的,因為它直在衍變當中。從藝術的價值評判來說,并不需要有這條邊界線。
邱志杰:“新媒體藝術”這個概念已經把藝術的可能性嚴重閹割,這是個妨礙了學科發展的過時的詞匯,應該盡快被拋棄。所謂的媒體藝術就是與傳播媒介有關的藝術,時代在變化,傳播的媒介也在發生改變。更早之前可能紙張本身就是種新媒體,因為紙張取代了石頭、布和竹簡;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電視攝像就是新媒體;而到了互聯網時代,網絡藝術就是新媒體藝術。一旦使用“媒體藝術”或“新媒體藝術”這樣的詞,所有人都會誤以為媒體藝術就是科技的全部,也會誤以為所有的科技創新都是圍繞著數字化和屏幕展開的。實際上,很大范圍的科技創新發生在生命工程、基因技術、納米技術等,包括地球科學、氣象科學等領域,這些都不是“媒體藝術”這個詞所能涵蓋的。堅持以“媒體藝術”來解釋些新現象,其實是種黔驢技窮的辦法。所以,我們在設置
個學科的時候要求這個學科要有充分的解釋力和廣闊的實踐空間。我更愿意用“科技藝術”來概括這正在展開的藝術類型。
《收藏·拍賣》:新媒體藝術往往與商業進行著各種混搭,也讓新媒體藝術創作的門檻變低,技術手法的同質性嚴重……究竟什么樣的新媒體創作才是值得在學術上進行研究和探討的?
車健全:炫酷和高科技一直以來是公眾對新媒體藝術的印象,沉浸、人機交互、觸摸和互動給參與者帶來強烈的體驗感。新媒體藝術雖然目前僅在當代藝術領域有所突破,未來的發展會遠遠超出當代藝術領域,我們很難估量它在不同學科和實用研究領域的深遠作用。如果把新媒體技術當作手段的話,重點是藝術家用它來干什么,是不是能夠更深入地探索人性以及我們知之甚少的世界,這是新媒體藝術的重點,否則就是好萊塢大片淺溥的感官刺激和催淚彈。
管懷賓:就中國美院跨媒體藝術學院而言,以學科交叉的形態,融通多個專業領域,形成了個集“媒體實驗、藝術創作、文化研究、策展實踐”為體的多維互動的教學格局。新媒體藝術與商業的結合,可以從媒體與技術、媒體與社會雙向推動當代藝術實驗性和跨媒介研究、跨領域實踐的發展。但深入探討“作為媒體的藝術”和“作為藝術的媒體”,進步解決技術語言與人文關懷的關系,建構理論研究、實踐創造新的先鋒性,也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問題。
黃篤:學術的開放性要求我們不能用老套的眼光去衡量新媒體藝術。藝術作品都和創作者的成長軌跡、生活經歷相關。20世紀50-70年代藝術家的作品,更有歷史感和批判性,而年輕代藝術家屬于快節奏的數字時代,他們的作品更強調視覺的沖擊感,這種變化和社會、科技的變化有很大的關系。我們要研究新媒體藝術作品的價值,必須要把它放在個大的結構里面去審視,要考慮它的創作者的經歷與時代背景,不能只說深度。
胡介鳴:“新媒體藝術”,新媒體是定語,主語是藝術。既然稱之為藝術,就應該用藝術的標準來評判它,創作元素是不能忽視的。很多藝術樣式都有這種情況,藝術家過于強調聲光電等手段的運用,就像傳統繪畫玩弄技巧樣,這些都是形式主義,可以追求,但形式和內容應該是個高度的統—體。技術不過是手段,重要的是創作者想要表達什么。如果你的酷炫視覺效果能觸及觀者的精神領域,喚起觀者情感上的些變化,它就是有價值的作品。如果達不到這種效果,視覺再炫酷,也是微不足道的。
邱志杰:科技藝術當然要密切地跟所有的科研機構、企業的需求去進行對接,才可能真正地服務社會,這樣才能用藝術思考來改造社會,要不然學院閉門造車,會被產業遠遠地甩在后頭。很多科技探索的先鋒其實是在企業的研究所展開的,一些創新型的企業到了定規模后,就會直接引領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我們勢必要對接社會企業的這種創新力。這個時候我們就科技藝術是否應該跟商業掛鉤展開討論,應該說是個毫無意義的問題。我并不認為今天所謂的“新媒體藝術”是眼花繚亂、層出不窮的。相反,我認為它大量的同質化,全息投影、3D、VR等手段都不夠富于想象力。那么在各種各樣的新媒體探索實踐中,每個藝術家會有不同的選擇,我個人傾向于反思這種技術論未來主義的態度。所有使用科技手段的藝術,最終還是要和那些原型性的命題掛鉤,才可能觸動人的心靈,否則就非常容易消費化和娛樂化。
《收藏·拍賣》:在新媒體藝術領域的日常研究上,哪些問題是我們應該留意或亟待解決的?
車健全:我的興趣是探究世界,聽上去像是科學家的工作,在不斷更新的技術背景下,藝術家和科學家的工作會越來越相似,只是路徑不同。我會根據不同的內容尋找不同的技術支持與合作。大腦和圖形的關系是我近期關注的主題,正在和斯坦福大學的相關機構合作。科學和藝術的關系變得前所未有的緊密,常常讓我想起文藝復興時代,充滿驚喜的跨界創造的時代。但是今天我們對技術的過度依賴又讓我懷疑,我們在科學至上的時代精神里面,忽略了技術帶來的副作用,這種副作用也具有前所未有的毀滅性,我們更需要能夠引領人類走向未來的新思想,而非被技術
黃篤:年輕代的作品更多是強調視覺的快感,就像玩技術活樣,缺乏人文、深刻的思想性、獨特的觀念,這也是新媒體普遍存在的問題。新媒體藝術不僅要有視覺的愉悅,更重要的是關注問題。尤其是我們今天說的當代藝術,如果沒有關注問題,當代藝術就沒有意義了,這個問題是討論藝術本體,還是觀念意義,還是社會上的問題,這都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胡介鳴:我們已經進入到數字化的時代,衣食住行都將新媒體化,它會帶來很多期待,也會產生很多問題,重要的是我們怎么去應對。我始終把新媒體當作藝術套了件華麗的外衣,藝術本體如何和這件衣服結合在體,才是我直想要追求的。在實踐當中,兩者有時候是對立的,有時候又可以找到共生的契機。
邱志杰:媒介材料、科學和生命技術給人類帶來了顛覆性的變化,這絕不僅僅是運用手段上的小小革新。就算不提生命工程或材料科學帶來的影響,僅僅就與IT有關的技術而言,我認為真正能夠帶來影響的會是人工智能,而不是AR、VR這些低級別或者新一代視頻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