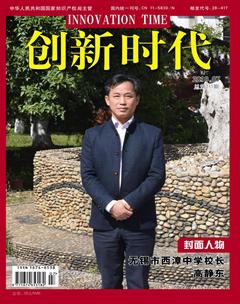王加寧:用微生物拆掉“化學炸彈”
唐鳳 仇夢斐 王晨
被稱為“工業血液”的石油是人類最重要的能源之一,但隨著越來越多油氣井的出現,土壤石油污染問題日益突出,這顆“化學定時炸彈”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環境問題。
而山東省科學院生態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王加寧帶領的“污染控制與環境修復”團隊另辟蹊徑,找到了拆掉這枚炸彈的“秘密武器”—愛吃石油的微生物。
世界難題
據了解,我國大慶、勝利、遼河和中原等油田數萬口油井附近100~200平方米的范圍內都看不到草木生長的痕跡。
“土壤被原油污染后就成了不毛之地,每開采40億噸原油,就有7%的原油流入周圍環境。”王加寧說。
而石油污染土壤修復既是油田環境保護的世界性瓶頸難題,也是衡量國家污染土壤治理技術水平的標志。
目前,石油土壤污染修復方法主要有3種—化學方法、物理方法和生物方法,通過物理方法或者化學方法處理后,土壤中微生物的生態受到嚴重破壞,土壤變成廢渣,難以根本解決問題。而利用微生物分解石油,不僅能修復污染,還能讓土壤更加肥沃。
生物修復作為土壤污染治理的主流技術,已經得到廣泛應用,但受限于石油類污染物的降解難度,一直還未形成工程化和實用化的石油污染土壤生物修復技術。
王加寧團隊從十幾年前就開始承擔國家“863”石油污染土壤生物修復課題。“難度在于石油成分很復雜,其中包括烷烴類的、芳香烴類的、石油里面的膠質和瀝青質。因為石油成分復雜,受污染土壤中可能存在幾百上千種化合物,一種方案很難修復。”他說。
因此,該項目技術攻關的難點之一就是不斷篩選,找到效果最好的菌群。“要篩出來一個菌劑最好的配方,可能得幾百上千次實驗。”王加寧說。
拆掉“炸彈”
2013年山東省科學院聘請了中科院沈陽應用生態研究所郭書海研究員作為學術帶頭人,成立了“污染控制與環境修復”創新團隊。數年來,他們經歷了不斷重復的實驗,針對烷烴、芳烴和膠質等石油組分的降解過程、強化機制及材料設備,開展了修復原理、工藝方法和技術工程化三方面的全鏈條創新,以電動協同、微生物包埋、生物增溶為增強手段,創建了石油污染土壤生物強化修復工程技術體系。“石油污染土壤生物修復工程技術體系構建及應用”成果榮獲2017年度山東省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
實際上,這些微生物就“生活”在油田附近。“油田周圍被污染的油泥地里生長著不少微生物。其中有一些依靠石油中的碳源生長,我們先挑選出‘飯量大的,然后進一步篩選論證,將它們制成菌劑。”王加寧說。
從上萬種菌群中發現適合細菌之后,研究人員還要找到最適合培養菌群的環境,然后投入模擬應用,再次不斷實驗。
最終,該團隊在石油污染土壤、采油產生的油泥砂、多環芳烴以及農藥污染場地及農業面源污染等領域的修復技術上取得了較大突破,在石油污染土壤修復技術方面,開發了耐鹽、耐低溫、耐高油污修復菌劑2個,結合生物強化、生物刺激、土壤改良等技術,在勝利油田建立了石油污染修復前、修復中和修復后的技術應用規范,填補了我國利用微生物—植物聯合修復石油污染土壤的空白。
落地生根
目前,該成果在勝利油田、遼河油田和吉林油田進行工程應用,累計處理石油污染土壤12萬噸,消減了生態脆弱區環境風險,取得經濟效益1.43億元,解決了長期困擾我國油田區石油污染土壤修復的工程技術難題,主要成果入選《2016年國家重點環境保護實用技術》。
例如,勝利油田金島實業有限責任公司利用該項目研發的生物及強化修復技術,自2014年1月至2016年11月針對勝利油田孤島采油廠、樁西采油廠、河口采油廠等多個采油廠周邊的石油污染土壤和采油過程中產生的10.4萬噸含油污泥進行了修復工程應用。經過12個月的修復周期后,土壤中石油污染物濃度降低73%,修復后的土壤達到了農田的使用標準。
現在,在勝利油田附近的實驗田,油污地開始有了生機,實驗棚里的植物已經生長得郁郁蔥蔥。
“新舊動能轉換每個產業都離不開環保,之所以叫舊動能,就是因為能耗高、效率低、污染重,從這個角度理解,動能轉換的最終問題還是環保問題,新舊動能轉換名單里的十大產業沒有把環保單獨拿出來作為一個產業,但每個產業都必須把環保、生態放在首位,而對關停企業的治理就更離不開環保技術了。”王加寧說。
此外,團隊先后與烏克蘭、俄羅斯、美國、澳大利亞、愛爾蘭、西班牙等國的相關大學、科研院所及企業建立了國際合作關系,在環保、高效石油吸附材料的研制以及關鍵技術引進及應用領域,開展聯合研究,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與產品,推動了我國石油污染控制及修復領域的技術進步。
(本文轉自《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