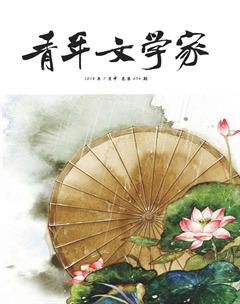楊德昌電影中的后殖民景觀
摘 要:楊德昌是上世紀(jì)八十年代臺(tái)灣“新電影運(yùn)動(dòng)”的旗手,被譽(yù)為九十年代最具影響力的臺(tái)灣電影導(dǎo)演之一。他用自己準(zhǔn)確的鏡頭記錄了臺(tái)灣近代社會(huì)的歷史變遷。這種變遷中包含著社會(huì)的復(fù)雜性和日殖后的殖民記憶,在本土與他者、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殖民文化潛移默化中對(duì)臺(tái)灣電影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
關(guān)鍵詞:楊德昌電影;后殖民主義;文化霸權(quán)
作者簡(jiǎn)介:王倩(1992.8-),女,漢族,山東省日照市人,現(xiàn)就讀于河北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2016級(jí)戲劇與影視學(xué)專業(yè),主要研究方向:影視藝術(shù)與文化批評(píng)。
[中圖分類號(hào)]:J9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18)-20--01
在臺(tái)灣被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五十年里,殖民母文化已經(jīng)滲透到臺(tái)灣的科技、經(jīng)濟(jì)、文化、社會(huì)中,臺(tái)灣電影作為文化的一種,也總在有意或無(wú)意的敘述、強(qiáng)調(diào)、表現(xiàn)“后殖民”這一敘事主題。在社會(huì)大背景下,楊德昌電影也呈現(xiàn)出一種獨(dú)特的后殖民景觀。
一、道具作為符號(hào):武士刀中的殖民意圖
道具作為電影創(chuàng)作者的一種主觀選擇,往往都附帶著導(dǎo)演濃烈的個(gè)人主觀意識(shí)。《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不論是小四住的房屋還是小馬、小貓王的家,都是日式風(fēng)格建筑。這些日殖侵略時(shí)期遺留的房屋,作為半永久性產(chǎn)品,它們記錄著殖民母文化的侵略。在這些住房里,有很多日本人撤離臺(tái)灣時(shí)并未帶走的遺留物,它們影響著臺(tái)灣普通民眾的生活。像小貓王,從家里的屋檐橫梁上翻出了一把武士短刀。新轉(zhuǎn)學(xué)來(lái)的小馬,父親是位將軍,家室顯赫的他在閣樓里翻到了一把制作精美的日本武士刀,傳言他曾用這把武士刀殺過(guò)人,所以大家很忌憚他。
不論是小貓王翻出的武士短刀還是小馬翻出的武士刀,作為道具的它們,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小馬,因?yàn)槲涫康秱餮允顾麚碛兄约翰豢珊硠?dòng)的地位,小馬和小馬背后的武士刀象征著一種暴力的勝利。臺(tái)灣歷史上的腥風(fēng)血雨已經(jīng)模糊了臺(tái)灣社會(huì)的道德觀,對(duì)日本武士道暴力精神的曖昧,使之成為了青少年之間所推崇的一種精神,在這種精神的推動(dòng)下,小四偷取了小貓王家里的武士短刀,最終刺進(jìn)了小明的身體,這也暗示出臺(tái)灣少年處在麻木不仁、冷漠殘忍的社會(huì)大環(huán)境下做出的犧牲。
二、語(yǔ)言作為工具:文化侵略的遺留
語(yǔ)言作為信息交流的渠道,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內(nèi)涵,同時(shí)也顯示出被殖民對(duì)于宗主國(guó)文化認(rèn)同的態(tài)度。在楊德昌的電影中有普通話、閩南語(yǔ)、粵語(yǔ)、日語(yǔ)、英語(yǔ)等,多種語(yǔ)言相互交織在一起,呈現(xiàn)出語(yǔ)言多元化狀態(tài)。但影片中對(duì)于日語(yǔ)的運(yùn)用,毫無(wú)疑問(wèn)也在說(shuō)明著一個(gè)事實(shí):在日本統(tǒng)治臺(tái)灣的五十年里,日語(yǔ)在臺(tái)灣社會(huì)文化中的滲透,其根蒂無(wú)法輕易拔出。
《青梅竹馬》里的阿隆是一個(gè)保守傳統(tǒng)的人,他最喜歡去日式卡啦OK屋,整墻的日式歌曲磁帶,舊式的放片機(jī),優(yōu)美的日本歌曲,讓人們看到了那個(gè)時(shí)期臺(tái)灣社會(huì)的娛樂(lè)文化環(huán)境。日式卡啦OK屋,對(duì)于阿隆和他的朋友們來(lái)說(shuō),是放松心情、尋找感情釋放的港灣。《一一》里的日本人大田在酒吧高歌一首日文歌曲時(shí),旁邊的聽(tīng)眾都能用流利的日語(yǔ)來(lái)合唱,酒吧的氣氛也因?yàn)檫@首歌變得火熱。這些細(xì)節(jié)的呈現(xiàn),都說(shuō)明了臺(tái)灣大眾對(duì)日語(yǔ)的熟悉程度和對(duì)日本歌曲的喜愛(ài)。即使日本殖民者已經(jīng)撤離臺(tái)灣,但日殖時(shí)期所留下的語(yǔ)言、文化還是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經(jīng)歷過(guò)這一時(shí)期的民眾,他們身上印刻著的歲月痕跡,無(wú)法消解,他們的存在也時(shí)時(shí)刻刻提醒、警惕著民眾后殖民時(shí)代的文化霸權(quán)。
三、情感依附:日本人智者啟蒙形象
在臺(tái)灣電影里對(duì)日本人的身份設(shè)置似乎暗示著他們來(lái)臺(tái)灣的目的好像是教化民眾,作為智者啟蒙的形象構(gòu)建民眾的心智的同時(shí),成為臺(tái)灣人的精神寄托和情感依靠。在《一一》中,大田作為NJ公司邀請(qǐng)的生意伙伴,他認(rèn)真嚴(yán)謹(jǐn),十分直率誠(chéng)實(shí),大田的出現(xiàn)不僅是公司的指路者,更是NJ的情感歸屬。這位人到中年的中產(chǎn)階級(jí)男性NJ,通過(guò)一次“日本之旅”,重溫了自己的初戀時(shí)光,獲得了新的生活動(dòng)力。在這次“心靈朝圣之旅”中,日本不僅是他慰藉心靈鄉(xiāng)愁之地,跟大田的交流更是解開(kāi)了他多年的心結(jié)。大田就像上帝一樣,對(duì)于一切了如指掌,又適時(shí)引導(dǎo)。不論是《一一》中擔(dān)負(fù)智者啟蒙的大田,《海灘一天》中傳言逃到日本的德偉,還是《青梅竹馬》里在日本生活的阿娟,都在無(wú)形之中告訴人們,殖民地經(jīng)驗(yàn)依然在影響著臺(tái)灣大眾的日常生活、文化想象。
結(jié)語(yǔ):
殖民者的離去并不是殖民歷史的終結(jié)。在經(jīng)受長(zhǎng)久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殖民過(guò)程之后,殖民主義文化已經(jīng)成為被殖民者的集體無(wú)意識(shí),他們總在無(wú)意中認(rèn)同于殖民者的身份、思想,楊德昌電影中就向人們呈現(xiàn)出了大量的后殖民景觀。電影中不同風(fēng)格的日式建筑、說(shuō)著流利日語(yǔ)的阿隆、唱著日式歌曲的普通民眾、從居住的日式建筑里翻出的武士刀、代表日本文化的插花和茶道,還有遵循日式禮儀的長(zhǎng)輩、日式風(fēng)格的屏風(fēng)花瓶、日本人的智者啟蒙形象、日本是電影主人公的心靈歸宿等等,它們的存在都在說(shuō)明著臺(tái)灣社會(huì)對(duì)于殖民國(guó)母不僅是文化的依賴,更是一直精神上的依賴,殖民地成為了被殖民一個(gè)心靈歸宿的港灣。這種混亂的現(xiàn)象也正表明著臺(tái)灣民眾對(duì)于自身身份認(rèn)同的缺失和迷惘。
參考文獻(xiàn):
[1](美)約翰·安德森.楊德昌[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4.
[2]劉翠霞. 從殖民記憶到后殖民想象——臺(tái)灣電影中的“日本書(shū)寫(xiě)”[J].社會(huì)科學(xué),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