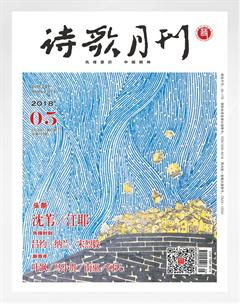主編薦語
這期選擇推出沈葦的詩和江耶的組詩《淮河》,這一南一北兩位詩人的詩風迥異,當然,我們的根本用意并不是為展示他們的不同詩風,我們的真正用旨是讓讀者體味他倆是如何寫好自己熟悉的地域里的物象背后情境和人們心中的情懷的。
沈葦反對用地域來劃定文學,他說這是評論家在偷懶,或是作家自我的矮化,但他擁躉對自己“兩個故鄉”——江南和西域的“綜合抒情”的認定。這次選他的詩時,我們也是特意選他寫的“兩個故鄉”的詩,譬如“烏鎮”“德清散章”和“喀拉峻歌謠”,以及他的阜康、苗寨、西樵山等,在這些詩行里,詩人總是用深情的、熾熱的赤子之心來傾述自己的永恒之愛和永遠的忠誠。同時,他也用思辨的哲思,打量他的地域變化進程中的一切傳統美好的流失之無奈和警覺,對親情在時光飛逝里的遠去的珍惜和哀挽。他吟唱道:“如果逝去歲月變成一種貼身的暖/我愿放棄天山上的瑤池彩虹”;他傾述道:“我有一部沙漠的沉思錄/你有一冊海邊的祈禱書/合上,便是言辭的沉默/打開,即為時空的蒼茫”。詩人的地域之思已經上升為對宇宙、對人生的哲學思緒。
江耶這組《淮河》,是為我國“四瀆”之一淮河寫照的。淮河流經千里,作為詩人精神中不可缺失的母親河,他為她寫了詩傳,寫出了她前世今身,寫盡了她的悲情和苦難,以及一條河流與兩岸人們之間千絲萬縷的生活上、文化上、精神上的聯系和糾纏。尤其是當下的淮河與人們的關系,他在努力地用詩行為這條大河雕像,這個地域自然給他的豐厚博大的內涵和資源,是詩人創作的“富礦”,一條古老而又年輕的大河和千里平原上的蒼生萬物,夠他挖掘開采寶藏的還有很多很多,我們期待著詩人的更多詩性表達。
米沃什曾說過:“我到過許多城市,許多國家,但沒有養成世界主義的習慣,相反,我保持著一個小地方人的謹慎。”當好,”J、地方人”,寫好,”J、地方”,我認為,是每位作家詩人都要遵循的創作規律。福克納寫“自己那像郵票大小的家鄉”,也是一個佐證。讓我們從沈葦和江耶的創作經驗里悟出點什么……
——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