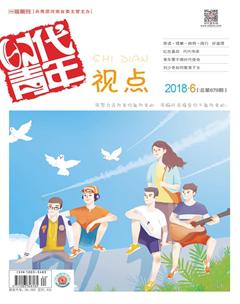從“東北易幟”前后析張學良的政治才干
鄭毅
摘要:1928年對東北奉系軍閥而言,是決定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在此危難關頭,少帥張學良展現出一個優秀政治家的政治才干,一方面成功團結奉軍上下,避免了分裂;另一方面,則積極展開與南京國民政府的“易幟”談判,對日本則采取隱忍與決絕的兩手外交策略,最終實現“東北易幟”,國家統一的夙愿。
關鍵詞:張學良;奉系;東北;日本;蔣介石
1928年,少帥張學良展現出一個優秀政治家的政治才干,一方面成功統一奉軍上下,避免了分裂。另一方面,則積極展開與南京國民政府的議和談判,對日本則采取隱忍與決絕的兩手策略,最終實現“東北易幟”,國家統一的夙愿。張學良將軍在“東北易幟”前后的政治表現,無疑是值得稱道的。
一、以“寬忍”為用——張學良團結奉軍上下的政治努力
1928年,張作霖被被日本人炸死。張的暴亡使得東北軍突然失去主心骨,而奉軍主力還在關外,東北內部空虛,日本隨時有可能發難。這個時候,奉軍上下沒有慌亂,反而以協助張學良返沈為中心任務,展開了秘密行動。少帥張學良與楊宇霆決定,由張學良本人立即返回奉天主持大局,楊宇霆繼續留在關內,指揮撤軍事宜。
1928年6月1 8日,張學良返回沈陽,19日正式就職東北保安委員會委員長。這期間,由于不知道張作霖的生死,日本未敢輕舉妄動,實現更大的陰謀。可以說,正是張學良等人臨危不亂,精心籌謀的安排,奉軍上下度過了最初的難關。
對于東北軍內部的山頭斗爭,張學良本人是清楚的,老將張作相德高望重,巨頭楊宇霆雖然才能卓著,但為人驕橫跋扈,如何對待這些“老前輩”,是實現張學良“東北易幟”的關鍵。張學良采取依靠基本盤,爭取“老前輩”,以“寬忍”為用的策略。
張學良恭請張作相出任東北保安部隊總司令,對此,張作相拒絕接受這一職務,反而發誓輔佐支持張學良。不久,楊宇霆也發來通典擁立“漢帥”張學良。這樣,奉系內部各個山頭都統一到張學良旗下,1928年7月1日,張學良正式就任東北保安總司令,同時兼任東北大學校長。開始了統治東北的少帥時代。日本妄圖分裂奉系,進而吞并東北的野心也暫時破滅。
二、“曲折往來”——對南京政府談判的“義利并重”
1928年7月1日,少帥正式致電國民黨,表示愿順從民意,實現國家統一,并派代表赴北京談判。談判的焦點在熱河的歸宿問題上,熱河作為東北的門戶,關系東北的安危,因此,張學良志在必守。而南京政府對此則采取,一邊答應張學良的全部條件,要少帥立即“易幟”,雙方初步商定7月下旬舉行“易幟”;另一方面,蔣介石又積極調兵遣將,向熱河進軍。
就在此時,日本方面對張學良將軍施加了壓力,7月13日,日本駐沈陽總領事林久治郎秉承田中首相的旨意,拜會了張學良,提出了日本的警告。在內外壓力下,張學良授意湯玉麟7月19日宣布熱河易幟,但東三省全部易幟時間延后。少帥企圖是用熱河“易幟”,打掉蔣介石武力攻占熱河的圖謀。
張學良一再延期易幟,并沒有迫使蔣介石在熱河問題上讓步,他拒絕了張所提停止熱河軍事行動的請求,指示白崇禧:“前方部隊中止前進的底線,是張學良讓出熱河。”。雙方你來我往,進行了艱苦的拉鋸談判,“東北易幟”的時間也一拖再拖,直到1928年10月,國民黨方面才最終同意了東北方面的“易幟”條件,其中核心的熱河省正式劃歸張學良管轄,成為東北第四個省。這樣,少帥張學良既實現了國家統一的大目標,繼而又實現了掌控東北的區域小目標。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勝利,少帥在東北的地位由此得以鞏固。
筆者以為,談及歷史事件,決不能脫離該事件所處的歷史時代背景。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處于軍閥割據混戰的背景下,張學良將軍首先是一位愛國的、擁護國家統一的政治家;這毋庸置疑。其次,他也是奉系軍閥的首領,是一派地方軍政集團的代言人。因此,他所作的任何決定,必然帶有二者共同的利益交集。在堅持國家統一的基本立場不變的前提下,積極擴大奉系集團的利益,因為這不但是張學良將軍本人的訴求,也是奉系軍閥集團上下的共同追求。如果不能有效的維護集團利益,張學良下臺也是必然的。正如以“江浙財團和黃埔軍校”為基礎的蔣介石集團,山西閻錫山集團、廣西白崇禧集團等等,都是國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交集追求者。因此,在“東北易幟”問題上,張學良積極追求奉系集團的利益,無可厚非。
三、“軟磨硬頂”——張學良對日外交的兩手策略
“東北易幟”必然面臨日本的激烈干涉,這是張學良將軍意料之中的事情。日本處心積慮、苦心經營扶持奉系軍閥,是絕不會甘心將即將到手的肥肉吐出來的。“在皇姑屯炸車案發生前的5月末,日本既已由朝鮮調來一個旅團到東北,加上關東軍原有第14師團的所有兵力全部集中奉天業已一月有余。張學良暫時放下了父仇,對日本選擇了隱忍不發的“韜晦”路線。1928年7月19日,日本駐沈陽總領事林久治郎拜會張學良,進行威脅恐嚇。張學良采取拖延敷衍的策略,告知林,如果違背東北民意,“他本人必將陷入困窘地步,甚至被迫辭職。”8月4日,日本前駐華公使林權助作為田中以首相特使身份,前往沈陽與張學良會面交涉“東北易幟”問題,其態度之蠻橫,氣焰之囂張,至今讀來都令人憤慨。他對張學良強調,日本在滿蒙有特殊利益。張學良仔細耐心的聽他講完后,向他解釋,尊重日本人的“勸告”,但決不能因此違背東三省人民求統一的愿望和意志。林權助當即發飆,大聲嚷叫,日本已經下定決心,即便冒干涉中國內政的嫌疑,也在所不惜。少帥聽罷,勃然變色,這時日方的一位代表又進一步恐嚇,日本將不惜在東北使用武力。張學良強硬回應:“絕不做違背中國人民意愿的事。”
面對日本的威逼恐嚇,少帥悲憤交加,背地里潸然淚下。但為了東北安危,只能延期“易幟”。張學良認為日方所說“如不聽我方之勸告,即訴諸武力”,確非空言恫嚇,必須進行斟酌。即“不給政友會的田中義一首相以‘軍事介入東北的機會,來轉移民政黨等的攻擊,延長其政治口實的政治判斷。”
果然,不出少帥的預料,田中內閣對華的蠻橫態度,在國內外激起了強烈的反響。不僅重新引起了遍及中國的經濟抵制,“抵制日貨運動一浪高過一浪,日中貿易持續萎縮,沉重打擊了日本的經濟擴張。”同時也引起其他列強的疑慮。與此同時,日本國內政治反對派也對田中內閣展開猛烈攻擊。
面對國內國際一片抗議浪潮,田中內閣被徹底孤立。于是被迫調整對華政策。正是在這種內外有利的環境下,10月12日,少帥正式宣布東北易幟。
結論
東北易幟后,日本帝國主義并未放棄侵略東北的野心,隨后向東北當局提出鐵路交涉問題,少帥對此胸有成竹,以東北外交問題蓋由中央全權負責,地方當局無權過問,加以巧妙推脫。日本當局對此無可奈何。“楊常事變”的爆發,體現了少帥“寬忍”性格的另一面——“決絕”。通過霹靂手段,迅速解除了東北當局的內患,不失為高明。這種性格在后來的“西安事變”中,也表現的淋漓盡致。“中東路事件”固然被評論為“無故挑釁,又無故投降,辱國喪權,莫此為甚,國際地位即從此降落。”,筆者卻認為,張學良將軍力爭收回東北權益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對于雙方實力的誤判,過不在少帥,日本在二戰中也是經過了“張鼓峰”等系列事件,才確認了蘇聯的真正實力,從“北上”戰略改為“南下”戰略。而少帥在戰敗后,跳過中央,立即展開對蘇談判,力爭彌補損失,也是其靈活外交的體現。
對于“九一八”事變的責任,筆者以為,其根源還是當時軍閥割據這個大的歷史背景造成的。以史明鑒,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這是中國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任何時候強調這一點都是不為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