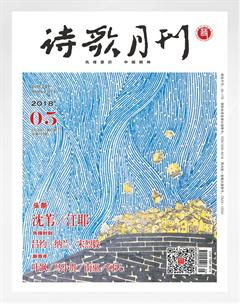生活、生命與詩
葉青青
1
詩,蘊藏在生活的礦藏中,因而,詩是生活本質的凝練與濃縮。
我們不否認詩人個人的認識、才能與技巧在創作實踐中的作用,但是豐厚的生活基礎乃是創作的源泉,離開了生活的土壤,即使你有再出眾的才智和純熟的寫作技巧,也無法寫出生活的詩意。
羅丹曾說“美是到處都有的,對于我們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其實美就是詩意,生活中無處不充滿著詩意,只是需要詩人去發現。《獨居》就是詩人的發現,是詩人謝克強撥開遮蔽,在簡單孤寂的生活中發現詩意。本是與電視機、書柜里的書毗鄰而居,但詩人卻“將心匍匐下來/在汗水浸泡的深處開采詞語/用凋落的月光喂養詩意/或者將眼睛嫁給書”。而“墻上那支蘆笛/甘愿沉默/(它曾奏過好多動情的曲子)/想以此來肯定自己”。
《獨居》以沉實的力量和充盈的詩意,不僅為我們提供了詩意的情感,更是對塵世、對生命本質的思索。可見,詩是理解生活的感官,詩人是洞察生活意義的目擊者。
2
“詩人是懷著痛苦身不由己地燃燒自己并燃燒別人的”托爾斯泰語)。
詩人只有自己燃燒,他在詩中蘊藏或輻射出的光熱,才能使讀者燃燒,使讀者心中產生光和熱。這不“那些積攢淤積的孤獨/常被月光翻譯著時不時/肆意折磨著我那時/我就懷抱瘦骨沉人生存深處/用孤獨與寂寞淘洗詞語/讓思想開花”(《活著》)。
“讓思想開花”,便是詩人懷著痛苦燃燒自己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痛苦已成為檢驗詩人良心是否醒著的唯一標準。
3
“昨日稿紙上打的草稿/修改了一次又修改了一次/我仍找不到感覺/幸好這陡來的一場雪/掩埋了稿紙上的那些/蒼白棋鐺的文字”(《踏雪》)。
這首詩的價值,不在于對事物所作的本質挖掘或寓意的發現,而在于詩人獨特的感悟。“幸好這陡來的一場雪/掩埋了稿紙上的那些/蒼白屏孱的文字”。陡來的一場雪,本來掩埋的是腳下的土地,詩人卻說掩埋了稿紙上那些蒼白孱弱的文字,就是詩人獨特的感受。詩是以詩人獨特的感受為生命的,詩人不是通過對審美對象的“知”與“不知”而產生詩的,而是通過對審美對象發生某些獨特感受激發了胸中的詩情才有詩的,而這種感受的獨特與深刻,常常帶來藝術構思的獨特與深刻,沒有前者,后者就是無源之水。
藝術感受,換言之,也就是對生活進行藝術認識、藝術體驗和藝術發現。
4
獨特的藝術感受來自哪里?或者說詩人的靈感來自哪里?我以為來自對生活熟悉的程度。詩也如其他文學作品一樣源于生活,但決不是生活的翻版,而是生活的升華,猶如酒釀自糧食,蜂蜜釀自花粉一樣,是生活本質的凝練與濃縮,是詩化了的藝術。不可否認,詩人個人的資質、才能與技巧在創作實踐中的作用,但是離開生活的土壤,即使再聰慧、再有才能、再有熟練的寫作技巧,也無法創作出好的詩歌作品。從這個意義上,與其說詩人在某個時刻有了寫作欲望,還不如說詩人是為生活的魅力所吸引、所激動。
朋友送來一部詩集,作者閱讀的感覺竟是“待等我的目光穿過迷宮/心卻沒有醒來/無疑我的目光與思緒/迷惘在你精心制造的/一片暈眩中”。“合上你精裝的詩集/我欲瀟灑地吮吸一口香煙/……扔煙的動作很隨意/卻斷然結束了/一種意義的存在”(《讀某君詩集》)。
如果只注意對生活現象的描寫和表現,詩的力度發揮就有限,詩人謝克強不滿足于此,而是希望對生活有更深層的發掘和表現,形象地理解世界或者借助于形象向人們解說世界。這是因為詩歌是“對不可表達之物的表達”(馬拉美語),正因為如此,作者才調動自己的想象,借來一支熄滅的煙頭,并用一個扔煙的動作,形象而生動地暗示更豐富、更深刻的言外之意。
5
詩人沒有想象,就像鳥兒沒有翅膀,他的詩思就不會在藝術的天空里自由地翱翔。
什么是想象呢?“想象為從來沒有人知道的東西構成形體,使虛無縹緲的東西有了確切的寄寓與名目。”(莎士比亞語)。因此,想象,奇特的想象,是賴以創造奇特形象的酵母。正如赫斯列特所說:“想象是這樣一種機能,它不按事物的本相表現事物,而是按照其他的思想情緒把事物揉成無窮的不同形態和力量綜合來表現它們。”
謝克強的想象是豐富、新奇,甚至是獨創的。“想象填不滿六平方米的居室/羽化成蝶/落在窗臺的塑料花上/討論詩與意象”(《獨居》),在這里,詩人詩緒抽象的想象,竟具象羽化成蝶,與窗臺上的塑料花討論詩與意象。在這里,蝶與塑料花,不僅是詩人想象的具象,更是詩人經心營造的意象。
詩人之所以要千方百計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就在于要從客觀事物上發掘出隱藏的不易發現的也不易道破的藝術效果。
6
生活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為詩人提供寫之不盡的素材,使之從生命的潮汐中淘洗詩歌高貴閃光的金子,而這對詩人來說則是身心俱焚的煎熬。
“當然最想偷的/還是生活中彌漫的詩意……/如果所有這些都偷不了/那就偷一個繽紛的夢”(《偷生》)。在生活中,人們總是向往著美好的生活,尤其是在生活不如意時,這種向往更加強烈。這不,當霧霾、污染、混沌充斥在空氣中,詩人竟異想天開地在仿徨與痛苦中,用“偷”的方式向往鳥鳴、溪水、花姿,不僅如此,還要偷一部《論語》,以營養人生。一個“偷”字,道盡了詩人的向往與期待。
正是這種向往與期待,無疑成了詩人的一種理念、一種信仰、一種超越此在的烏托邦幻夢。然而,理想畢竟只是理想,當詩人開始將一種理念和信仰轉移為世俗的感動時,雖然也為一種博大、崇高的東西所懾服,但觸目所及,卻讓詩人的向往與期待變得更為豐富與深刻。
這首詩在構思時、著筆時也有自己獨特的東西,那就是在尋找矛盾,即捕捉心靈與心靈的撞擊,或者說情緒與情緒的摩擦,并在撞擊與摩擦處著筆,使其進出思想的火光,同時產生一種強烈反差的藝術效果,讓詩不僅更具表現力,也有了力度與深度。
7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軾這首富有哲理的詩,讀后給人很多啟示,啟示之一就是觀察事物的角度。
在客觀現實生活中,無論哪一種事物,它總是呈現出多側面的美。這種多側面的美既是客觀存在,也是詩人能動的創造。因此,詩人的藝術本領就看他是否能選擇獨特的視角去發現事物獨特的美。正如詩人萊辛所說:“詩所選擇的那一種特征應該能使人從詩所用的那個角度,看到那一物體的最生動的感性形象。”
詩人自嘲自己,“一種錐心的隱痛/漣漪一樣在心里擴散/周身奔騰的血頃刻間/在巨大的郁悶中沉默/失去了溫度”(《自嘲》)。本應是自言自語的獨白,然而,詩人卻以掛歷上的妙齡女郎的視角,朝“我”嫵媚地笑著。正是妙齡女郎嫵媚地笑著,讓與“我”不想說話的杯子、拒絕下水的筆,還有一種錐心的隱痛,一時間都生動起來,有了生命與活力。其原因就是有掛歷上的妙齡女郎朝“我”嫵媚地笑著這個獨特的視角。如果這首詩沒有妙齡女郎朝“我”嫵媚地笑著,這首詩恐怕要遜色許多。
所以我向來認為題材是否重要不要緊,要緊的是取材的角度。
8
寫詩是一件苦樂參半的艱辛的勞作。苦在其表,在詩人的生存狀態和物質利益;樂在其中,在詩人內心寄居的伊甸園,在靈魂放牧的廣闊時空。
《獨居》應該說將詩人這種苦樂參半的艱辛勞作表現得淋漓盡致。“看見墻角自己瘦削的影子/寂寞與孤獨常在這時襲來/偷偷淹沒我”,“我把孤獨吐成一縷縷瀟灑/然后漫不經心/數著雜亂的胡子”。
寫作的個人化,使得詩歌更強調獨特的個體生命體驗。與以往詩歌寫作的工具化、公共化不同,如今詩歌寫作越來越變成一件純粹個人的事情,一種僅僅聽從內心召喚從而抵達人性深處的寫作,詩成了生命存在的方式。個人化的基本內涵是不可通約的個體生命體驗、具有個人特質的經驗轉化方式、個人獨特的話語方式。其根本的含義在于提醒詩人回到自己的經驗世界中去——只有個人的經驗對于詩才是有意義的。詩人只有從自己個體的生存經驗出發,堅守個人精神獨立的寫作姿態和價值立場,才會對生活進行個人化的觀照。
社會生活或社會生存狀態有時代的、共性的一面,但詩人觀察、體驗、把握生活的視角以及其中的生命體驗和表達的話語方式,無疑都是極具個人化的。正因為如此,才會暗示出生活內部的某種精神秘密,也使一個詩人內心的體悟擁有區別他人的重量和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