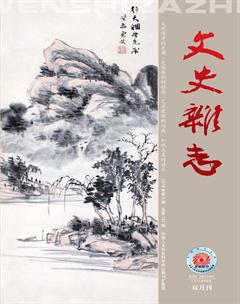為什么會(huì)有反《詩(shī)序》論爭(zhēng)
聞衷
《詩(shī)序》為《毛詩(shī)序》的簡(jiǎn)稱,系東漢流行的古文《毛詩(shī)》所傳。在《詩(shī)經(jīng)》研究中,歷來(lái)重視對(duì)《詩(shī)序》旨義以及《詩(shī)序》作者、《詩(shī)序》劃分問(wèn)題的探討,由此形成的觀點(diǎn)則互相抵牾,壁壘分明,從而在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上形成一場(chǎng)延綿一千八百余年,且頗為壯觀的反《詩(shī)序》論爭(zhēng)。
要弄清歷史上反《詩(shī)序》論爭(zhēng)的緣起及其意義,就首先有必要了解《詩(shī)經(jīng)》學(xué)界對(duì)《詩(shī)序》劃分問(wèn)題與作者問(wèn)題的論爭(zhēng);特別是《詩(shī)序》作者問(wèn)題是和尊《詩(shī)序》與反《詩(shī)序》論爭(zhēng)密切相關(guān)的。
一、《關(guān)雎》之前是《大序》還是《小序》?
對(duì)于《詩(shī)序》,歷來(lái)都分作《大序》《小序》的,并且均比較一致地認(rèn)為,列在各詩(shī)之前,解釋各篇主題的一小段文字(即一般所說(shuō)的“題解”)為《小序》,至于《大序》則位處《詩(shī)經(jīng)》開(kāi)篇《關(guān)雎》詩(shī)之前,以總說(shuō)全《詩(shī)》主旨。而所謂《詩(shī)序》的劃分問(wèn)題便恰恰出在這里:既然大家都說(shuō)各詩(shī)之前均為《小序》,那么,《關(guān)雎》之前有沒(méi)有《小序》?如果有,它與總領(lǐng)全《詩(shī)》的《大序》又如何區(qū)別?
這個(gè)問(wèn)題,歷來(lái)大體有兩種說(shuō)法。第一種說(shuō)法講,《關(guān)雎》之前的那一大段文字就是《大序》;至于《小序》,則分布在《關(guān)雎》以下(不包括《關(guān)雎》)的其他詩(shī)篇之前。即以今人的說(shuō)法為例。陳子展在《詩(shī)經(jīng)直解》(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83年版)之《關(guān)雎》注一里說(shuō),《詩(shī)大序》就是《關(guān)雎序》。祝振先在《詩(shī)騷魅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里也指出:“自從漢代的‘毛詩(shī)一統(tǒng)天下后,《詩(shī)經(jīng)》及其每篇作品的大意便有了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的解說(shuō),這就是《詩(shī)序》。在我們現(xiàn)在見(jiàn)到的古本《詩(shī)經(jīng)》中,每首詩(shī)前都有一小段題解性的文字。如《周南·漢廣》篇前說(shuō):‘《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guó),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wú)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古人把它稱為‘小序。另外在第一篇《周南·關(guān)雎》前,有一篇較長(zhǎng)的文字總述全書(shū),前人稱之為‘大序。”
第二種說(shuō)法講,每篇詩(shī)前的“題解”都是《小序》,包括《關(guān)雎》之前都有“題解”;至于《大序》,則與《關(guān)雎》的“題解”同處一個(gè)位置。這也就是說(shuō),《大序》是與《關(guān)雎》的“題解”——《小序》相混編的。也以今人的說(shuō)法為例。夏傳才在《詩(shī)經(jīng)語(yǔ)言藝術(shù)》(語(yǔ)文出版社1985年版)里說(shuō):“《毛詩(shī)序》各篇題解文字簡(jiǎn)略,獨(dú)在第一篇《關(guān)雎》的題解下面,有一大段文字,比較全面地闡述了詩(shī)歌的特征、《詩(shī)經(jīng)》的內(nèi)容、分類、表現(xiàn)方法和社會(huì)作用等問(wèn)題,可以看作《詩(shī)經(jīng)》的全部序言,稱作‘大序;其余的題解都稱作‘小序。”《辭海》(上海辭書(shū)出版社1979年版)在“詩(shī)序”條下也寫(xiě)道:“在首篇《關(guān)雎》的‘小序之后,有大段文字概論全經(jīng)的,為‘大序。”李澤厚、劉綱紀(jì)主編的《中國(guó)美學(xué)史》第一卷(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4年版)則說(shuō)得更為周詳:“《毛詩(shī)序》很早就有所謂大序、小序之分。小序是用以說(shuō)明《詩(shī)經(jīng)》各篇的主題、作者和歷史背景的。現(xiàn)存《毛詩(shī)序》寫(xiě)在《國(guó)風(fēng)》首篇《關(guān)雎》題下,而其中大部分內(nèi)容是概述詩(shī)的一般理論,顯然并非僅僅針對(duì)《關(guān)雎》而發(fā)。這些內(nèi)容應(yīng)是全書(shū)的總序,也就是所謂大序,但后來(lái)因卷冊(cè)錯(cuò)亂,竄入了《關(guān)雎》的小序之中。”
筆者很贊成第二種說(shuō)法對(duì)大、小詩(shī)序的交代。但是,現(xiàn)在大家所看到的通行的毛傳、鄭箋《詩(shī)經(jīng)》,在《關(guān)雎》之前擺著的就是那么一大段文字。在那里面,哪些是《大序》,哪些又是《小序》呢?
這里,為了方便進(jìn)一步地討論,特占用一點(diǎn)篇幅照錄出這段文字,以饗讀者:
《關(guān)雎》,后妃之德也,《風(fēng)》之始也,所以風(fēng)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xiāng)人焉,用之邦國(guó)焉。《風(fēng)》,風(fēng)也,教也。風(fēng)以動(dòng)之,教以化之。詩(shī)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shī)。情動(dòng)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詠)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fā)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lè),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guó)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dòng)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shī)。先王以是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fēng)俗。故《詩(shī)》有六義焉:一曰風(fēng),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fēng)化下,下以風(fēng)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wú)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fēng)》。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guó)異政,家殊俗,而“變風(fēng)”“變雅”作矣。國(guó)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fēng)其上,達(dá)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fēng)”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發(fā)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guó)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fēng)》;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fēng),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shī)》之至也。然則《關(guān)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fēng),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fēng)化,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guān)雎》樂(lè)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jìn)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wú)傷善之心焉。是《關(guān)雎》之義也。
按前面第二種說(shuō)法,《關(guān)雎》前的這一大段文字,應(yīng)該是大、小序摻和混雜在一起的。如何區(qū)分它們呢?孔穎達(dá)《毛詩(shī)正義》說(shuō):從起首至“用之邦國(guó)焉”為《小序》,是《關(guān)雎》的題解;從“《風(fēng)》,風(fēng)也”開(kāi)始至文末,則為《大序》,是面向全《詩(shī)》的。孔穎達(dá)的觀點(diǎn),為《辭海》“詩(shī)序”及“大序”條所吸收。
不過(guò),李澤厚、劉綱紀(jì)主編的《中國(guó)美學(xué)史》第一卷則對(duì)這段文字的劃法表示出不同意見(jiàn)。該書(shū)這樣寫(xiě)道:
我們認(rèn)為,現(xiàn)存《毛詩(shī)序》開(kāi)首,自“《關(guān)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guó)焉”,就屬于說(shuō)明《關(guān)雎》的小序。末尾“然則《關(guān)雎》”至“《關(guān)雎》之義也”一段看來(lái)也是說(shuō)明《關(guān)雎》的小序,從文義似應(yīng)接在開(kāi)首一段的“用之邦國(guó)焉”以后。這也就是說(shuō),上述兩段話都是《關(guān)雎》的小序,被前后割裂而竄入了大序。此外,緊接在開(kāi)首“《關(guān)雎》,后妃之德也。……用之邦國(guó)焉”之后的“《風(fēng)》,風(fēng)也,教也。風(fēng)以動(dòng)之,教以化之”這幾句話,可能是屬于下文對(duì)“六義”中的“風(fēng)”的解釋,似應(yīng)接在“故《詩(shī)》有六義焉:一曰風(fēng)……六曰頌”之后和“上以風(fēng)化下……故曰《風(fēng)》”之前。這樣,不論從邏輯上和行文上來(lái)看,才顯得較為合理。總起來(lái)看,我們認(rèn)為現(xiàn)存《毛詩(shī)序》把《關(guān)雎》小序割裂和大序(即全書(shū)總序)混到了一起,同時(shí)大序的文字也有錯(cuò)簡(jiǎn)之處。
我們認(rèn)為,在關(guān)于《詩(shī)序》之大、小序的第二種說(shuō)法中,李澤厚、劉綱紀(jì)等的說(shuō)法比之孔穎達(dá)及《辭海》的觀點(diǎn)更具合理性一些,也更容易為人所接受。
二、《詩(shī)序》的作者是子夏還是衛(wèi)宏?
那么,《詩(shī)序》的作者是誰(shuí)呢,或者說(shuō)是哪些人呢?今人張西堂在他的《詩(shī)經(jīng)六論》(商務(wù)印書(shū)館1957年版)中對(duì)歷代說(shuō)法作了粗略統(tǒng)計(jì),得有16種說(shuō)法之多。而徐澄宇在《詩(shī)經(jīng)學(xué)纂要》(中華書(shū)局1936年版)里的統(tǒng)計(jì)更達(dá)24種。這里介紹比較重要的三種說(shuō)法。
1.子夏之作
最早指明《詩(shī)序》作者的是東漢鄭玄的《毛詩(shī)傳箋》。《鄭箋》在《詩(shī)經(jīng)》已亡六笙詩(shī)《南陔》《白華》《華黍》題下云:“子夏序《詩(shī)》,篇義合編,故詩(shī)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故訓(xùn)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shī)亡。”鄭玄的說(shuō)法為三國(guó)魏王肅《孔子家語(yǔ)注》、吳陸璣《毛詩(shī)草木鳥(niǎo)獸蟲(chóng)魚(yú)疏》所沿襲。他們均認(rèn)為:孔子刪《詩(shī)》后傳與學(xué)生子夏(即卜商),子夏為之作序再傳于后世。正是出于子夏作《詩(shī)序》的緣故,鄭玄為《詩(shī)》作序時(shí)有意“避子夏序名”而稱作《詩(shī)譜》。(參見(jiàn)孔穎達(dá)《毛詩(shī)正義·詩(shī)譜序疏》)當(dāng)然我們應(yīng)該了解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即鄭玄為三《禮》《論語(yǔ)》作序都是以“序”冠名的。
2.子夏、毛公合作
這個(gè)觀點(diǎn),最早也由鄭玄《詩(shī)譜》提出,稱《大序》為子夏作,《小序》則系子夏、毛公合作。
以上兩大觀點(diǎn),其實(shí)皆以子夏為中心,突出孔子刪詩(shī)、子夏傳詩(shī)的承緒嗣統(tǒng),稱《詩(shī)序》的觀點(diǎn)乃圣人所傳,體現(xiàn)了孔子的“微言大義”,包含有孔子的“圣王”教化觀,從而將《詩(shī)序》置于漢學(xué)《詩(shī)經(jīng)》義疏的中心地位,使之成為解釋《詩(shī)》義的唯一依據(jù)。
3.衛(wèi)宏之作
最早見(jiàn)載于《后漢書(shū)·儒林列傳下》。其云:
衛(wèi)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xué)。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shī)》,乃為其訓(xùn)。宏從曼卿受學(xué),因作《毛詩(shī)序》,善得《風(fēng)》《雅》之旨,于今傳于世。
這一觀點(diǎn)擁護(hù)者最多,并在宋代以此形成挑戰(zhàn)《詩(shī)序》權(quán)威的第一個(gè)高潮。先有蘇轍在《詩(shī)集傳》中為衛(wèi)宏作《序》說(shuō)大張其目,向漢唐之際幾乎眾口一辭的子夏著《序》說(shuō)發(fā)起詰難。他認(rèn)為,第一,孔子敘《書(shū)》《易》“皆不詳言,常舉其略以待學(xué)者自推之”,而《詩(shī)序》卻十分地詳盡,這與孔子為經(jīng)典作序的義例相悖。第二,《詩(shī)序》在語(yǔ)言上“反復(fù)煩重,類非一個(gè)之詞”,因此《詩(shī)序》的主體部分絕非出自孔子—子夏嗣統(tǒng),而是漢儒衛(wèi)宏。不過(guò),他又以為,《小序》的首句是孔子或孔子弟子之知詩(shī)者所為,首句下面的申而續(xù)之的話,則“皆毛氏之學(xué)而衛(wèi)宏之所集錄也”。所以,他在《詩(shī)集傳》中只取首句作為解詩(shī)的依據(jù)——因?yàn)槟遣攀强鬃踊蚩组T(mén)弟子的真言。今人蔣見(jiàn)元、朱杰人認(rèn)為:“蘇氏對(duì)《詩(shī)序》的批駁大多是言之成理的。……有力地動(dòng)搖了《詩(shī)序》的權(quán)威,為宋代疑古的學(xué)術(shù)思潮提供了材料,為以后的《詩(shī)經(jīng)》研究開(kāi)拓了道路。”(蔣見(jiàn)元、朱杰人:《詩(shī)經(jīng)要籍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到了南宋初,鄭樵著《詩(shī)辨妄》則更為激烈。他第一個(gè)提出全部廢除《詩(shī)序》,因?yàn)椤对?shī)序》斷非先秦人所作,而是漢代“村野妄人所依”。其后,理學(xué)大師朱熹重作《詩(shī)集傳》,從初本不反《詩(shī)序》的立場(chǎng)轉(zhuǎn)變過(guò)來(lái),改而全面攻詰《詩(shī)序》,指出“《詩(shī)序》害《詩(shī)》”“妄誕其說(shuō)”“亂《詩(shī)》本意”(《朱子語(yǔ)類》八十一),主張“去《序》言《詩(shī)》”。他將《毛詩(shī)》每首詩(shī)前的《詩(shī)序》并在一起,改置于全《詩(shī)》之末,以后又逐篇加以反駁,形成《詩(shī)序辨說(shuō)》一書(shū)。
蘇轍、鄭樵、朱熹們掀起的反《詩(shī)序》運(yùn)動(dòng)動(dòng)搖了漢唐之際所確立的以《詩(shī)序》為代表的《毛詩(shī)》的絕對(duì)權(quán)威(在南宋至清初這長(zhǎng)達(dá)六七百年的時(shí)間內(nèi),《詩(shī)序》可以說(shuō)已被廢去了),引起了與朱熹同時(shí)的漢學(xué)領(lǐng)袖呂祖謙的不滿,他說(shuō):“學(xué)《詩(shī)》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呂氏家塾讀詩(shī)記》卷一),仍然堅(jiān)持《詩(shī)序》是孔子弟子得自圣人嫡傳。他作的《呂氏家塾讀詩(shī)記》三十二卷,遵從《詩(shī)序》,嚴(yán)格按照《序》義解《詩(shī)》;對(duì)訓(xùn)詁的取舍,也多依據(jù)《毛傳》。不過(guò),他在《讀詩(shī)記》里又承認(rèn)蘇轍關(guān)于《詩(shī)序》非一人所作的判斷的合理性,稱“三百篇之義,首句當(dāng)時(shí)所作,或國(guó)史得詩(shī)之時(shí)載其事以示后人,其下則說(shuō)詩(shī)者之辭也”。這說(shuō)明,“呂祖謙已經(jīng)看出了《詩(shī)序》的矛盾,但由于思想保守,不敢大膽懷疑,只得回避矛盾”(蔣見(jiàn)元、朱杰人:《詩(shī)經(jīng)要籍解題》)。呂祖謙以后的嚴(yán)粲(著《詩(shī)緝》)對(duì)《詩(shī)序》的態(tài)度也與呂祖謙大體一致。
那么,現(xiàn)代學(xué)者又如何看待《詩(shī)序》作者之爭(zhēng)呢?應(yīng)該說(shuō),就一般而言,都比較認(rèn)可這樣一個(gè)結(jié)論,即《詩(shī)序》是由漢代毛詩(shī)派的一些經(jīng)學(xué)家(當(dāng)然包括毛亨、毛萇)在長(zhǎng)達(dá)三四百年的時(shí)間里連續(xù)不斷地撰寫(xiě)終至衛(wèi)宏而集大成。這誠(chéng)如李澤厚、劉綱紀(jì)等所言:“《后漢書(shū)·儒林傳》對(duì)《毛詩(shī)序》的作者有明確記載,指出是衛(wèi)宏所作,這應(yīng)當(dāng)是最為可信的說(shuō)法。但所謂衛(wèi)宏所作,并非衛(wèi)宏一人的創(chuàng)見(jiàn),而是對(duì)毛萇一派的詩(shī)說(shuō)的纂集整理。”《詩(shī)序》“大約是衛(wèi)宏把源于荀子學(xué)派的毛萇對(duì)詩(shī)的看法加以記錄、整理、加工的結(jié)果。”(《中國(guó)美學(xué)史》第一卷)又如夏傳才所言:《詩(shī)序》“可以認(rèn)定不是一時(shí)一人之作,而是在漢代《毛詩(shī)》流傳的幾百年過(guò)程中,經(jīng)過(guò)許多傳授者陸續(xù)增修完成的,其中有毛亨、毛萇、衛(wèi)宏,還有其他人,衛(wèi)宏對(duì)現(xiàn)在流行下來(lái)的《毛詩(shī)序》的編纂,起了較大的作用。”(夏傳才:《詩(shī)經(jīng)語(yǔ)言藝術(shù)》)
三、讓思想沖破牢籠
那么,宋人何以要對(duì)自漢至唐確立起的《詩(shī)序》權(quán)威發(fā)起猛烈挑戰(zhàn)呢?難道僅僅因?yàn)椤对?shī)序》的作者不是孔子—子夏么?以蘇轍、鄭樵、朱熹為代表的宋儒之所以揭發(fā)《詩(shī)序》“作偽”行為的真實(shí)目的何在呢?
其實(shí),《詩(shī)序》作者問(wèn)題之爭(zhēng)在本質(zhì)上屬于儒家文化的保守與革新之爭(zhēng),是宋代思想界、《詩(shī)經(jīng)》學(xué)界的一場(chǎng)破權(quán)威、倒偶像,“讓思想沖破牢籠”的斗爭(zhēng)。漢儒們之所以要托名孔子—子夏而作《詩(shī)序》,無(wú)非是拉大旗、作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將《詩(shī)序》以及與之一體的《毛傳》《鄭箋》《毛詩(shī)正義》予以神圣化、教條化、僵尸化,讓對(duì)《詩(shī)經(jīng)》的說(shuō)明、解釋只允許有一種聲音,一個(gè)模式,一條標(biāo)準(zhǔn)。而宋儒們的針?shù)h相對(duì)的行動(dòng),則首先在其外包裝上動(dòng)手術(shù)、剝畫(huà)皮,讓躲在圣人光環(huán)下的漢唐經(jīng)師現(xiàn)出原形,再?gòu)摹霸?shī)義”的層面去剝其內(nèi)核。總之,漢代至唐的經(jīng)師們?cè)凇对?shī)經(jīng)》學(xué)界搞一言堂既久,勢(shì)必會(huì)帶來(lái)強(qiáng)烈的抵觸與反抗。這種抵觸與反抗由北宋古文運(yùn)動(dòng)的領(lǐng)袖、“慶歷新政”主將之一的歐陽(yáng)修撰寫(xiě)的《詩(shī)本義》投出第一枚問(wèn)路的石子。歐陽(yáng)修寫(xiě)道:
蓋詩(shī)人之作詩(shī)也,固不謀于太師矣。今夫?qū)W《詩(shī)》者求詩(shī)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乎學(xué)詩(shī)也?若圣人之勸戒者,詩(shī)人之美刺是已,知詩(shī)人之意,則得圣人之志矣。
這段話的要旨,是強(qiáng)調(diào)《詩(shī)經(jīng)》解說(shuō)與研究中的“本”與“末”,提請(qǐng)人們不要本末倒置。在他看來(lái),所謂經(jīng)師之說(shuō)、太師之職甚或圣人之志都屬于“末”的東西,只有“詩(shī)人之意”才是“本”。解說(shuō)者、研究者應(yīng)該即文求義,一心探求“詩(shī)人之意”,不要顧及其他,即所謂“求詩(shī)之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yuǎn)矣”(《詩(shī)本義》)。從這個(gè)立場(chǎng)出發(fā),歐陽(yáng)修對(duì)束縛《詩(shī)經(jīng)》研究的《詩(shī)序》以及《毛傳》《鄭箋》等舉起了討伐之劍,并繼而提出《詩(shī)經(jīng)》中不僅有“淫詩(shī)”,有“男女相悅之詩(shī)”,而且還多得很!在此之前的歷代經(jīng)師都將《詩(shī)經(jīng)》視為“圣王教化”之書(shū),視為嚴(yán)肅的政治讀物而對(duì)《詩(shī)經(jīng)》之“淫詩(shī)”(用今天的話講,即情詩(shī))視而不見(jiàn),避而不談。陸游說(shuō):“唐及國(guó)初,學(xué)者不敢議孔安國(guó)、鄭康成,況圣人乎?”可是自歐陽(yáng)修《詩(shī)本義》問(wèn)世以后,“諸儒發(fā)明經(jīng)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shū)》之《胤征》《顧命》,黜《詩(shī)》之序,不難于議經(jīng),況傳注乎!”(蔣見(jiàn)元、朱杰人:《詩(shī)經(jīng)要籍解題》)
朱熹繼歐陽(yáng)修之后重作的《詩(shī)集傳》二十卷,首先宣布廢棄《詩(shī)序》,而用他理學(xué)家的眼光去重新審視詩(shī)義,對(duì)《毛傳》《鄭箋》以及魯、齊、韓三家詩(shī)義以己意為取舍,并因此提出著名的“淫詩(shī)”說(shuō)。朱熹之論完全改變了漢儒以《詩(shī)》為美刺、為“諫書(shū)”的傳統(tǒng)和搞穿鑿附會(huì)、“以史證詩(shī)”的學(xué)風(fēng),在宋代思想界、文學(xué)界刮起了一場(chǎng)疑古思辨的狂飆。當(dāng)然,朱熹們的終極目的是以此為突破口之一,來(lái)改造舊儒學(xué),建立新儒學(xué),以替正從封建盛世頂峰上開(kāi)始衰落的傳統(tǒng)社會(huì)尋找一種擺脫危機(jī)的思想武器。而元、明、清三代皇帝正是看到《詩(shī)集傳》的這一良苦用心,而將它列為科舉標(biāo)準(zhǔn)之一,終使《詩(shī)經(jīng)》學(xué)復(fù)歸一統(tǒng)。這樣,原本曾帶領(lǐng)士子們沖破思想牢籠的《詩(shī)集傳》,重又將他們送回牢籠,讓他們戴上了新的枷鎖。而入清以后漢學(xué)的興起,乾嘉學(xué)者們對(duì)《詩(shī)序》的重新尊崇有加(以馬瑞辰的《毛詩(shī)傳箋通釋》、胡承珙的《毛詩(shī)后箋》、陳奐的《詩(shī)毛氏傳疏》為代表),便是對(duì)《詩(shī)集傳》這種獨(dú)霸天下的至尊地位的一種反叛。但這一次《詩(shī)序》所享受的好景并不長(zhǎng)。進(jìn)入近代以后,魏源(著《詩(shī)古微》)、康有為(著《新學(xué)偽經(jīng)考》)們又一次挑起了批判《詩(shī)序》的戰(zhàn)斗(最初是以今古文之爭(zhēng)的形式展開(kāi)的),至民國(guó)前期形成反《詩(shī)序》的新高潮(1922年開(kāi)始,一直延續(xù)到全民族抗戰(zhàn)期間。其代表人物為胡適、鄭振鐸、郭沫若、俞平伯、顧頡剛等)。
歷史就是這樣一波又一波地起落,一次又一次地輪回,將人們推向一片又一片的新天地。最終,大家認(rèn)識(shí)到,《詩(shī)序》不是圣經(jīng),《毛傳》《鄭箋》《毛詩(shī)正義》不是圣經(jīng),《詩(shī)集傳》不是圣經(jīng),即連《詩(shī)經(jīng)》本身也不是圣經(jīng)——它們通通都不是完美無(wú)缺的,都是可以討論的,可以批判的;并且這種討論與批判也容不得一個(gè)圣人、一種圣言高高在上地指揮與指點(diǎn)。只有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氛圍里去自由地閱讀《詩(shī)經(jīng)》,它才是鮮活的,有生命力的,有藝術(shù)價(jià)值、思想價(jià)值與社會(huì)價(jià)值的,才是屬于中華民族全體人民所擁有的真正意義上的國(guó)寶。這誠(chéng)如民國(guó)前期在反《詩(shī)序》運(yùn)動(dòng)中首開(kāi)自由詮釋《詩(shī)經(jīng)》旨義之風(fēng)的郭沫若在其《卷耳集·序》中所自白的:
我們的民族,原來(lái)是極自由極優(yōu)美的民族。可惜束縛在幾千年來(lái)禮教的桎梏之下,簡(jiǎn)直成了一頭死像的木乃伊了。可憐!可憐!可憐我們最古的優(yōu)美的平民文學(xué),也早變成了化石。我要向這化石中吹噓些生命進(jìn)去,我想把木乃伊的死像蘇活轉(zhuǎn)來(lái)。(郭沫若:《卷耳集·屈原賦今譯》,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