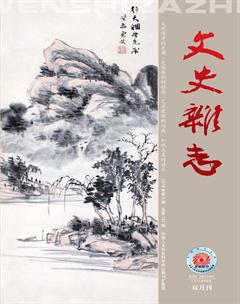周易的生命哲學
王世德
《周易》是一部彌綸天地之道的奇書,對中外哲學和美學等都產生了深遠廣泛的重大影響。它原是一部占筮之書,對國家大事興亡成敗的預測,對歷史經驗事實的認識和解釋,對治國處事的看法,有很多智慧。六十四卦的筮辭有不少能給人哲學、政治、道德、美學等社會思想感情的啟發。
《周易》有經和傳。易經是周代筮官根據歷代筮辭編選而成。《易傳》寫成于《荀子》之后,《樂記》之前,大約在秦末漢初。列國爭雄,百家爭鳴之后,荀子、韓非、《春秋左傳》等,都綜合各家思想,提供建國方略。《周易》站在儒家立場上,吸收道家思想,第一次設想建立一個自然、世界模式,強大國家,如《乾卦·彖傳》說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周易》最大的特點是講生命哲學
劉綱紀教授在《周易美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一書里明確斷言:“我認為《周易》的哲學乃是中國古代哲學的生命哲學,這是《周易》哲學最大的特點和貢獻所在。”所言極是。包含在《周易》中的古老的生命哲學,比19世紀70年代的德國狄爾泰(1833—1911)和法國柏格森(1859—1941)的生命哲學,更有不可輕視的合理性和優越性。可以說,生命是《周易》哲學的中心。
《周易》生命哲學的基礎是天地。生育萬物,推進不已,是天地最偉大的功能與生命陰陽交感創新最大的特性。
中國農歷也叫“夏歷”。從夏代起,按照季節種植農業,稱“行夏之時”。要靠天“云行雨施”。人類要掌握四時變化。天地是生命之所從出,又按照生命變易,推陳出新之道,不斷變化。天地是生命的根基,源泉。生命是天地的靈魂與中心。《易傳》是天地宇宙哲學,其本質核心是生命哲學。美是天地順動的產物。天地順動,符合人類不斷推進創新的理想,不忒(違反)規律和理想追求,才是美。天地順動,符合事物發展規律和人的進步理想目的(達到統一)就是貞(正),有利于人類,也符合天道、地道、人道。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天地正道,自然秩序,都是順動的“不易之道”,符合規律、法則、準則:生生不息,永恒發展,天地日月能永照,四時變化能永成,萬物化育能久美,就是永恒無限的生命之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成象謂乾,剛健運行。效法為坤,順通為亨。64卦象數,昭示世界天地變化,為陰陽對立變化和諧統一的總規律,也是多樣豐富統一和諧構成的美的規律。
生命美學的寶貴核心
去掉古代滲進的宿命、天命的神秘思想,發揚《周易》重視生生不已,自強不息的對立統一發展觀,爭取吉福發展,是我國《周易》中生命美學的寶貴核心。
《周易》的生命哲學(美學),對人類生命存在有積極的獨到見解。《乾》卦中對此高度概括的一句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要剛健自強,志同道合,求進展(《泰》卦:“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因為過猶不及)而四時不忒。圣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卦》)。
一切要取法于天地,陰陽變化統一而順行合序,使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乾》卦)
人要自然化(效法自然,符合規律),自然要人化(趨向人的進步合理的理想,兩者要同時進步,逐步結合得完善美好),要經過長期探索,努力,總結,改進。要使自然生命的發展規律與社會發展規律和美的結合統一,是要經歷不斷的努力改進才能逐步實現的。
《周易》的生命哲學和柏格森的《生命美學》可以做一番比較。柏格森最重要的生命哲學的著作是《創造進化論》,獲得1912年諾貝爾文學獎,出版于1907年。《周易》產于秦末,大約為公元前206年。兩者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把世界存在理解為一個生生不息、永無止境的“流”,乃《莊子·大宗師》中說的:“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天道》說的:“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秋水》說的:“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也是《荀子·天論》說的“陰陽大化”。《周易》把這些思想集中、發展、提升為哲學的根本原則,加以系統論證,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辭下》),“日新之謂德”,“生生之謂易”。(《系辭上》)這是把“天地”宇宙自然與生命的變化聯系起來,認為生命是在天地永恒運動中不斷變化的。
柏格森《創造進化論》提出,生命像綿延不息,變化無窮的長流,不斷創新。他說:“存在就是變易”,“不斷變化創新”;“萬物新生,是內部生生不已的沖動力,向前綿延發展”,“永無止境的創造”。
《周易》和《創造進化論》都把生命的變化運動聯系起來,認為與生命變化運動不可分,都有生生不息的創新,是永恒無止境的;在時間中呈現為不斷變動革新,與時偕行,不斷創新。柏格森認為,生命是自由創造,不可遏制,截斷,遇見,有更多的個性自由創造。《周易》說要“順天應人”,有等級制不能不講仁義,也有必要進行一些革新,要有獨立不羈的精神。柏格森重視生命的自由創造,認為生命存在要不斷地推進和生成,不能機械停止。《周易》雖不談創造,但分開談“創”與“造”,常說動詞“生”,就是要有創造的新。
“生生不已”的思想,要“立成新器以為天下利”(《系辭上》),要觀象于天,效法天地,“生”“立”“制”出萬物,要變動不居,唯變所適(《系辭下》),重視“陰陽不測之謂神”;同時又重視自然規律,不主張隨意改造規律。
美在生命
孔子在《論語·八佾》中說,有的音樂“盡美矣,未盡善也”,就是希望美善兼通最好。《周易》認為,人類道德的行為要效法自然,人類對美的欣賞要從自然生命對味、色、聲的愉快欣賞出發去研究。《周易》視生命為美,最初是從味、色 、聲得來的生命感覺愉快,說明人性,講味、色、聲給人美感,符合人的情愿望欲求,受人喜愛歡迎。如果過度了,則對生命造成損害,就不受歡迎,反遭厭棄。所以,首先就要看是否有利于生命,能否把生命調養得更好更愉快。一切都以生命為取舍標準。墨子說:“食必常飽,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麗。”也是以生命為標準。
荀子針對生命享受的味、色、聲的愉快,卻主張要節制,這是為了保持生命健康。他還要求這種生理上的愉快感覺,要提升到與動物不同的層面,即社會性的人當獲得更為高級的精神心理上的愉快。《周易》也要求君子的飲食宴樂,生命中的一切,都要中正,崇德,要文明,要做到乾卦要求的“元、亨、利、貞”四德,從而有利于生命境界的提升,并有利于天下。自然的運動、變化、生長,生命的流行不息,欣欣向上,順暢亨通,時空暢達,繁榮興盛,物質和精神都豐富多彩,形成天地大和,都有利于生命的長成,增添生命的美。
墨子怕追求生命過分而成災;荀子說不必怕,不必“私憂過計”,萬物養人足有可余,不必擔憂大而富。《周易》說:“富有謂之大業”,“發于事業,美之至也。”要統治者善于治理好國家,安排好天下之民的“事業”,“積美之源”,就能有美有樂。《周易·乾》說:“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國足以干事”,生萬物,富邦,養民,天下和平,久成,安民,上下、內外、大小、遠近皆無害,天地合,生命都美,達到最高理想:“大和之美”(大音泰,即太),就是“乾卦”說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貞”。天象變化和萬物生長變化都“各正性命”,永久而長遠。陰陽會合,氣象沖和,要社會人際和睦相親,要雜多統一,不同而和,如音樂和生命都是如此。
史伯說得很好:“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世界就是由雜多事物統一構成的,而且正因此才能永繼創生新物。生命延伸出萬物之美,各得其所,其宜,并繁榮茂盛,給人無限美妙愉快。這就是生命美學。
人有生命。萬物有沒有呢?萬物各有本性。有機物有生命。《周易》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云從龍,風從虎。圣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這就是“各正性命”。人有男女,物有剛柔,動植物有不同季節的生長繁殖,“各從其類”。天下“至賾(雜)而不可惡也”“至動而不可亂也”。萬物都順利繁茂發展,生生不息,不相妨害,就能“保合大和”(《系辭下》)。這就是“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有差異,百花齊放,才有和諧,才有繁榮發展,興旺發達。有人以為滅盡異己才好,其實那樣只能導致貧乏單調,自趨滅亡。所以一定要和而不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這個道理太正確,太深刻,太精彩了,可惜有的人就是不懂,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周易·睽卦傳》說:“君子以同而異”,此之謂也。
天下大同、大和
孔子認為,君子應異而不同。他以不同為前提。他因同而要異。百花齊放,異了之后,世界仍要大同。《周易》認為,君子應同而不異,要因異而要同。所以,以天下大同為理想。因為,天下萬物是異的,可以保留異,百花齊放,但要實現天下大同。
孔子和《周易》都是要百花齊放,世界大同的。大同才是美,大和才是最高的美。各不相同的個體生命,百花齊放都能和諧發展,天地間大自然和人類都興旺發達,萬物“大和”之美,就是最高、最廣大的美!
古希臘人重視對色、味、形的視聽感覺、實用功利、道德、認識四個方面愉快的美;孟子除了味、色、聲的美,還提出“理義之悅我心”,說倫理道德給人審美愉悅。中國沒有神秘狂歡的“酒神”精神,但《周易》不否認美“暢于四肢”,要打破四體對靈魂的束縛,卻不主張無節制地放縱行為,損害生命。它也不同于古希臘的“日神”精神,崇拜清晰的秩序法則、尺度比例等。中國文化重視“陰陽不測之謂神”,立足生命永恒于變化中,認為其規律不能機械規定,但又不是像西方有神憑附的迷狂狀態。
《樂記》說:“大樂與天地同和”,不只是作為日常消遣,而認為音樂,可以塑造人性,與自然和諧,不是超自然的神秘。
《周易》崇尚君子“自強不息”的精神,要效法天地大自然運行不息;不是為求知識,也不是要冷漠、不動情地觀察和模仿、認識自然,而是要熱烈效法自然,積極進行發展,獲得美好發展的“存在”;要有積極有為的創造性,與天地自然萬物相互交相感應,取得心理、精神的暢快,玩賞的歡悅。
《周易》基于生命哲學,以天地萬物生命存在與發展的合規律性,來說明宇宙是和諧的,抓住了宇宙之所以和諧的根本。因為“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向人們顯示了無限雜多、變化不定的自然萬物具有相互協調、不斷生長變化的合規律性。要讓人取得自由,肯定自己的生存。有了和諧的美,才能引起人類的歡欣和贊美。
古希臘哲學家、數學家畢達哥拉斯認為,秩序和比例是美的,有用的,那是宇宙規律的表現,還不是規律本身;“無序”之中也未嘗沒有合規律性。《周易》認為宇宙合規律性表現在不息的變化中,并且不認為數決定比例秩序的和諧,而是生命的陰陽變化合規律,才有自然和社會的和諧。
《周易》把美與生命不可分地聯系起來,同時確認美在生命生生不息的變化、更新中,在君子自強不息、創造天下“大業”的不懈努力中。劉綱紀教授在《周易美學》中認為:中國美學自古以來就是把美與藝術和生命聯系在一起的,《周易》所說的生命運動變化規律,同時也就是藝術創造必須遵循的規律。《周易》講生命運動變化規律都與藝術創造有關,在藝術中可以找到一切生命形式的特征,例如有變化的動力,是有機結構,有統一節奏,有興亡規律。
《周易》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與人的存在都是生命運動變化的表現,這樣生命就有了“本體論”的意義。《周易》還提出了自然生命的運動變化與社會倫理的表現性有一致性。
《周易》認為,美為天地所生,天地、自然、萬物生命的合規律、和諧的運動變化本身就是美。美就存在于天地自然萬物生命正常有規律地和諧變化中。美要遵循陰陽變化等規律,因為一切事物都由對立因素組成的。
天行健,生命自強不息
“天行健”,就是強健運行,說明“自勝者強”,也可說“自強就能勝”。《老子》還認為,柔弱可勝剛強。守柔曰強,生命力強大。《周易》則說“剛健”,就還包含了浩然之氣,中正、恰好、健壯、不逞強。八卦中,風、地、山、澤,不是有機生命物,但與有機生命物分不開,也有剛健的美。雷和火都有陽剛之美,有氣勢力量。
《古詩十九首》和曹操的詩作,是漢魏風骨剛健的代表。鐘嶸《詩品》只有兩句:“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雖只有兩句卻得曹作的神髓。陳子昂提倡魏晉風骨,反對齊梁“興寄都絕”的“彩麗競繁”。
魯迅也很重視剛健之美。他熱烈贊揚“剛健不撓”,“發為雄聲”,“致吾人于善美剛健者”,歌頌“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著跳著,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生命是進步的,是樂天的。”(《熱風·生命之路》)這些話語,洋溢著《周易》高揚的生命剛健精神,可以當做魯迅的美學宣言。魯迅還重視并贊揚現代木刻,評論蕭紅《生死場》等都是有“力的美”和剛健的作品。
《周易》在注重剛健的同時,也重視“陰柔之美”,強調厚德載物,仁愛精神,有含弘廣大,含章可貞的美,有含蘊無盡之意,能使人一唱三和,反復吟詠。《詩經·小雅》中的《伐木》,既有優容的幽靜,又有美的生氣。柔和的兒女情和陽剛的風雷氣,都是可貴的美。唐代顏真卿、宋代米芾的書法,則是不偏于剛,“溫而厲,威而不猛”,柔剛兼之。元代倪云林柔和的山水畫,疏淡柔靜,卻非纖弱無力,呈極美可賞之狀。清代姚鼐則全面發揮了《周易》關于剛柔的論述……這些都能給我們深廣的啟發。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