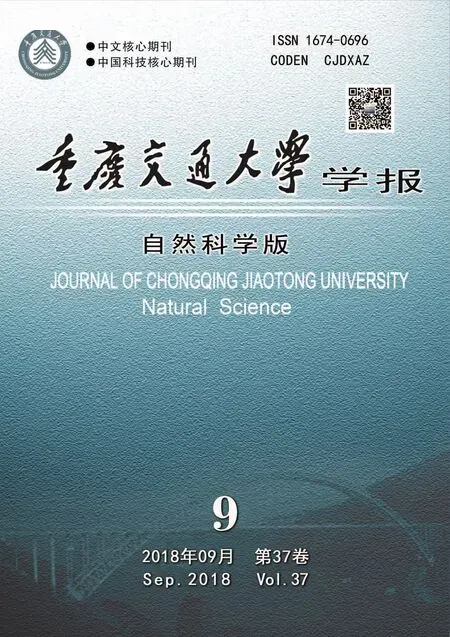“反規劃”理念下的山地農村建設用地適宜性評價
王桂林,江 蔚,汪 鵬,何 建
(1. 重慶大學,山地城鎮建設與新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重慶 400045; 2. 重慶大學 土木工程學院,重慶400045; 3. 重慶市國土資源和房屋勘測規劃院,重慶 400020)
0 引 言
土地利用規劃是對一定區域內未來土地利用的超前性計劃和安排,是依據城鄉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和土地的自然歷史特性,在時空上進行土地資源分配與合理組織土地利用的綜合技術經濟措施[1]。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西部大開發的深入推進,西部農村地區土地資源亟待開發利用,對山地農村建設用地規劃的研究越來越得到重視。曹春華[2]對西部山地城市土地開發利用進行了研究,認為西部山區由于其特殊的自然條件,建設方法應改“大挖大填”為“內斂整治,外放保育”;趙萬民[3]針對西南山地城市規劃建設,提出適應性新技術支撐體系,為山地土地的適宜性評價奠定了深厚理論基礎。山地農村地區由于其復雜的地質條件和特殊的地理環境,城鎮化發展難度較大,需要大力引導其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和科學規劃。
山地農村建設用地適宜性評價多以傳統評價方法為主,即根據區域的地質、地形、水文、生物、生態、社會、經濟等諸多方面因素,綜合判斷某區域是否適合作為建設用地。陳燕飛等[4]在南寧市建設用地適宜性評價中選取了水域、土地利用現狀、坡度、斷層、地貌、工程地質及自然保護區等影響因子;周建飛等[5]在對城市建設用地做生態適宜性評價時選取了自然生物、土地資源、社會人文、地形地貌等方面的評價指標;孔雪松等[6]在對農村建設用地適宜性評價的過程中,采用生態、地形、水文、社會、經濟等因子來構建指標體系;張翔等[7]在山地城鎮化與地質生態環境協調性研究中,將各項指標概括為山地地質生態環境系統和山地城鎮化系統兩部分。國外學者在土地適宜性評價研究中比如:F.STENINER等[8]和D.U.PHAM等[9]分別選取了土質、工業、水文、生物、地形、社會景觀等諸多指標,并針對評價模型、評價結果等做了大量研究;ZHANG Kaisheng等[10]和SUN Jian等[11]則重點研究了交通與土地利用的相互關系。
近年來,隨著我國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日益突顯,關注生態和諧、提高生態保護、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開始受到全社會重視。因此,傳統建設用地評價方法難于滿足生態用地優先規劃的發展需求,而類似于地質學“遠觀近校”觀察方法[12](即將整體規劃與單元分割方法相結合)的“反規劃”理念應運而生。俞孔堅等[13]提出了“反規劃”理念,即優先將不適宜建設區域劃出,再進行土地規劃。該理論最早主要應用于城市景觀規劃領域,旨在運用“反規劃”理念為城市規劃良好的生態基礎設施。彭德勝[14]將“反規劃”理論應用于沅江市城市規劃之中,以沅江五湖為中心,規劃出組團式布局結構;俞孔堅等[15]將其與科學發展觀相結合,并以北京東三鄉為例,提出了運用“反規劃”理論與景觀安全格局相結合的方法;周萬東[16]結合“反規劃”與傳統土地規劃理念,提出尊重自然生態過程的土地利用規劃方法;張曉燕[17]基于“反規劃”理論,結合區域生態基礎設施對秦皇島盧龍縣基本農田分布進行再規劃,得到優于現狀基本農田的規劃結果。
綜上,“反規劃”理念目前在城市或城鎮規劃中已得到了成功應用,而對農村尤其是山地農村的規劃應用較少。山地農村地區因其復雜地形地貌蘊含著豐富多樣的生態系統,成為我國國土生態安全的重要保障地區;若是規劃不當,則會對當地生態環境造成巨大損害。
此外,現有研究成果大多著重于對各安全過程及影響因子的選定,并未提及各因子之間的重要性差別(即權重分布定量評定)便直接得出結果[11-14];部分研究成果雖然對影響因子進行了定量評定,但并未給出相關評定方法理論依據[16]。
筆者以重慶市涪陵區義和鎮為例,根據山地農村特點,提出農村土地安全格局評價指標體系,基于“反規劃”理念建立山地農村建設用地適宜性評價方法。
1 “反規劃”理念下評價方法構建
“反規劃”理念是相對于傳統規劃理念而言的,“反規劃”并非不規劃,也亦非反對規劃,而是在規劃建筑用地之前優先劃出城市生態基礎設施用地。傳統規劃方法出于經濟考慮,先行規劃建設用地及商業用地,會導致生態用地破碎化,隨著城市擴張會進一步加劇城市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沖突;“反規劃”則主張對生態用地先行規劃,使其始終作為一個整體存在,保證生態功能最大化,降低或避免由于城市擴張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危害,達到可持續發展目的。
“反規劃”理念強調區域發展必須以生態基礎設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EI)為基礎。EI 即是指區域賴以生存的自然系統,是將生態系統各種功能整合在一起的關鍵性網絡狀土地空間格局[18]。
筆者以“反規劃”理念為依據,結合山地農村用地特點,遵循客觀科學性、主導性、層次分明性、可操作性,從土地水土保持、生態文明、地質災害這3個安全格局對其開展評價,所建立的山地農村土地安全格局評價指標體系如圖1,而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技術作為土地分析的工具,具有海量信息儲存、圖像顯示快捷的特點和強大的空間分析功能[19],筆者將“反規劃”理念與GIS技術相結合,模擬各安全格局發展過程和對土地影響程度。

圖1 山地農村土地安全格局評價指標體系Fig.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land security pattern in mountainous area
在土地適宜性評價中,常用的評價模型通常有模糊數學模型、信息量法、綜合指數模型、數理統計法、灰色系統評價模型、BP人工神經網絡模型等。這些模型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是模糊綜合評價模型和綜合指數模型。筆者選用較為簡單、成熟的綜合指數模型中的加權疊加法,如式(1)。
(1)
式中:Qij為第ij個網格生態紅線劃分分值;k=1,2, …,n,表示第k個因子;W(k)為第k個因子權重;Cij(k)為第k個因子在第ij個網格紅線區劃分值。
為解決各因子重要性定量確定過程中主觀經驗性與客觀科學性矛盾,筆者采用綜合指數模型與AHP專家層次分析相結合方法獲得影響因子權重。并據此疊加得到土地水土保持、生態文明、地質災害相應的安全格局,由此建立生態基礎設施(EI)。
2 實例應用
2.1 評價區概況
義和鎮位于重慶市涪陵區西北部的長江上游北岸,東接涪陵區李渡新區工業園區,西南臨長江與藺市、龍橋、石沱隔江相望,北止黃草山脈與長壽區但渡鎮相連,義和鎮區位如圖2。義和鎮幅員面積104.39 km2,下轄12個行政村,4個社區,108個村民小組,28個居民小組,4.8萬人,耕地面積21 69 hm2,森林面積2 000 hm2,森林覆蓋率18.57%。

圖2 義和鎮區位Fig. 2 The location of Yihe town
義和鎮地處平行嶺谷拆皺暖熱半濕區的長江河谷淺丘地帶,灰棕紫泥土屬,部分為深丘低山暗紫泥土屬,黃草紅春屬及冷沙黃泥土屬。境內海拔最低點為鶴鳳灘鋪子(156 m),海拔最高點為黃草山頂灣(787.8 m),年均溫度為17~18 ℃,年均降水量為1 000~1 100 mm,無霜期為290~320 d。境內除長江外,還有奚家河溝、沙灘河、烏楊溪、馬斑溪、黎家河溝、大磨溪等支流。
2.2 評價單元
參考《重慶市巴渝新農村民居通用圖集》中典型房屋設計尺寸(進深10 m),并考慮評價結果的可操作性和合理性,以3倍房屋進深的網格大小為基準,選取30 m×30 m網格作為評價單元。
2.3 評價過程及結果
由圖1可知:生態基礎設施包括水土保持安全格局、生態文明安全格局、地質災害安全格局這3個方面。其中:由于該評價區無斷裂帶、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質災害,在地質災害安全格局中只選取洪水和滑坡這兩項指標。
2.3.1 指標權重
因子權重采用以專家經驗為判斷基礎的AHP法確定,也稱作“專家-層次分析”。由于層次分析法具有人為判斷的片面性,兩兩比較結果不一定具有客觀一致性,通常需要一致性檢驗。若不能通過檢驗,便憑著大致估計調整判斷矩陣,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盲目性。為此筆者采用一種改進層次分析法來確定權重,用3標度法代替傳統的9標度法建立判斷矩陣,并通過最優傳遞矩陣把比較矩陣轉化為一致性矩陣,可快速得出權重排序。其操作性更強,且不需做一致性檢驗。
以水土保持安全格局為例,選取水源距離、坡度、林地保護這3個因素作為2級指標。即:U1={u11,u12,u13}={水源距離,坡度,林地保護}。
首先采用3標度法構建各指標之間的比較矩陣,如式(2)。
(2)
式中:cij=1表示指標Xi比Xj重要;cij=0,表示指標Xi和Xj同等重要;cij=-1,表示指標Xi沒有Xj重要。
求出C的最優傳遞矩陣O,如式(3)。
(3)

把矩陣O轉化為一致性矩陣D,矩陣D即為該準則層下的判斷矩陣,如式(4)。

(4)
其中:dij=exp(Oij)。
最終根據判斷矩陣D,求出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根所對應的特征向量,即為各評價因子的重要性,歸一化處理后,即得到指標u11~u13的權重為W=[0.148 3 0.289 0 0.562 7]T。
用同樣方法處理每個比較矩陣每位專家評出的指標權重,剔除偏差較大數據,取剩下權重值的平均數,最終得到u11~u13各指標的權重分別為W=[0.215 9 0.404 7 0.379 4]T。
同理,可得全部2級指標的權重為:U2={u21,u22,u23}={植被覆蓋率,自然風景區,土地利用現狀};W(u21~u23)=[0.503 6 0.327 7 0.168 7]T;U3={u31,u32}={洪水,滑坡};W(u31~u32)=[0.513 9 0.486 1]T。
2.3.2 1級指標評價結果
水土保持安全格局評價標準及分級設置如表1;生態文明安全過程評價標準及分級設置如表2;地質災害安全水平評價標準及分級設置如表3。

表1 水土保持安全格局評價標準及分級設置Table 1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classification setting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ecurity pattern

表2 生態文明安全過程評價標準及分級設置Table 2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gradation setting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afety process

表3 地質災害安全水平評價標準及分級設置Table 3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classification settings of geological disaster safety level
2.3.3 土地安全等級綜合劃分
土地安全等級綜合劃分評價模型為綜合指數模型加權疊加法,因子權重也采用與“專家-層次分析”法(AHP法)確定,并采用3標度法構建各指標之間的比較矩陣,確定各指標的權重如表4。

表4 建設用地適宜性評價指標權重Table 4 Weights of construction land suitability evaluation index
根據多因子分級加權指數和法來進行綜合等級評判,較好考慮了各因子影響疊加效果,但不能有效反映各指標獨特性。當部分權重較大的指標值達到某一范圍時,其對建設用地適宜性的影響程度呈現出較極端增長趨勢,直至最后具有決定性作用。從上述綜合評價模型得到結果中不能得到反應,因此需要在上述綜合評價結果的基礎之上人為的對評價結果作調整。根據文獻[20],綜合等級調整如表5;安全水平生態基礎設施EI最終劃分結果如表6。

表5 綜合等級調整Table 5 Comprehensive level adjustment

表6 安全水平生態基礎設施EI最終劃分結果Table 6 Safety level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EI final division results
2.4 評價結果分析
目前傳統評價方法[4-8]中多以自身條件(地質地貌)、用地條件、社會經濟條件、絕對限制條件作為評價要素,把生態保護簡單地綜合考慮為限制條件,表7為傳統分析方法中的評價要素選取及權重,據此得到的評價結果見表8。

表7 傳統分析要素選取權重Table 7 Weights of traditional analysis elements

表8 傳統評價方法所得建設用地適宜性匯總Table 8 Suitability of land for construction in traditional evaluation methods
為統一指標,根據建設用地安全情況,選取傳統評價結果中的適宜建設區域作歸為高安全水平區,較適宜及以上區域歸為中安全水平區,一般適宜及以上區域歸為低安全水平區。相比傳統評價方法結果,筆者所提出的評價方法中,高安全水平區面積增加16.7%,中安全水平區面積減少1.6%,低安全水平區面積減少14.8%,如圖3。
2.4.1 高安全水平區劃定
傳統評價中,經濟因素和地形地貌因素所占權重較大,對地貌類型復雜的山地農村,該評價方法會導致高安全水平區遠小于實際情況。而筆者基于“反規劃”理論的評價方法則充分考慮山地農村的特殊性,以水土保持、生態保護及地質災害情況為評價重點,以綜合指數模型和AHP層次分析法計算權重,將土地作為有機整體來考慮,盡量減少對土地的拆解,得到與實際情況更為符合的高水平安全區。
2.4.2 低安全水平區劃定
對于低安全水平區,本評價體系依據重慶市《生態保護紅線劃定方案》,充分考慮生態保護紅線對山地農村建設用地決定性影響,對生態紅線區域的劃定相較于傳統評價方法更為嚴格,因此低安全水平區域范圍小于傳統評價結果。
2.4.3 對農村居民點建設的影響
高、中、低安全水平的土地劃定對農村居民點建設選址具有較強的參考價值。農村居民點建設可根據自身需求選擇不同安全水平區:如建設用地需求較大且資金足夠建設生態防護設施以減免生態風險,可將建設用地擴展至中低安全水平區;反之,則可選取對生態防護設施需求較低的高安全水平區。
由上述結果可知,相較于傳統評價結果,本評價結果中高安全水平區增加,可更好地滿足山地農村發展對土地的需求,避免開發建設與自然生態過程爭奪空間;低安全水平區減少,生態紅線的劃定更加嚴格,從最大程度上保持山地農村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從生態基礎設施EI和建設用地安全性角度考慮更加優越,符合現今關注生態和諧、提高生態保護、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圖3 反規劃與傳統評價結果對比Fig. 3 Comparison between “inverse planning” and traditional evaluation results
3 結 論
基于“反規劃”理論加綜合指數評價模型的山地農村建設用地評價方法是落實《保護生態紅線劃定方案》、促進土地可持續利用的有效途徑:
1)相較于傳統評價的結果,本評價結果中、高安全水平區增加,可以更好地滿足山地農村發展對土地的需求,避免開發建設與自然生態過程爭奪空間。
2)高、中、低安全水平的土地劃定對農村居民點建設選址具有較強的參考價值,農村居民點建設可根據自身經濟條件及發展需求選擇不同的安全水平區。
3)最終得到的低安全水平生態基礎設施區結果對農村居民點選址具有指導性意義,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減免山地農村建設過程中對生態環境的不良影響,以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