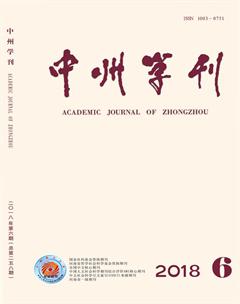惠洪《冷齋夜話》中的東坡記憶
王魁星
摘 要:比蘇軾小34歲的北宋著名詩僧惠洪,在當時文壇頗負聲名,據其《石門文字禪》部分詩作及陳敬《陳氏香譜》記載,他與蘇軾大約于崇寧三年之前相識。惠洪著《冷齋夜話》十卷,其中涉及蘇軾者達55篇。正由于惠洪與蘇軾相識,并對其在海南、杭州等地的行跡進行過實地考察,因而《冷齋夜話》中的東坡記憶帶有鮮明的紀實性與唯一性。在涉及蘇軾的這55篇中,除記述其行跡、交游外,有的講述蘇軾前世今生的故事,為明清小說中有關這一故事創作提供了原型,也有一部分記載蘇軾的創作軼事及其詩學觀念,對我們考察蘇軾被貶期間的創作心態、創作背景及其詩學思想提供了文獻支撐。
關鍵詞:惠洪;蘇軾;交游考述;冷齋夜話;東坡記憶
中圖分類號:I207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8)06-0129-06
北宋著名詩僧惠洪(1071—1128)詩文兼善,著有《冷齋夜話》十卷①,《石門文字禪》三十卷,《天廚禁臠》三卷,其中,《冷齋夜話》論及蘇軾者達55篇。據其《石門文字禪》數首詩作及陳敬《陳氏香譜》記載,惠洪與蘇軾曾有交集。由于惠洪與蘇軾相識,并與“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有詩文往來,加上他對蘇軾在儋州的行跡進行過實地考察,因而《冷齋夜話》中有關蘇軾行跡交游、前世今生、詩歌創作及詩論的記憶具有鮮明的紀實性與唯一性,這對蘇軾的貶謫行跡、創作心態研究向縱深處推進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依據,對明清小說中蘇軾前世今生故事提供了原型。在探討《冷齋夜話》中的東坡記憶之前,我們有必要對惠洪與蘇軾之間的關系進行一番系統地考察。
一、惠洪與蘇軾交游考述
對于惠洪與蘇軾是否相識,學界看法相左。持否定觀點者,以無確切文獻記載為據,否認二人有直接往來。持肯定觀點者,往往以他們有共同友人而推測二人應當相識。翻檢惠洪詩作,我們可以發現,二人確曾有過直接交往。如四部叢刊本《石門文字禪》(以下所引《石門文字禪》詩文均采用四部叢刊本)卷三《聞端叔有失子悲,而莊復遭火焚,作此寄之》載:
……
東坡昔無恙,豪俊日填門。君如汗血駒,膽氣終逸群。坡今騎魚去,眾客亦繽紛。翩然淮海上,霜鬢此身存。我亦識坡者,一見等弟昆。乃知水與乳,自然和不分。……②
端叔即李之儀,乃蘇軾門人。惠洪《石門文字禪》有數首酬贈李之儀之作,可見二人關系相當親厚。從該詩“我亦識坡者,一見等弟昆”可以看出,惠洪與蘇軾的確相識且有交往,惠洪當不至于在李之儀面前冒著被揭穿的風險妄稱與蘇軾相識。此外,《石門文字禪》卷一《次韻龔德顏柳貼》亦云:“積墨如陂池,積筆高隴阜。學之不至顏,要亦終至柳。此詩聞東坡,請君書座右。”由后二句可以看出,惠洪用自己從蘇軾處習得的書法見解勉勵龔德顏。卷十一《春日同祖賢二道人,步云歸亭,忽憶東坡此日詩,有懷其人,次韻》乃惠洪在蘇軾去世后所作,詩曰: “誰家楊柳欲遮門,依約東坡醉處村。捶地不堪華屋句,仰天空記刻舟痕。尚余千載風流在,乞與三人語笑溫。歸路松風吹凍耳,共追前事吊英魂。”惠洪在東坡行跡所到之處與友人共憶“前事”憑吊蘇軾,亦說明二者有一定交情,否則“共追前事”就無從談起。此外,宣和五年(1123),惠洪在興化遇到徐質夫,作《宣和五年四月十二日,余館湘陰之興化,徐質夫自土山來。一昔夜語,甚傾倒。且日前嘗夢見東坡,今復見子,何清事相聯耶!吾所居有亭,名“閑美”,嘗有白燕巢梁間,屢見鶴翔舞于層霄,囑予為詩紀其事。質夫,大梁人,賢而有文,佳公子也》《石門文字禪》卷十三:
徐侯官舍土山邊,頗為看書廢晝眠。偶見畫梁巢雪乙,更驚云漢舞胎仙。致坡入夢殊堪紀,與儼忘形亦自賢。聞道小亭時縱目,江山信美似斜川。
從詩題可以看出,惠洪與蘇軾當相識,否則,其夢到蘇軾就顯得頗為費解。頸聯中“儼”乃惠洪自稱,“忘形”即“忘形友”,從詩題及此二句可知,惠洪、蘇軾、徐質夫三人當有共同交集。徐質夫乃大梁人,三人或在京師相識、相知。此外,蘇軾去世后,惠洪有數首挽作,如《石門文字禪》卷十一《與客論東坡作此》及卷十五《袁州聞東坡歿于毗陵書精進寺壁三首》,從以上挽作亦可看出,二人應當相識。
除上述所舉惠洪詩作內證外,我們還可以從宋代陳敬《陳氏香譜》卷三《韓魏公濃梅香》翻檢到惠洪與蘇軾交往的記載:
黃太史公跋云:余與洪上座同宿潭之碧湘門外舟中,衡岳花光仲仁寄墨梅二枝,扣船而至,聚觀于燈下。余曰:只欠香耳。洪笑發谷董嚢,取一炷焚之,如嫩寒清曉,行孤山籬落間。怪而問其所得,云自東坡得于韓忠獻家。③
對于引文所述之事,宋代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六亦有記載:“《冷齋夜話》云:衡州花光仁老以墨為梅花,魯直觀之嘆曰:‘如嫰寒春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余因為賦長短句曰……”胡仔引惠洪《冷齋夜話》這段引文不及《陳氏香譜》記載詳細,且《陳氏香譜》以黃太史公口吻敘述,而胡仔引文則從惠洪角度講述,但兩段材料所述乃同一事。黃庭堅善于用香在當時頗有聲名,《陳氏香譜》將其所制四帖香方稱為“黃太史四香”,故《陳氏香譜》中的“黃太史公”即黃庭堅。此外,宋代阮閱《詩話總龜后集》卷四十六、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六、清代卞永譽《書畫匯考》卷四十四、清代《石渠寶笈》卷十四、清代《御制佩文齋書畫譜》卷十四與此相關記載中,“黃太史公”均作“黃魯直”,亦可作“黃太史公”乃黃庭堅的旁證。與此同時,惠洪《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跋與法鏡帖》曰:“山谷作黃龍書時,與予同在長沙碧湘門外舟中。”也記載了惠洪與黃庭堅在長沙碧湘門外舟中相見一事。黃庭堅乃蘇門四學士之一,若惠洪與蘇軾未曾謀面,斷不會在黃庭堅面前稱其香得自于蘇軾。通過以上引文可知,《陳氏香譜》中的“黃太史公”即黃魯直(黃庭堅),“洪上座”乃惠洪。因而,陳敬《陳氏香譜》所載惠洪與黃庭堅在長沙碧湘門外舟中相見一事可信,惠洪所言其香“自東坡得于韓忠獻家”亦當不誣,所以惠洪與蘇軾有直接交往乃是可以肯定的事實。韓忠獻即韓琦,由于韓琦于熙寧八年(1075)去世,是年惠洪僅4歲,故而其香當為蘇軾多年前得于韓忠獻家,后輾轉于惠洪之手。孔凡禮先生《蘇軾年譜》亦據此認定惠洪與蘇軾曾相識,頗有見地。
從上述所引《陳氏香譜》相關記載可知,惠洪與蘇軾相識在前,而后才與黃庭堅在長沙碧湘門外相遇,否則惠洪無法以其香得自于蘇軾回答黃庭堅之問。因而,弄清楚惠洪與黃庭堅在長沙碧湘門外何時相遇對確定惠洪與蘇軾相識的大致時間顯得極為重要。前面我們提到,惠洪《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跋與法鏡帖》也提到了他與黃庭堅在長沙碧湘門外舟中相遇一事,只是記載較為簡略,我們無法從中考察二人相遇時的具體信息。對此次相遇記載比較詳細的,則是黃庭堅《西江月》(月側金盆墮水)一詞之序。該詞乃黃庭堅贈惠洪之作④,今見于《山谷集·山谷詞》。序云:
崇寧甲申,遇惠洪上人于湘中。洪作長短句見贈,云:大廈吞風吐月,小舟坐水眠空。霧窗春色翠如蔥,睡起云濤正擁。往事回頭笑處,此聲彈指聲中。玉箋佳句敏驚鴻聞道衡陽價重。次韻酬之,時余方謫宜陽而洪歸分寧龍安。⑤
“崇寧甲申”,即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可見黃庭堅乃于是年與惠洪在長沙相見,故而他們相見當在黃庭堅南遷之前。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引《冷齋夜話》亦提及此事,“山谷南遷,與余會于長沙,留碧湘門一月”⑥。《石門文字禪》卷三《黃魯直南遷艤舟碧湘門外半月未游湘西作此招之》以及黃庭堅《贈惠洪》“吾年六十子方半,槁項頂螺忘歲年”亦可作為二人見于崇寧三年(1104)的旁證。
綜上可知,惠洪與蘇軾當相識于崇寧三年(1104)之前,在此基礎上,我們進一步考察二人相識的上限。惠洪《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四《寂音自序》云:“十九試經于東京天王寺得度,冒惠洪名。依宣秘大師深公,講《成唯識論》,有聲講肆。服勤四年,辭之南歸,依真凈禪師于廬山。”惠洪生于熙寧四年(1071),元祐五年(1090)十九歲,故而惠洪于元祐五年(1090)至元祐八年(1093)當在京師。據孔凡禮先生《蘇軾年譜》,蘇軾元祐五年(1090)在杭州任職,于元祐六年(1091)五月二十九日赴京師任翰林學士承旨,在京師僅三個月便又去潁州赴任,元祐七年(1092)赴揚州任職,十月至京師任兵部尚書,元祐八年(1093)九月底知定州。⑦故而惠洪與蘇軾在京師有交集的時間在元祐六年(1091)五月二十九日赴京后三個月當中,或元祐七年(1092)十月至元祐八年(1093)九月底知定州前之間,故而二人當相識于此二段時間之中。
二、《冷齋夜話》中的東坡行跡、交游與前世今生
惠洪與蘇軾同處一地的機會雖少,但二人行跡卻有較多的重疊,如他們都曾在杭州、廬山、惠州、江西等地留下過足跡。惠洪中年后四次入獄,曾被發配至海南崖州三年,故而對蘇軾行跡進行過實地考察,尤其對蘇軾在儋州行蹤頗為熟悉。如《石門文字禪》卷五《次韻蘇東坡》:“先生謫儋耳,一葉航渺茫。……我曾至其舍,月出波心房。追惟對遺編,燈火夜初涼。麗詞有逸韻,文君方小籹。便覺胸次閑,八窗玲瓏光。”哲人逝去,惠洪曾親自到蘇軾儋州的居所進行憑吊,面對其遺編感慨萬千。卷九《早登澄邁西四十里宿臨皋亭補東坡遺》抒發了詩人對蘇軾在海南澄邁臨皋亭艱難生活的感傷:“天下至窮處,風煙觸地愁。村囂聞捉拗,岸汁忽西流。鳥道通儋耳,鯨波隔萬州。趁雞行落月,凄斷在蠻謳。”其中,也飽含著惠洪對自己被發配至海南的憂傷之情。《冷齋夜話》卷五《東坡屬對》記述了惠洪實地考察蘇軾在海南的三件軼事:
予游儋耳,及見黎民為予言,東坡無日不相從乞園蔬。出其臨別北渡時詩:“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游。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醞佳甚,求一具,臨行寫此詩,以折菜錢。”又登望海亭,柱間有擘窠大字曰:“貪看白鳥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暮潮。”又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予檳榔。予問母:“識蘇公否?”母曰:“識之,然無奈其好吟詩。公嘗杖而至,指西木凳,自坐其上,問曰:‘秀才何往哉?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祝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尚在。”予索讀之,醉墨欹傾……⑧
第一件記述了蘇軾在儋州的困頓之狀:靠乞當地居民菜蔬生活,北歸時竟至于以詩抵菜金。第二件記錄蘇軾在儋州望海亭柱間所題對聯事。第三件乃蘇軾訪姜唐佐不遇而留墨寶一事。三件軼事雖未詳細展開,但蘇軾豁達、率真的個性躍然紙上。此外,惠洪還曾到儋州陵水縣、瓊山之愛泉尋訪蘇軾足跡。《石門文字禪》卷十三《過陵水縣補東坡遺二首》即惠洪到海南陵水縣之作⑨:“白沙翠竹并江流,小縣炊煙晚雨收。蒼蘚色侵盤馬地,稻花香入放衙樓。過廳客聚觀燈網,趁市入歸旋喚舟。意適忽忘身是客,語音無伴始生愁。”卷二十三《送李仲元寄超然序》記述了蘇軾在海南北渡時所游之地——愛泉附近的風物:“余至海南,留瓊山,太守張公憐之,使就雙井養病,在郡城之東北隅。東坡北渡,嘗游愛泉,相去咫尺,而異味為名,其亭曰‘炯酌,且賦詩而去。”惠洪所記此類軼事紀實性特征顯著,而且部分記載具有其他文獻所無的唯一性特征,對研究蘇軾在海南的生活狀況、心路歷程、詩文創作均有重要的文獻價值。除儋州外,惠洪也曾對蘇軾所到的杭州有所考察,如他與廓然游西湖時所作《讀和靖西湖詩,戲書卷尾》便是對蘇軾在杭州游西湖時所作《飲湖上初晴后雨》詩的戲作。
《冷齋夜話》還記載了較多蘇軾在高郵、徐州、南昌、武昌等地的蹤跡,如卷一《秦少游作坡筆語題壁》:“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中寺。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豈此郎耶!”⑩此段記載可與蘇軾《次韻秦觀秀才見贈與孫莘老李公擇甚熟將入京應舉》一詩相印證,記載了蘇軾在高郵初睹秦觀才華及詢問于孫覺之事。卷七《東坡和陶淵明詩》記述蘇軾從惠州至儋州及北歸途中的交游情況,重點講述了他在北歸至南昌與太守葉公祖洽相遇戲謔之事:“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至南昌,太守云:‘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耶?東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B11此段對話比較傳神地展現了蘇軾北歸途中的心態,為我們深入理解蘇軾豁達、幽默個性提供了翔實的文獻材料。
《冷齋夜話》也記錄了較多蘇軾與僧人交游之事。其中涉及道潛者頗多,如卷六《東坡稱道潛之詩》:
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州。”坡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于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饌客罷,與俱來,而紅妝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名聞海內。B12
該篇記錄了蘇軾未識道潛前對其詩的稱賞,既而在錢塘、西湖、東徐三次交往中相識、相知及詩文互動的過程,比較詳細地記述了蘇軾被貶期間的具體行跡及與道潛之間的交游。卷七《東坡留戒公疏》再現了蘇軾在維揚作疏留戒長老長住石塔一事,惠洪對蘇軾此疏極為稱贊,認為“戒公甚類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想,托之以為此文,遂與百世俱傳也”,高度評價了蘇軾的文學才華及“妙觀逸想”的處事之法B13。卷七《東坡戲作偈語》講述與劉安世山行訪玉版長老并作詩戲劉安世一事:
又嘗要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筍何名?”東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戲,為大笑。東坡亦悅,作偈曰……B14
此段所載乃靖國元年(1101)寒食節蘇軾遇赦北歸途中在虔州事,其《器之好談禪,不喜游山,山中筍出,戲語器之可同參玉版長老,作此詩》便作于此時。關于此事,《元城語錄》《苕溪叢話》均有記載,但前者十分簡略,且未涉及東坡戲弄玉版和尚細節,后者雖提及東坡戲謔玉版和尚一事,但遠不及惠洪記載詳細、生動,故而《冷齋夜話》對蘇軾研究向縱深處推進有著重要的文獻價值。
《冷齋夜話》中也有一些篇章講述蘇軾前世今生的故事,這或與惠洪為僧人的身份有關。蘇軾前世今生之事,見卷七《夢迎五祖戒禪師》:
蘇子由初謫高安時,云庵居洞山,時時相過。聰禪師者,蜀人,居圣壽寺。一夕,云庵夢同子由、聰出城迎五祖戒禪師,既覺,私怪之。以語子由,未卒,聰至。子由迎呼曰:“方與洞山老師說夢,子來亦欲同說夢乎?”聰曰:“夜來輒夢見吾三人者,同迎五戒和尚。”子由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良久,東坡書至,曰:“已次奉新,旦夕可相見。”三人大喜,追筍輿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坐定無可言,則各追繹向所夢以語坡。坡曰:“軾年八九歲時,嘗夢其身是僧,往來陜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托宿,記其頎然而眇一目。”云庵驚曰:“戒,陜右人,而失一目,暮年棄五祖來游高安,終于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歲矣。B15
此篇敷衍蘇軾前世本五祖戒禪師之事,該故事不見于同時期其他筆記小說,或為明代短篇白話小說《明悟禪師趕五戒》(見《喻世明言》卷三十)演繹東坡前世故事的原型。孔凡禮先生《蘇軾年譜》卷一指出蘇軾有“戒和尚”之稱,其依據便是《冷齋夜話》中的該段記載,這說明《冷齋夜話》對蘇軾的部分記載確具唯一性。附會名人前世今生或誕生奇聞的記載較為常見,即便史傳亦不例外(如《史記》中關于劉邦早年故事的記載),加上惠洪本為釋氏,將聞于他方的此類故事付諸筆端亦不足怪。可貴的是,惠洪并未將蘇軾神圣化,如卷十《三君子瑕疵可笑》就指出,東坡雖讓人敬畏,卻也并非完人:“東坡議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其視死生如旦夜爾,安能為哉!而欲學長生不死。”B16認為東坡既時刻有殺身成仁之想,卻又學長生不死之術,此類“顛倒”、矛盾之舉,令人發笑,展現了惠洪尊重本心,不盲目攀附名人的個性。《冷齋夜話》還有許多關于蘇軾好友前世今生故事的記載。如卷七《張文定公前生為僧》,講述的便是張定公在滁州大悟前生事的故事,蘇軾為其重寫,“題公之名于其后,刻于浮玉山龍游寺”B17。《冷齋夜話》中的此類記載為我們進一步了解蘇軾及當時的文壇風尚提供了文獻支撐。
三、《冷齋夜話》中的蘇軾詩文創作及詩論
《冷齋夜話》記載了較多蘇軾詩文創作的軼事。如卷一《東坡留題姜唐佐扇楊道士息軒姜秀郎幾間》詳細地記錄了蘇軾被貶儋州期間題姜唐佐扇、楊道士息軒及姜秀郎幾間楹聯及詩作的創作場景:
東坡在儋耳,有姜唐佐從乞詩。唐佐,朱崖人,亦書生。東坡借其手中扇書,大書其上曰:“滄海何曾斷地脈,朱崖從此破天荒。”又《書司命宮楊道士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黃金不可成,白發日夜出。開眼三十秋,速于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望見過海席。家山歸未得,題詩寄屋壁。”又嘗醉插茉莉,嚼檳榔,戲書姜秀郎幾間曰:“暗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其超放如此。B18
其中,蘇軾“醉插”茉莉花、“嚼”檳榔之戲作“暗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一聯不見于其詩文集,這有益于補蘇軾在海南創作之遺,也有助于考察他在海南的行跡。此外,卷一《東坡南遷朝云隨侍作詩以佳之》、卷七《東坡留戒公疏》等涉及蘇軾被貶期間具體作品的創作背景及心態,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理解這些作品。
卷五《東坡滑稽》記載了蘇軾在惠州因老舉人生子及戲贈調侃之作:“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杖藜相過,村校喜,延坐其東,起為壽,且乞詩。東坡問:‘所買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為詩,其略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對于此事,《侯鯖錄》卷三與《續墨客揮犀》卷六《豐城老人生子》亦有記載,可以與《冷齋夜話》相參。但此二書記載僅限于此,惠洪《冷齋夜話》此段記載卻有一個主題,即圍繞東坡滑稽展開,因而在調侃老舉人之事后,又記錄另外兩則能夠彰顯蘇軾滑稽之作:
又曰:“世間事無有無對,第人思之不至也。如曰‘我見魏徵嘗嫵媚,則對曰‘人言盧杞是奸邪。”又曰:“無物不可比類,如蠟花似石榴花,紙花似罌粟花,通草花似梨花,羅絹花似海棠花。”B19
圍繞某一主題記錄蘇軾詩文創作情況,是惠洪《冷齋夜話》與同時期其他記載蘇軾創作之筆記小說的不同之處,體現了惠洪獨到的識見。此外,卷六《僧可遵好題詩》記載了蘇軾游廬山時在湯泉壁間見僧可遵詩所作和作之事,《東坡和惠詮詩》則記錄了蘇軾見壁間東吳僧惠詮詩而書和作于其后的過程。
惠洪《冷齋夜話》對蘇軾創作中有爭議之作亦進行考辨。《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引《冷齋夜話》:“(東坡)與少游維揚飲別,作《虞美人》曰:‘波聲拍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世傳此詞是賀方回所作,雖山谷亦云。大觀中于金陵見其親筆,醉墨超放,氣壓王子敬,蓋東坡詞也。”該首《虞美人》為蘇軾之作目前已是學界共識,秦觀亦有和作,惠洪在當時能夠實地考察辨別真偽,足見他對蘇軾行蹤及創作情況的熟悉程度。另如蘇軾與佛印、云庵克文禪師所作之簡,《冷齋夜話》均有記載,其中的部分對聯具有一定的補遺價值。
《冷齋夜話》雖為筆記小說,卻有一部分論詩之作,故而部分學者將其列入詩話一類著作。其中,涉及蘇軾詩論者如卷一《東坡得陶淵明之遺意》《東坡論文與可詩》《的對》《詩用方言》等。《東坡得陶淵明之遺意》闡發了蘇軾論詩主張“奇趣”的觀念:
東坡嘗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趣。如“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又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知悟,而俗人亦謂之佳。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如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桉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對甚的,而字不露,此其得淵明遺意耳。B20
惠洪通過正反兩類詩例,闡釋了蘇軾的“奇趣”觀。蘇軾認為,平庸者一味追求模仿,致使“一覽便盡”,而“奇趣”源于詩人的才氣,在于“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故蘇軾之作能深得陶淵明遺意。
其實,蘇軾的“奇趣”觀與其“自然”說互為表里。《冷齋夜話》卷一《的對》篇即闡發了蘇軾論詩主張“自然”的觀念:“東坡曰:世間之物,未有無對者,皆自然生成之象。雖文字之語,但學者不思耳。如因事,當時為之語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則其前有‘雍齒且侯,吾屬何患。太宗曰‘我見魏徵常嫵媚,則德宗乃曰:‘人言盧杞是奸邪。”B21在蘇軾看來,詩歌創作與世間萬物一樣,高者均為“自然生成”。在《東坡論文與可詩》中,蘇軾認為文與可“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一聯乃“拾得耳”,亦強調了“自然”在詩歌創作中的重要B22,卷四《道潛作詩追法淵明乃十四字師號》闡述蘇軾對陶淵明自然之旨的推崇,這與卷一《古人貴識其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惠洪看來,詩人“窮盡其變,不過以事、以意、以出處具備謂之妙”,但這都不是最高境界:
乃不若東坡征意特奇,如曰:“見說騎鯨游汗漫,亦曾捫虱話辛酸。”又曰:“蠶市風光思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縱掀舞。”以“鯨”為“虱”對,以“龍驤”為“漁舟”對,小大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杰之氣終不可沒者,此類是也。B23
該段出自卷四《王荊公東坡詩之妙》。惠洪此處所批評詩人追求“以事、以意、以出處”之妙,均屬人工使然,而東坡為詩之妙在于“征意特奇”,蘇軾之“奇”源于其才華,并非刻意為之,因而,此處的“奇”仍是蘇軾才華“自然”的呈現。
綜前所述,惠洪不僅與蘇軾相識、相知,有著如黃庭堅、李之儀、華光等多位共同的友人,而且他與蘇軾的經歷較為相似,行跡也頗多重疊,又曾對蘇軾足跡所到之處進行過實地考察,因而其《冷齋夜話》中的東坡記憶有著異于同時期其他筆記小說所不能匹敵的獨特之處。也正因為此一特征,《冷齋夜話》中的東坡記憶可以彌補史傳、蘇軾詩文集及同時期筆記小說之不足,可以為蘇軾研究提供有益的文獻補充,因而值得學界重視,值得我們對其進行多方位的考察、研究。
注釋
①關于《冷齋夜話》有六卷本、十卷本之說。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馬端臨《文獻通考》作六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作十卷。當前通行《稗海》本、《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均作十卷。
②〔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三,四部叢刊本。
③〔宋〕陳敬:《陳氏香譜》卷三,四庫全書本。
④唐圭璋所編:《全宋詞》、朱德才所著《增訂注釋秦觀黃庭堅詞》、馬興榮與祝振玉所校注《山谷詞校注》均將該詞置于黃庭堅名下,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也以此序為據確定黃庭堅南遷時間。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依陳善《捫虱新話》,認為該詞乃惠洪偽作。《捫虱新話》卷八曰:“據《夜話》載,洪與山谷往返諸話甚詳,而《集》中不應不見,此詞亦不類山谷辭,真膺作也。”從此段引文可知,陳善依據有二:其一,惠洪、黃庭堅往來甚密,黃庭堅集中“不應不見”該詞;其二,該詞風格與黃庭堅主流詞風不似。以上兩點均為猜測,并無文獻依據。對于第一點,從友人處補遺詩作較為常見,以此否定此詞非黃庭堅之作難以成立。對于第二點,同一作家多種文風并存亦客觀存在,故而此論亦站不住腳。此外,《四庫全書總目》與《捫虱新話》意在譏諷惠洪有攀附黃庭堅之嫌,但這不影響黃庭堅南遷之事實,因而,即使該詞為惠洪偽作,亦不影響二人于該年相見這一事實。
⑤〔宋〕黃庭堅:《山谷詞》,四庫全書本。
⑥胡仔所引之語,今傳世十卷本《冷齋夜話》不見。《冷齋夜話》并非一個版本乃學界定論,且《蘇軾年譜》等也經常采用多種詩話所引未傳世本之語作為證據。
⑦孔凡禮:《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年,第904—1135頁。
⑧⑩B11B12B13B14B15B16B17B18B19B20B21B22B23〔宋〕惠洪,〔宋〕費袞:《冷齋夜話;梁溪漫志》,李保民、金圓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4、9、42、39、43、42、43、42、44、13、35、12、13、13、28頁。
⑨《過陵水縣補東坡遺二首》,當為《過陵水縣補東坡遺一首》。
責任編輯: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