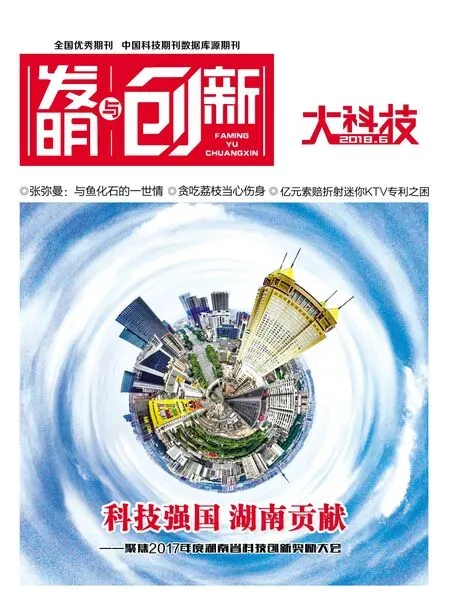張彌曼: 與魚化石的一世情
文/ 屈婷 全曉書

▲張彌曼(圖/中國文明網)
魚化石,是中科院院士張彌曼大半輩子的迷戀。
“也許,我們這樣的人都是傻瓜吧。”這位82歲的古生物學家說,“但是人類沒有‘傻瓜’可能還是不行。”
3月22日,自嘲為“傻瓜”的張彌曼在巴黎摘取了“世界杰出女科學家獎”。
該獎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歐萊雅基金會于1998年設立,每年授予全球五位為科學進步做出卓越貢獻的女性。頒獎詞稱:“她開創性的工作為水生脊椎動物向陸地演化提供了化石證據。”
逃難途中讀的書
張彌曼有一雙名震古生物圈的巧手,總能把化石和巖石沉積物準確地剝離。“我相信我的雙手還不算太笨拙。”張彌曼回憶道,“因為我的父親在醫學院工作,我看慣了那里的學生在實驗室解剖尸體。高中實驗課上,我解剖很細的小蚯蚓也不會碰破血管。”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八一三”淞滬會戰后,父親帶著全家疏散到南京,又在1940年搬遷到重慶北碚,之后又輾轉江西各地。
當時,年幼的張彌曼和弟弟妹妹尚不懂家國之恨。跋涉在贛南的路途間隙,這些逃難的“野孩子”常常潛在河里,不顧撐篙人的怒罵,迅速爬上船沿,從船尾跳到河里,把肚皮拍得生疼。
也有一些事令張彌曼萬分恐懼。日軍轟炸重慶北碚時,她和懷孕的母親躲在床下,父親趕回來時幾乎以為她們已經被炸死;她親眼見到孩子因缺醫少藥死去,自己得了瘧疾“打擺子”,頭暈眼花卻一刻不敢落在隊伍后面。她說:“這段逃難的經歷決定了我一生為人處世的取向。”
愛上了魚
1953年,17歲的張彌曼響應國家“地質報國”的號召,考入北京地質學院。1955年,張彌曼被送到莫斯科大學學習古生物學。但這位地質學專業的學生完全不知道該學哪類古生物。
“學魚!”當時在蘇聯訪問的魚類學家伍獻文先生建議張彌曼。
張彌曼聽了伍獻文的建議,從此開始了對魚化石的研究。張彌曼經常到莫斯科河岸邊的全新世沉積中采集魚化石,夜里用小船撒下橫跨莫斯科河的魚網,清晨把撞在網上的各種魚類采集下來,用來和化石進行對比,以探究古魚類同現代魚類之間的關系。
1960年,張彌曼回國,進入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工作,開始了她的尋“魚”生涯。年輕時每年約有三個月,她都隨地質勘探隊在荒野采集化石。
那時,野外勘探基本靠腿,一天步行20公里是家常便飯,很多時候只能投宿老鄉家,或在村里祠堂的戲臺上過夜。“每次身上都帶著虱子,回家進門前要先把衣服煮一遍。”回想起這些,張彌曼眼中綻放出快樂的光彩。
“不睡覺”的中國女人
約4.3億年前到4億年前,云南東部還是一片處于赤道附近的熱帶淺海。海里陸續“游”出了包括晨曉彌曼魚、斑鱗魚、楊氏魚、奇異魚在內的“明星物種”,譜寫了魚類從海洋向陸地演化的關鍵篇章。
“晨曉彌曼魚”的命名者、古魚類專家朱敏說:“它是獻給我的老師、中國肉鰭魚類研究的開拓者張彌曼女士最好的禮物。”
在生命“進化樹”上,人類屬于四足動物。大約在3.8億年前,肉鰭魚類登上陸地,演化出了四足動物。但哪一種肉鰭魚類才是人和魚的最近共同祖先呢?數百年間,這個謎在古生物學界懸而未決。
1980年,張彌曼訪學瑞典自然歷史博物館,看到瑞典學派代表人物雅爾維克用25年時間還原的肉鰭魚化石。震撼之余,她決心用最短的時間趕上去。那時,沒有CT掃描技術,想從內到外“看清”微小的魚化石,需要一種極為復雜的連續磨片和臘制模型方法。
張彌曼還原的是云南曲靖的楊氏魚。它的顱骨化石只有2.8厘米長,張彌曼需要先磨掉極微小的一塊,在顯微鏡下畫出切面圖,直到整塊化石完全磨完為止。她畫了540多張圖,把它們貼在平整的石頭上,用熔化的石蠟和蜂蠟制作出薄薄的拓片,再將剖面圖雕刻出來……最后,所有的剖面“拼裝”出一個20倍等比例放大的標本。
漸漸地,博物館里的人都知道這個中國女人“不睡覺”。于是,有人給她搬來躺椅,有人在她桌上放一束鮮花以示敬意。就這樣,她僅用兩年完成了這項研究。
按照瑞典學派的觀點,楊氏魚應有一對內鼻孔,頭顱分成前后兩半,由一個顱中關節連接。張彌曼在做這個魚標本時,既沒找到內鼻孔,也沒找到顱中關節。內鼻孔是魚類登陸時學會呼吸的關鍵構造。由于她的工作無可挑剔,人們開始對內鼻孔的起源乃至四足動物的起源有了各種新的認識。
后來,張彌曼用更多證據動搖了瑞典學派的權威,認為楊氏魚和奇異魚都是一種原始的肺魚,在國際古生物界激起軒然大波。直到1995年,世界古生物學界才普遍認同她的觀點,肉鰭魚類起源的中心地區也逐漸從歐洲和北美轉向了中國云南曲靖。
做學問要平等和誠實
20世紀90年代初,張彌曼把炙手可熱的“金礦”——泥盆紀魚類研究移交給了朱敏等年輕人,轉而研究很多人不屑的新生代鯉科魚類化石。彼時,六七十歲的她去過青海、新疆野外勘探。她說:“年輕人做得比我好。”
朱敏說,張彌曼從不責罵學生,但“她淡淡地說幾句,你也受不了的”。因為她的嚴謹是學術圈出了名的,也不會繞圈子,說出的問題往往切中要害。
“我小時候受到的教育就是平等和誠實。”張彌曼笑著說,把錯的、對的都擺出來,對科學有益處。“我很喜歡人家不同意我,也喜歡看年輕人比我們做得好。”
鯉科魚類化石分布廣、比較常見,很難在短時間內發表高質量的論文。張彌曼說:“我不是沒有思想斗爭。但沒有寂寞、枯燥的基礎工作,怎么會有真正的大發現?”
魚類分布嚴格受水系格局的限制,因此,新生代魚化石研究可以揭示諸如古氣候、古水系格局、古高度等古環境因素,進而協助重建地球變化的歷史。
近年來,張彌曼和同事在青藏高原上發現了豐富且保存精良的新生代魚化石,將有助于揭開這一地區的演化歷史。比如伍氏獻文魚全身極度增粗的骨骼,可能是隨著水中鈣鹽濃度升高而逐漸變化的,“今天我們說高原干旱化的故事,還有什么比它更生動呢?”張彌曼說著,目光炯炯。(據《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