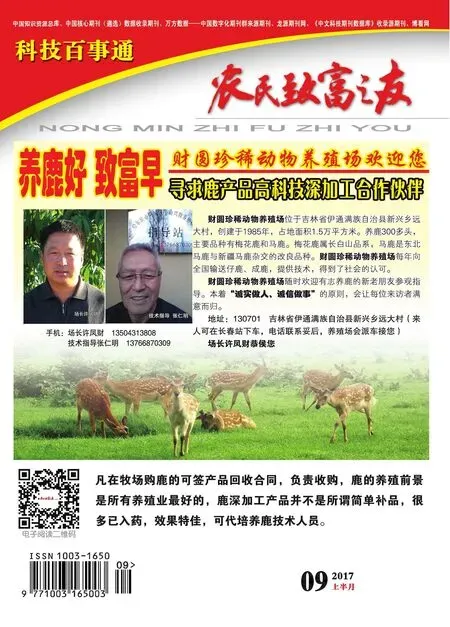山林權屬糾紛調處及確權問題探討
覃可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集體林業建設取得了較大成效,對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集體林權制度雖經數次變革,但產權不明晰、經營主體不落實、經營機制不靈活、利益分配不合理等問題仍普遍存在,制約了林業的發展。本文從山林權屬糾紛出發,主要對山林權屬糾紛調處和確權問題進行了探討。
隨著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開展,山林資源越來越被廣大人民所重視,以前的荒山荒地在現在也得到了升值,為了獲得更多更大的利益,逐漸形成了“寸山必爭,寸林必爭”的一個局面,山林權屬糾紛問題逐年上升,如果不及時的處理將會破壞人民之間的和諧。因此本文根據相關資料和經驗,對山林權屬糾紛調處和確權問題進行了探討。
1.山林權屬糾紛現狀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農村地區的居民的收入有著一個明顯的提升,基本上擺脫了貧困,解決了溫飽,但是和城鎮居民的收入相比,還是比較低的,隨著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由過去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新的社會形勢下,廣大農村地區的居民想實現增收致富的愿望越來越強,而林業資源開發潛力大、市場需求大與廣大農民生活息息相關,因此成了廣大農村地區人民增收致富的必然選擇。因此人們對林權越來越重視。林權制度的改革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確定林權,頒發林權證,隨著山林確權工作的不斷深入,引發了一些山林權屬的一些糾紛。山林確權發證工作陷入了困境。主要原因有:山林地區面積廣,具體數量難以確定;山林權益涉及的利益較大,人數也比較多;歷史遺留問題嚴重,很多糾紛難以處理。

2.山林權屬糾紛歷史緣由
我國林權制度主要經歷了四次改革:一是土地改革時期的“分山分林到戶”;二是生產合作化時期的把山林分配到一個社;三是人民公社化時期的山林集體經營集體所有;四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林業三定”土地改革時期的“分山分林到戶”。從1950年6月開始,農村地區開始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1951年4月,國家規定在確定林權歸屬之后的林權證書的發放由縣級人民政府發放,這一舉措使農民從此擁有了自己的山地和林地,調動了農民對發展林的生產積極性。
生產合作化時期的山林歸一個生產隊管理。在計劃經濟時期,林業和農業、工商業一起走上了生產合作化的道路,在1955年國家頒布了相關法律法規對農村諸如山林在內的各種經營形式進行了一些相關的規定。山林逐漸由原來的個體擁有變成了個體和集體共同所有,逐漸從原來的分散經營變成集體經營。
人民公社化時期的山林集體經營集體管理。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1960年國家對我國農村勞動力、耕地、牲畜養殖以及農業生產所需要的農具進行了固定分配使用,1961年時國家確定了山林權屬,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山林又逐漸歸集體所有。人民公社化期間內,林業統一經營管理成為了當時主要的經營模式,集中經營在一定程度上削減了農民林業生產經營的積極性。
改革開放初期的“林業三定”。1981年,國家展開了以穩定林權、劃自留山地等內容開展了“林業三定”工作,1985年,國家頒布相應的法律法規,對木材市場進行開放,允許木材自由上市,集體經營進一步開放,這一政策極大的鼓舞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人們對林權越來越重視,因為它會給人們帶來利益。
經歷了這么幾個歷史階段的發展加上政府對山林粗放式的管理和在頒發林權工作中的一些失誤就造成了現在日趨嚴重的山林權屬糾紛。
3.糾紛調處和確權的建議
3.1 歷史與現實相統一
對于歷史我們應該尊重,我們在解決山林權屬糾紛中我們應該充分了解歷史,找出存在的問題,然后與我們的實際生活相聯系,考慮這件事對我們生活的影響,以促進林業的發展和增加農村地區人民的收入。
3.2 加強思想工作
在山林權屬糾紛解決的過程中,解決好農村地區人民的思想工作對于解決山林權屬糾紛問題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只是講道理做思想工作,解決該問題的效果可能就會不盡如人意,做思想工作不僅僅是向當地居民講道理,還應該站在居民的角度,設身處地的為他們想一些解決的辦法。
3.3 健全相關法律法規
雖然我國建立了山林權屬確權的相關法律法規,但是仍然不夠完善,所以才會導致山林權屬糾紛越來越嚴重,因此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勢不容緩。
3.4 多種手段相結合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我國各級人民政府是處理山林權屬糾紛問題的主要機關,因此各級人民政府就應該運用好法律賦予的權利,同時和政府的行政權相結合,來解決這一問題。
綜上所述,山林權屬糾紛的調處和確權問題,我們要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在尊重歷史的同時,對于歷史中存在的問題,要和現在的實際生活相聯系去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