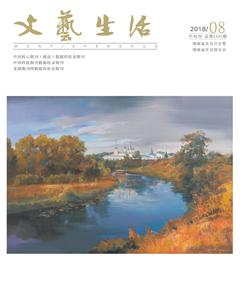當代海上偶型新探
劉全福
摘要:水流千轉歸大海。上海,坐落于雄雞腹地,瀕臨海洋,自開埠便涌進了中外無數的商賈流民、宮官草寇,并匯聚于此爭地占埠,作為上海木偶劇團前身的木偶皮影藝術,亦從民間來到都市,經過多年的演繹,在繼承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廣納百技,不斷創新,形成了獨有的海派木偶藝術。
關鍵詞:上海;偶型;探析
中圖分類號:J8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8)23-0148-03
一、前言
上世紀初期直至中葉,木偶、皮影的表演由于場地、觀眾群及票行的局限,只在微小的場地或街巷為人們演出,到了六十年代,木偶戲的表演有了量身定制的專業劇場,其構建主要為學生和兒童服務,八十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全國各地的劇場、舞臺如雨后的春筍拔地而起,特別在跨入新世紀的當代,劇院越做越高,舞臺越做越大,觀眾席與舞臺間距越來越深,木偶藝術若要走出去,且當今不得不走出去,就要適應現代的大型舞臺及觀眾的要求而改變自己,故而木偶越做越大,布景、道具亦越做越高,越來越重的木偶對演員自身的活動以及對木偶的操作帶來眾多不便,甚至無法完善表演,這就要求偶型設計,摒棄固有思維,探求新的路徑。
早期的偶型制作,多為傳承千年的木材、泥土、石灰、漿紙、絲綿、皮毛甚或銅、鐵等原料,即便著色也是取之礦石、植物等自然界的天然材料,而今社會倒逼偶型設計師,必須打開思路,尋求新的表現方式,為此形式各異的新材料、新方法應運而生,在此大潮下,上海木偶劇團除了沿襲傳統的習法之外,大量開發加入現代科技人工合成的新物質、新元素,隨著新生事物不斷涌出,現謹以我之所見,羅列如下。
二、EPS的興起
“EPS”即聚苯乙烯,俗稱白泡沫。改革開放進入八十年代,科技、文化迅速發展起來,隨著影視、舞臺劇的蓬勃興起,文藝工作者對造型表像的要求亦越來越高,作為經濟實惠、容易操作的白泡沫被廣泛應用開來,尤以雕刻制作大型偶人、動物等異形造像,“EPS”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為造型設計所采用,其質量較輕,易于拼接,可刀削鋸割,電熱絲、電烙鐵甚或電熱刀溶燙設形,省時省力,泡沫有軟,硬之分,可根據制作要求選定所需泡沫的密度,密度俞高,泡沫俞硬,過硬的板材會為雕刻帶來諸多不便,故在選材上多用18至20克左右的泡沫材料。
在制作或成型后的使用過程中,雖泡沫輕便易控,但其松軟易碎,懼怕腐蝕,故在雕琢打磨完成之后,須做表面處理,因設計要求不同,故制作表現方式亦多種多樣。
1.整形露“面”,習慣上將棉紙、報紙或其它紙質品通過調制的糨糊黏貼
于“EPS”偶型、道具表面,待完全干燥后銼平,補、批膩子,手工或電動平整研磨,打底漿、上色,因化學性質不穩定,故不可用酸性或含有香蕉水等易腐蝕的顏料、漆類等噴刷,作為偶型造像,泡沫具有多樣的可雕性,如木偶劇《尋太陽》中的“大地之母”、多媒體人偶劇《小狐貍與神奇的魔法王國》中的人形等眾多面具,涂料上漿,打磨后競鮮膜光亮、嫩如兒膚,打破了對泡沫不能細琢的傳統觀念。
2.依形做“皮”,上世紀九十年代,電視劇《聊齋》的陳列鳥獸大道具全部由“EPS”泡沫雕制,待磨光后,選用上海墨水廠出品的“777”膠水作為涂層,在泡沫表面形成膠質硬膜,對泡沫有一定的保護作用,近年來,用調制好的樹脂(俗稱玻璃鋼)亦出現在偶戲舞臺上,最近局部地方舉薦“PU”881或“PU”882作為表面處理劑,雖工藝不盡完善,還在驗質,但將來會推廣開來,我有接觸兩次,2006年4月,杭州樂園景觀劇《第一世界秀》,園主黃巧靈從美國進口兩臺機器調整稀料噴繪在雕刻好的大型泡沫山體上,因對其性質不夠了解未能做出效果,2017年,偶戲《白蛇傳》繼又采用鎧甲“PU”為試劑,涂與一佛二山,佛像如石似玉,神采亦然,然而山林異樣,經過消光又上光,效果遠非過去所能,作為化工材料,上世紀中期即被歐、美等發達國家的藝術家所采用,除了用于“EPS”之外,亦可用“XPS”、“PF”、“PE”、“EVA”、泡沫海綿等板材塑型。
3.包形易“表”,作為以布包形,古已有之,只不過隨著“EPS”的興起多個選擇而已,但與傳統的縫制、黏貼不同,除了不對泡沫產生化學反應的膠水根據需要可用可不用,另對泡沫表層劃線開口進行固定,若有同樣布料拼接,則先注意布面的正反倒順,特別是剪絨類材料,以免出現色差。
三、EVA的擴張
“EVA”是石油化工的產物,作為原油附加值,多年來廣泛運用于建筑、商用包裝、管道保溫等眾多領域,如今被木偶設計師造型所用,是近幾年的事情,談不上發明,而是無奈之舉,傳統上木偶戲及國外偶戲并非是針對少兒演出的,現今在眾人心目中被界定為兒童劇范疇且走進了大劇院,如果說木偶劇摒棄了傳統習俗登上了大雅之堂,倒不如說是現實社會商業環境倒逼偶戲“擠進了對偶戲來說超闊、超高的豪華劇場,作為木偶不得不改變自身矮小的身軀、走向高、大、上的時代,這就迫使設計師在許多劇目創作之初,就從寬大的舞臺、超遠的座距考慮,而將木偶改形換代、越做越大,為適合大型偶戲制作及表演所能承受的需求,本用于建筑、隔溫、包裝的化工合成材料“EVA”、“EPE”、“PE”板被普及開來。
(一)萬般歸屬取其輕
“EVA”從顏色分為黑、白、灰三大色,因密度、質量不同有軟、中、硬等多種規格,除特殊道具,造型設計師都會選擇中性的多為板材為基料,其輕便易琢,有一定的支撐力,如上海木偶劇團現階段制作《最后一頭戰象》場景中的大象,即是采用“EVA”所具有的屬性而選用這一材料,依據其固有的韌性由點到線、由線到面鏈接成片,拼接出立體形態,這就要求設計師不僅要有嚴謹的繪畫基礎,堅實的造型能力,還要有對材料的理解和運用能力,“戰象”從嚴格意義上講,是“結構主義”中的立體構成,雖含具象,仍是裝置表現。
“輕”是偶型設計師永不停息、孜孜以求的主題,上海木偶劇團舞美制作團隊為此對材料進行了不斷的探索、實踐,為偶型制作獲得了許多經驗,如為小橙堡《熊出沒》人偶舞臺劇《繽紛王座》之熊大、熊二做的身架,《熊出沒之奪寶奇兵》中三個強盜以及《小紅帽》中乖巧的小紅帽,奸詐詼諧的老狼,活潑可愛的小白兔,都是利用“EVA”、“PE”板的輕質特性而塑形。
(二)彎弓自便,游刃有余
“EVA”有背膠和無膠之分,除輕便易刻之外部分產品亦有延展性,如人偶劇《創世一補天》的大道具“水滴”,它是由直徑80多公分的空心圓與邊長160公分圓錐組成框架結構,外表分布眾多鏤空的海洋水生動物,內置燈光散射于舞臺,演出極具效果,同場的山石土木亦通過“EVA”得以體現,其切割方便,柔韌自如,且松弛有度。
四、EPE與XPS軟硬有別,高分子板真假貓偶
“EPE”(俗稱珍珠板)是偶型制作相較最輕的材料,性軟懼擠壓,具有一定的彈性,易切割,可用于卡通偶像或道具輔材,而“XPS”亦是非常輕的板材,依據密度有軟、硬之分,密度低的性脆易碎,高密度的則是制作五官、小道具的優選。
2014年,意大利米蘭世博會中國多媒體“全息”投影人偶劇目,上海木偶劇團為其制作偶型大熊貓,采用厚度一公分半以內、俗稱高分子板材為主料頭像造型,其優點堅挺易刻,內部減少或勿用支撐,但難點是須造型設計師要有堅實的造型基礎以及完整的空間預判能力,一次成型,此種造像既不屬雕又不是塑,還須對稱無異,故在造型前要謹慎估算,將板材劃割為眾多“橄欖”形材拼接成大頭坯模,局部還需電吹風加熱整形,如眼窩、鼻背、口形等,因材質硬挺,不易碎拼,故開料須干凈準確,每一片的粘接都應在結構上,不宜反復,若一片跑形,則影響下片的走勢,待一切成型,覆置“皮毛”、眼睛,此作優勢內部開間空闊,便于演員呼吸、散熱,在舞臺劇《熊出沒》偶型、森林國王“吉吉”、小猴等亦用此材。
五、PVG的滲透
“PVC”模片,俗稱塑料片,并不陌生,它與生活息息相關,伴隨人們走過了許多年,但言“PVS”餿影,似乎于皮影‘風馬牛不相及,童年記憶深刻的電影《青松嶺》里有段壞分子錢廣在家弄驢皮影,甚覺得滑稽好玩,時而仿其腔調,后來了解還有牛皮、羊皮影,是乎皮影都是皮的,那“PVC”的“影人”是皮影嗎?如同木偶也不都是木頭的,久而久之,堂而皇之。
“PVC”材質因配料不同亦有透明、軟硬差異,用在燈具投射,早已實施,而作為皮影整體代之,則是近些年的“發明”,上世紀90年代,上海木偶劇團徐文琪老師即著手研制“PVC”影偶,通過油性筆墨繪于塑料片上,因材料、技術受限,只做了幾個短小劇目,如《雞斗》、《狗拿耗子》、《羚羊飛渡》,后來亦有了用復印機彩印圖片于塑料片上,但仍是小幅形象。
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上海木偶劇團為此編排了超大的皮影戲:《三國演義》之《草船借箭》、《空城計》、《驅獸破蠻》、《孔明燈》四個劇目,影窗寬大,許多景片設計居高2至3米,影人亦到80公分,偌大的場景,眾多的人物、繁瑣的道具,顯然對設計、制作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此時計算機打印技術已經成熟,經研判吾摒棄了以皮制偶、手繪敷色的傳統模式,改用干勾墨稿、水性顏料韻色、通過電腦調整,噴打在“PVC”上,制作的片劑清晰透明、顏色豐富,虛實易于變化,并首次在皮影構架上,研發、裝置了兩個滾筒帶動“PVC”膠片,利用人工循環往復的操縱,使河川、大地動了起來,奔騰的江水、搖擺的戰船,逝去的草地、行軍的人馬,在行動中緩急自如,且節奏、儀式感極強,解決了長期以來人物碎步,江河死水微瀾的尷尬表演,飛馳的野獸與逆向劃過的大地形成對比,在隆隆的戰鼓聲中,使畫面更加緊張、刺激,扣人心弦,而最讓吾首肯的,還是“PV”色彩的飽和度以及表現時空虛實的多樣性,它有油畫的渾厚、敦實,兼有水墨的氣韻流動,雖皮影影人講究的是側面率、橫向交集,但依據西洋一點、二點透視規律將景物一層層鋪開,構成由實到虛、色彩由濃到淡,結合國畫留白或散點透視法則使空間更加深邃、立體,突出主題以達到筆斷意連、事半功倍的效果,此戲舞臺著重強調歐美與日式結合的繪畫風,參插中國淡彩水墨技巧,使畫面更加含有意境而引人入勝,在上海世博會長達幾個月的演出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15年,為了劇目的發展、中外文化的交流,劇團創排了又一部大型皮影戲《花木蘭》,偶型、景物仍為“PVC”材質,造像為剪紙或黑、白板報風格,萬墨叢中一點紅為補充的煙火、血滴,具上世紀60、70年代裝飾感,與世博會皮影戲《三國演義》色彩新穎亮麗、以面帶線形成反差,其插入的投影動畫如老酒新漿,打破了傳統皮影戲平行移動、不可直面進退的常規,運用投影技術伴隨多變的音律,使畫面熱烈激昂、人物豐富飽滿,讓人耳目一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在《花木蘭》戲中插入老虎的表演,個人覺得有破古典名著的美學,對兒童可否產生影響且存待論。
六、紙偶的掙扎
紙偶:用皮紙、紙板或其它紙質材料經人為加工組成的立體偶型,其特色棱角分明,難于細琢,相對于其它偶像,紙偶乃一尷尬的品種,沒有滅絕,亦沒能發展,只是設計在感到需要時閃現一見,紙偶來自古時祭祀,并非起源于曲藝舞臺,在民間,因喪葬習俗用紙偶為俑,以奉逝者。2009年秋,吾到皖北參加葬禮活動,一悼者對手藝人扎制的紙馬、兩紙人順口塞食熟米、饃塊,并拍打偶面、念念有詞,而2018年仲春,吾見黑龍河、松花原葬禮活動再無紙俑、紙馬、紙轎,替代的是畫工粗糙、制作簡易、機械化生產的“PVC”吸塑產品。預計不久的將來,紙藝冥品這種流傳數百年的扎紙技藝恐怕也隨哀者逝去了。
舞臺上紙偶難得一見,2001年,上海木偶劇團以紙制偶,制作新戲《特殊使命》,劇中的偶型用折紙方式拼接,因材質受限,偶面不夠細膩,難捕捉性情亦缺少變化,故演出一段時間后便放棄了,現唯一可演的為早期折紙小戲《東郭與狼》,東郭先生臉型呆板,面目迂腐、線條僵硬的文人下士,而狼則眼面夸張,狹腰垂尾,動作猥瑣而不失兇殘本性,隨著梆子的慢板及急速劃過的弦音,整個劇目緊張不失詼諧,可見造型設計對狼、人物、劇情的藝術感悟與堅實的表現能力,是偶類劇目中的一朵奇葩,成為上海木偶劇團經典小戲傳演至今。
七、布藝的惆悵
布擬:布以為偶還是不以為偶?
舞臺上以布擬偶,因形式較真,上海木偶劇團自詡日布擬,由上世紀九十年代資深老師陳為群先生在劇目研討會上首倡提出,經過眾創作人員長時間的探索、實踐,一部亮麗、新穎的布擬音樂劇《春的暢想》應運而生:在幽暗神秘的舞臺深處,一塊塊布片猶如阿拉伯飛毯飄忽著款款而至,隨著毛毛蟲的閃現,兩只大公雞“脫胎”而出,并四目對峙,略思后拔地而起,相向廝殺,伴隨跌宕起伏的音樂,掙扎到精疲力盡、無力爭斗時發覺毛毛蟲在逃,此時小肚雞腸的雞公公意識到只有合作才能共贏,隨之互諒互讓,分而食之,皆大歡喜,喧鬧之后是一片寧靜,少許,低沉的旋律從遠處隨風而至,一片片彩云(布片)隨著器樂的鼓點瞬間羽化為色彩斑斕、著裝時尚的妙齡舞女,伴隨熱情激蕩的舞曲,跳起了強勁、奔放的迪斯科,其動作夸張,節奏歡快,令人安奈不已,激情過后,一曲優美的曲牌、弦樂二胡獨奏《春江花月夜》讓人陳定下來,漸漸陷入迷境,月光如水,玉蘭花慢慢綻放,一襲綾羅綢緞斜肩而下,彰顯出江南才女、荷塘月下引弦靜思,獨享良宵的美妙情景。
《春的暢想》猶如巨石砸向大地,在空洞的舞臺上掀起塵埃,開創了先河,其一:首次它以纖弱、輕盈的織品詮釋了布擬在木偶舞臺、木偶應盡的能量,且形神兼備,惟妙惟肖,在國內外取得了眾多獎項,并作為經典保留劇目時常傳演,其二:首次在國內打造黑光舞臺,運用紫外光映像與常規燈切光、隔離投射方式凸顯偶戲,取得完美效果,亦為其它劇目、院團所借鑒,特別是在上海木偶劇團偶劇、黑影戲《海的女兒》中運用熒光燈顯像技巧益使畫面豐富多彩,亮麗可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色彩高度。
折紙為偶,揮布擬人,如果說紙偶是上海木偶舞臺的一朵奇葩,布擬則是最具表演意義的海派偶像,其擬人似人,擬物似物,角色的轉換就在彈指一揮間,令人目不暇接,可謂是偶界的新秀。
八、3D的發掘
“3D”即英文THREE DIMIENSIONS,意指三維立體空間,日常最早見識的是電影《阿凡達》,此后,“3D”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2014年秋,設計大型多媒體劇目《小人國與大人國》,劇中不僅大量運用二維繪畫投影模式,且首次嘗試三維立體、即“3D”噴打技術,打印了些許小偶,材質為“ABS”,即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三元共聚物,其面光潔如脂,勾畫色彩鮮亮,取得了良好效果,為制偶工藝的改進和提升,奠定了基礎,此后在大型文化傳承劇目《創世一補天》一戲中,仍采用“3D”方式打制水滴等道具,因設計與制作協調不多,且對材料配比了解不夠,故產品抗摔打能力不足,還須進一步了解和實踐。
“3D”可用的材料有數百種,其打印范圍廣泛,如發達國家制造飛機、汽車,大部分零部件都采用“3D”打印,隨著計算機數碼科技的發展,“5G”的到來,“VR”、“AR”的突破,打印即將迎來無窮大的發展,亦為木偶舞臺的拓展帶來機遇。如今,“全息”折射影像作為造型藝術跟進了木偶舞臺,木偶,做為流傳千年的古老傳說,披上了皇帝的新裝,綜上所述,乃偶戲造型之一論,權作索引。
上海,一座開放不久、起調頗高的都市,匯聚了眾多的“宮廷”及“民間”藝人,木偶,無論高雅還是鄉俗,經歷了世間最漫長的紛爭年代,仍隨時代在延展,可見其堅毅的生命力,普世的“真”、“善”、“美”,值得留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