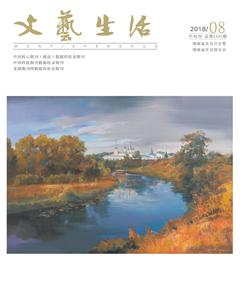淺析海派文化系統對都市與鄉土矛盾關系的調和
王翠玲
摘要:物質文化條件的劇變,促使文化系統重新調和,都市文化的產生無法脫離具有孕育作用的鄉土,其發展卻不會囿于低速率的鄉土。人們在都市與鄉土的割裂與粘著狀態中掙扎、尋找,逐漸形成了一套融入市民趣味的安然自處的海派文化系統。帶有新的時代、地域特色的海派文化系統實現了與鄉土文化的對接與跨越,散發出新的生命力。
關鍵詞:海派;文化系統;都市;鄉土
中圖分類號:TP391.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8)23-0189-02
一、前言
“鄉土是家園、是童年、是母親,都市是什么?都市僅是罪惡的享樂之所,從《子夜》到《日出》,大部分新文學作家嫌惡上海,”鄉土情懷從實實在在的土壤中被孕育,被不少人懷想,從情感而論,都市更多地被當作鄉土的對立面而存在,是人們謀求生計的無奈之舉。
伴隨上海物質文化條件的劇變,都市與鄉土曾經在上海這座典型的大都市刀鋒相見,都市與鄉土既割裂又粘著,既對立又統一。文化系統經歷了一個重新調和的過程,形成了一套融入市民趣味的安然自處的海派文化系統,為人們在繁華的都市中筑建了新的精神家園。
二、都市與鄉土的割裂
上海在褪去小縣城的舊裝后,重新裝扮,披上華衣美服,跳起了上海的狐舞步,以全新的姿態呈現在世人面前。人人都加入到這個行列中來,仿佛在進行一場狂歡,全然不見往日鄉土的氣息,散發著洋氣。
都市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新式的舞廳、影院、跑狗場……各類娛樂場所一應俱全,百貨商店琳瑯滿目的商品消費著人們的口袋,裝飾著人們空虛的外殼,繁華的表象背后散發出肉的氣息、物的氣息。《海上花列傳》中含有較多的繁華與糜爛的都市景象的描寫,郭沫若在一首題為《上海印象》的詩里更是直接描寫了一幅“都市游魂”的畫面:“游閑的尸/淫囂的肉/長的男袍/短的女袖/滿目都是骷髏/滿街都是靈柩/亂闖/亂走。”
現代都市的速率帶給人們巨大的壓力,都市的繁華也吸引著人們去放縱、享受,不管是什么原因,在燈紅酒綠的花花世界里,人生被作為消費品極度享用,欲望得到了實實在在的滿足。移民人口們早就遺忘了自己來自哪里,跳脫了舊的環境與舊的自我,人們的靈魂似乎無所歸依,鄉土的“根”漂浮著,不知道去哪里尋找,遙不可及。
新文學作家表現出對上海這座都市的極度厭惡,認為它是畸形的。1926年,高長虹寫到:“我實在誠懇地厭惡上海的小商業的社會。它已經不是鄉村了,但又沒有走到城市,它只站在歧路上徘徊。鄉村的美國都市的美,它都沒有,所以只顯現出它的丑來”。高長虹認為上海既不是鄉村也不是城市,鄉土與都市割裂開來。
面對物質條件的急速轉向和異質文化的大量涌入,任何一個社會都難免要經歷一個調和的過程,在迷茫中打轉,從表象上看來,都市與鄉土是對立的,人們跳脫鄉土來到都市,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三、都市與鄉土的粘著
都市文化的產生無法脫離具有孕育作用的鄉土,都市與鄉土無法完全的割裂開來,二者始終粘著在一起。
上海作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它的文化中融入了太多的移民文化,外來人口將自己所在鄉土的文化帶到上海這片土地上,雖然是不自覺的文化遷移活動,卻對上海的文化產生了不可否認的影響,呈現出碎片式的記憶,在日常的行為中表現出來,在語言中流露出來。
文化的異質性難免會產生碰撞,各方鄉土文化交流與融合的過程會產生新的適應上海本土的文化,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博厄斯提出了文化動力的概念,伴隨著移民的過程,鄉土文化成為都市文化產生的內在動力之一。
都市與鄉土的粘著還表現為人們在狂歡過后產生的失落感,都市的步伐不會為任何人停止,當融入它的節奏的時候,人們會被它的速度追趕,像機器一樣運轉、狂歡,當人們疲憊的時候想要尋找的東西就是鄉土。對鄉土隱約的懷想是對歸屬感的找尋,鄉土是安放情感的處所,主要表現在因時間、空間的遙遠而萌生美感的家鄉。
郁達夫在《春風沉醉的晚上》里描寫了一個上海香煙廠的女工與一個流浪型的現代知識分子的短暫相遇,文中的女工就是這樣一類帶有殘碎鄉土文化記憶的群體,他們進入這座都市,用勞動力來換取生活,也將她所在的鄉土文化帶到這片土地,她是不是也會聽著齒輪的轉動聲想念著什么呢?
在海派文學的創作中,劉吶鷗試圖展現都市背景下人的失落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都市,描寫都市人們的一次偷情、尋歡,甚至男女邂逅,類似于《麥田的守望者》,沈從文指責劉吶鷗的寫法“邪僻”。
上海張國安教授曾指:“就對生活的觀照態度來看,劉吶鷗和沈從文,應當說是在同一地平線上的。善惡美丑是非等等,這些價值觀念,在他們單純和全然的觀照態度中純屬多余。不過,劉吶鷗的單純和全然是都市化的,沈從文則散發著泥土的芳香。劉吶鷗和沈從文,都缺完美,他們最吸引人的是單純和全然。”劉吶鷗通過對傳統倫理道德的反叛呼喚著自由,何嘗不是對鄉土的眷戀。
四、海派文化實現的對接與跨越
城市的文化基礎薄弱,如果將它與鄉土割裂開來,它似乎只是漂浮的建筑物。然而二者是無法割裂的,城市的拉力吸引著帶有鄉土文化背景的人們,在經歷了城市本土文化與異質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后,人們會不停地尋找可以安放情感的新的文化土壤,一代或者兩代,一種個人的新的鄉土文化就在城市里扎根了。
四十年代,張愛玲把現代主義和傳統傷感言情小說對接,以她照人的才華描寫生活氣息濃郁、人情味道十足的世態小說,運用了一種婉轉的是非觀——善中有惡、惡中有善,更加貼近現實層面,創造了一種“活”的境界,集海派文化之大成。“婉轉的是非觀”與海派文化多元包容的特點相呼應,較為典型地展現在《金鎖記》里的曹七巧身上,她的丈夫是個“骨癆”病人,七巧正常的情欲受到嚴重壓抑,以致人格變態,她設法破壞兒女的幸福婚姻,可憐又可憎,舊式大家庭氣息的熏染,已使她人性扭曲。張愛玲試圖挖掘人的本性,揭示善惡常常是集于一體的,給處于糜爛與繁華都市的人們不安的心靈一劑解藥,打破了通俗文學善惡各執一端的傳統。
張資平、葉靈鳳—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張愛玲,海派文人經歷了一個從物質表象掙扎出來的過程,海派在市民趣味中逐漸體現文人趣味,體現悲劇型感受,“從一件小事里看到一個永恒的真理”,就像張愛玲所展現的浮世的悲歡。
再比如“海上畫派”,其繪畫題材多取自歷史故事、神話傳說和民俗生活,大量使用諧音、暗喻等手法,表現了趨吉避兇、多子多福、加官進爵等主題,對美好前景的向往與憧憬正如潛藏在心底的鄉土情懷一樣,讓人們可以在新的環境中安然自處,感受到溫暖與希望。
以“速度”著稱的上海有著繁華的經濟外貌,將身處其中的個體都卷進快速發展的漩渦中來。上海的海派文化系統具有多元包容與趨時求新的特點,它樂于接納一切時尚、新奇、高效率的東西。城市中的個體猶如一抔抔陶土,在高速旋轉中被塑造得愈發精致,可是,再精致的藝術品依舊離不開泥土的質地。
五、結語
海派文化把握了市民階級的心理,在敢于創新的基礎上,注重表現平、俗,尤其是海派文學,展現了都市與鄉土的融合過程,通過描寫與現實緊密相連的家庭中的瑣碎,完成了與都市中個體的對話,開拓出都市民間的新空間。
上海的海派文化系統是現代中國城市文明的一種典型模式。“新天地”在規劃改造中提出了修舊如舊的理念,已經認識到城市的魅力在于它獨特的歷史,以及它獨特的地域特色。都市可以是鄉土,但是,需要經歷一個鄉土意識逐漸轉變的過程,由地域上遠方的鄉土變為對城市的依戀,實際上是意識與情感的承載體的轉移,可以作為新的都市文化價值觀念來思考。
都市文化的產生無法脫離具有孕育作用的鄉土,都市文化的發展卻不會囿于低速率的鄉土。融入新的時代、地域特色的海派文化系統實現了與鄉土文化的對接與跨越,散發出新的生命力,鄉土在都市中有了新的表現形式,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