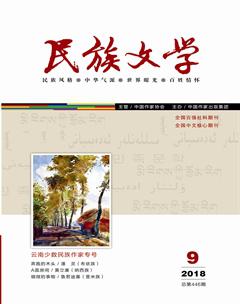重返根性的文學書寫
楊榮昌
云南有著蒼茫雄渾的高原山川和縱橫奔騰的大江大河,多達二十六個世居民族就生活在群山懷抱和江河環繞之中,孕育了綺麗多姿的民族文化,是文學產生的情感酵母。長久以來,一代代的各民族作家背負著傳承創新民族文化的歷史責任,以絢麗的筆觸點染奇幻的高原色彩,放飛恣意的文學想象,用嫻熟的漢語書寫出與高原氣韻相匹配的優秀文學作品。這期《民族文學》的“云南少數民族作家專號”選取了有代表性的二十余位云南作家作品,涵蓋小說、散文、詩歌等體裁,無論是精神意旨還是創作手法,都可見出云南多民族文學鮮明的美學特性。
小說:朝著歷史與現實的雙向掘進
云南的群山之中隱藏著諸多野史,不為正統所記載,如一顆顆遺落的珍珠,散發著迷人的文學魅力,那些血質與野性,哀婉與纏綿,展露了歷史的詭譎與人性的光芒,有待作家拂去塵埃重現其風采。潘靈的《奔跑的木頭》就是一篇向歷史深處探尋秘密的小說,寫的是西南邊地的民族歷史,一位柔弱又帶殘疾的年輕女土司與覬覦她資源的其他土司化解干戈的故事。年僅十八歲的阿喜土司接受了漢文化的教育,知曉天下大義,只身深入虎穴,以膽識和聰慧讓兩個家族免于打冤家。與她相襯的,是沉默無言的背腳(背負患癱疾的土司的男青年)木頭,他終日一言不發,卻胸藏萬響驚雷,知道審時度勢,憑借超強腳力忠心護主,一主一仆,演繹出一段驚心動魄的壯烈往事。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在少數民族地區施行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影響西南邊地數百年,小說通過復雜的矛盾編織,將這一制度所構成的歷史成因、現實困境和發展規律呈示出來,以文學的形象性保存了歷史的肉身。小說敘事疾徐有致,情節敘述波瀾涌動,懸念迭出,有較強的畫面感。精確的人物語言描寫貼近了各自的角色特點,畢摩的斯文儒雅,管家的市儈勢利,撒瑪土司的驕橫跋扈,甚至艄公的見利忘義,約涅頭人的陰險狡詐等,都在符合各自身份的言語舉動中顯現,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小說多處深度呈現了彝族人的心理意識,是最具文學張力的部分。眾所周知,民族的心理結構一經形成便難以改變,優秀的寫作者會精心采擷這些獨有的文化資源,發揮審美想象,創造出新的文學形象和文學世界,而不走平面化、獵奇化展覽民俗文化的路子。潘靈是布依族,卻對彝族文化心理有著深度的感知,體現了在云南多民族文化的互相滲透中,作家博采眾長的能力。
伊蒙紅木的《遷居》聚焦脫貧攻堅的社會熱點,表現了作家對于時代重大命題的參與能力。在當下,同類題材得到了越來越多作家的關注和書寫,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綻放其光彩。這類作品普遍寫出貧困地區人民思想觀念的變遷,他們從之前的猶疑、觀望,甚至安土重遷,不愿遷居,轉向主動朝著新的生活進發。在此過程中,利益的糾葛,如爭當貧困戶、分配扶持款、贍養老人,以及新舊思想與生活方式的交織碰撞,成為作品表現的重點,尤其是貧困群眾不愿搬、不敢搬的心理,值得社會關注和作家探究。由此可見,改變鄉村的落后面貌,需要將精神的改造與物質的提升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只有精神素質跟上了物質文明的進步,談同步小康和鄉村振興戰略才成為可能。而在《遷居》中,伊蒙紅木開掘了另一個角度。在眾多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堅韌的信仰已融入每個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他們習慣與神交流,達染老人每天去佛堂朝拜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他不愿遷居并非擔心物質生活的不適應,而是新的寨子與佛堂相隔較遠,不便于每日的祭禮。讓他最終同意遷居的,是廟里大和尚的一番規勸,某種意義上這是遵從于佛的旨意。由此可見,民間自有一套完整的倫理法則,規約著人們的意識和行為,其堅韌性、彌散性,是對主流政策的有效補充。小說提出了一個命題,即在脫貧攻堅成為“天字號”工程的當下,如何做到尊重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特別是重視其精神信仰問題,在搬遷新的居所的同時,也考慮到相應的宗教場所的設置,這比起艱難的思想動員,要有效得多。伊蒙紅木對于社會問題的思考,與云南民族地區諸多群眾信仰宗教的現實相聯系,在社會的普遍性中發現個性,并以小說的形式提出對于社會難題的解決辦法,體現了作家的社會責任。
散文:呈示民族變遷的心路歷程
中國傳統散文講究精粹、典雅、醇厚,無論載道還是怡情,散文永遠是心靈的藝術,真誠是其不變的核心。云南散文作者的審美視角,永遠離不開大自然給予的豐厚饋贈,這里的一方山水,一片風情,本身就是一首優美的詩歌,或一篇字字珠璣的美文。行走在這片高原大地上,即使不濃墨重彩,不刻意雕飾,真情流溢出的,也多是極品佳作。散文家卞毓方曾這樣形容張家界:“張家界絕對有資格問鼎諾貝爾文學獎,假如有人把她的大美翻譯成人類通用的語言”,移之于云南高原的奇山異水,如若用散文或詩歌的筆觸將其“翻譯”出來,也將構成一部彰顯大美的皇皇巨著。
黃立康的散文《A面房間》可視為成長的隱喻,他以個人生活經歷為線索,展露出人生各階段那些有記錄意義的片段。作品中大量出現的獨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符碼,寄寓著這個民族深層的文化心理,要走進民族的精神深處,探究深邃駁雜的精神景觀,離開這些物化的載體是不可能的。除了日常的生產生活物象,還有那些世世代代口耳相傳保存下來的文化典籍或民俗習慣,如姓氏、語言,它們是成百上千年形成的文化積淀,有著極高的辨識度,是民族的共有家園,通過它可于萬人叢中找到同道,于歷史長河中捋清脈絡。可貴的是,作者看到了民族文化在現代性進程中不可避免的衰退景象,那些保留了無數代人的傳統正在散失,家園、溫情、血性、歌謠等等珍貴的東西都在消散。語言是最具文明積淀的標志,民族地區的民間話語來自于生產生活之中,顯現著民間智慧,比文縐縐的漢語成語更有感染力,而大量語言的散失不啻一種連根拔起的抽空狀態,一個民族的凝聚力也將面臨分崩離析的危險。袁智中的《最后的獵王》書寫了一種普遍困境。在生產力極端落后的年代,狩獵使得一代獵王受到寨子里的無上尊崇,那時人們靠勇武取勝,狩獵能給族人帶來溫飽和美味。但隨著時代的進步,追求自然和諧的生態環保觀念逐漸成為共識,加之物質條件的改善,人們從之前的狩獵中逐漸轉化到農業生產和務工上來,獵王已不再是桂冠。這是一種革命性的進步,作家從族人思想觀念的變化中,看到的是時代的發展。只是伴隨發展而來的,是另一種困境,淳樸的村落開始變質,年輕的族人將黑發染成了黃色或紅色,視千年流傳下來的禁令于不顧,開吃狗肉,對自然神靈不再敬畏,不再懂得感恩。這確實兩難,一方面我們需要全球化,在現代性潮流中獲得平等發展的機會,共享人類文明的成果;一方面發展又多以散失特有文明為代價。作家是人類的先知,他們的感觸往往能夠超越表層,抵達本質,既可感知到山地民族融入現代世界的渴望,又能體會他們轉型中不可避免的陣痛,物質和心靈都面臨新問題。在此過程中形成的民族的自尊與自負,交織成復雜而猶疑的心理。作家對社會變化帶來的各種困境的敏銳捕捉和誠實的書寫,表達了對于人類走向更美好未來的渴望,其中對道德的拯救,離不開傳統的文化方式,如用雞頭骨卦做賧叫魂,寄希望于民間倫理的規約感召,體現出深沉的文化責任。
相較而言,李俊玲的《那些長在記憶里的蠻竹》在題旨上就沒有那么沉重,這是一篇立意謀篇、遣詞造句、敘事抒情都頗為考究的作品,彌漫著久違的鄉野之氣。作家以充滿情感的文字表述,將蠻竹的普通樸實,野性生長,與這片土地上的人物性格形成對照,竹子極強的生命適應性和對于人類生產生活的適用性,象征著人們的堅韌品質。以竹子為媒介,勾連起對昔日生活的追憶和對阿公的懷念,形成了淡淡的文化鄉愁。由蠻竹聯想到山里人的堅毅隱忍,由物及人,轉化得自然妥帖,沒有絲毫的矯揉造作,升華了散文的內在品格。云南寫作者,給人的印象大致是木訥隱忍,不懂投機取巧,不會嘩眾取寵,只是以自己誠摯的感悟,默默抒寫內心或隱或顯的愿望和想象,以文字建立個人與世界之間的秘密聯系。散文的寫作方式略顯樸拙,卻字字含情,是作者心靈觸角的延展與探尋。
詩歌:為山河大地賦形
云南文化的多樣性決定了精神的豐富性,各民族對精神世界的追崇形成了萬物有靈的觀念,在這片大地上漫游,可以隨時與那些消遁的神靈不期而遇,誘使你進入一片充滿神秘色彩的天地。文學,某種程度上充當了誘引者的角色。作家們匍匐于山河大地,傾聽歷史的聲響與地母的回音,以駁雜多彩的文學書寫,重構深沉燦爛的地域美學。作為彝族詩人,吉克木呷的詩歌是本民族心聲的吐露,詩中占卜、畢摩施法等意象,是本民族心理的呈現,習俗、禁忌等都有著明確的寓意,詩歌成為人與神對話的重要方式。這個民族有著鮮明的火崇拜,在遠古的祖先生活時代,是火驅逐野獸,讓食物變熟,烈焰象征著山地民族剛烈豪爽的性格,最終人也是在火的簇擁下走向另一個世界。火伴隨著彝族人從出生到去世,因此,對火的感情是深沉而熾烈的。當代彝族詩人寫火的作品很多,如吉狄馬加的《彝人談火》,普馳達嶺的《木炭彝人》,沙馬的《火葬地》等,火已成為彝族詩歌一個永恒而經典的意象。吉克木呷的《彝人的火》,從具象化的火聯想到它的前身——樹木,以及群山和高原,“而我知道/不管經歷或未曾經歷的火/火焰都是向上的/就像變成火之前的那些樹木/長出樹木的那些山/托起群山的云貴高原”,與火有關的所有物象都以向上的姿態生長,象征著這片大地之上蓬勃昂揚的精神品格。詩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體現在對祖先歷史的朝覲上,后來者在祖先的精神感召中獲取前行的力量,族譜的保留與存續之所以受到重視,就因為它是連接民族歷史的紐帶。《族譜上的那些名字》喻示了在一個個具體的名字后面,呈現的是鮮活的祖先行跡,是家譜將那些動人的家族往事串連起來,形成一種凝聚精神的載體。這種向著民族歷史的自覺靠近,也體現在李鐵柱的《我的族群……》中,詩歌重現了祖先開疆拓土的壯舉,捕捉到一個民族的歷史余溫,隱含其中的,是對傳統中充滿血質的豪氣性格的呼喚。
少數民族詩人同樣具有強烈的世俗情懷。超玉李的《丈量》是一名游子對故鄉的守望,身在他鄉,滿目陌生,他將身邊之景與記憶中的故鄉相對應,以兩者的相似性來襯托對故鄉深沉的愛戀。一遍遍梳理異鄉點與點的距離,其實是一遍遍思念故鄉的每個角落,帶有鄉野出身的淳樸與執拗。在現實中生活,面對民族存續下來的服飾、禮儀與文明,他的心中掠過一絲隱憂,在同質化的時代潮流中,這些民族文化的結晶是否能逃脫被遺忘的命運?《慢》是對親人的追憶,肉身在塵俗中存活數十年,卻終歸于塵土,一代又一代,莫不如此,在與漫長時間的對峙中,人類永遠是自然規律面前的弱者。這份帶有哲學意味的啟悟,增添了詩歌的藝術厚度。《無名英雄像雨滴》是面向革命先輩的致敬,當紅色的火苗燃遍千里彝山,火種卻遺落在了滇西北的群山深處,肉身已隕,精神長存,“無名英雄像雨滴/潤澤江山”,自有一份對革命先輩的感喟。李天永的詩歌有一種濃得化不開的情愫,他以綿密的語言針腳編制出春、夏、秋、冬的四季規律,每個季節的特點都在豐富的聯想中被固定為一種意象,形成繁富的意象群。詩歌以奇警的比喻,調動意象發揮其指代功能,形成內涵豐富的語義空間,給人以新穎之感,體現了成熟的表達技巧。當然,如果語詞的指向性更明確,不過度追求詩意的漫溢,而是化繁為簡凝結為一種更簡練的話語表達,他的詩歌會有更疏朗的風格。果玉忠的《信仰》描繪的是滇中地區獨特的精神現象,人們對精神之物的迷戀與未知,使神與鬼的認識處于一種混沌狀態,是敬還是畏,只能按照自己的主觀意識進行自我建構。詩人透過物化的表層,直面一個地區的精神狀態,進而提煉出一種重視靈魂寄托的滇中人文景象,觸摸到了這片土地的神髓。
整體來看,云南的詩人很少耽于內心的自我沉湎,他們總是把詩歌寫在大地上,與群山對話,和神靈共舞,祖先的歷史是靈魂的棲居之地,現實的故園又是安妥俗身之所,在歷史與當下的對比中,尋找情緒釋放的空間,那些帶有圣潔和純凈色彩的語詞有如神啟,不期然翩翩而至。這樣的書寫超脫于個人狹小的心靈空間,走向一種闊大的精神之境,詩歌有著輕盈靈動的風采和重金屬般的質地。
重構具有人類普適性的價值體系
多民族文學的發展離不開更為宏大的民族文化作背景,中華傳統文化精華是由各民族處于金字塔尖的優秀文化共同構建的,其文化經典在今天依然有著強大的感召力和濡染力,為文學創作提供著豐富的資源支撐。如果民族文化遺落了,便將是精神的掛空,其打擊是徹底性和毀滅性的。面對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傳統異化,作家們普遍保留了足夠的警惕,發出了憂傷的嘆息。他們深知,保存民族文化,就是保存民族的精神之根,只有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才能有更深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因此,無論是挖掘歷史還是關注現實,都極為重視傳統文化之根,將筆觸伸進民族精神的內部,把探究民族共有的情感結構作為書寫重點,體現了一種集體無意識,這是民族作家文化自覺的表現。他們以本民族的思維來考量世界,用漢語表達對于社會和時代的觀感,異樣的敘述方式,呈現出不同于漢文化的異質美學,閃爍著晶瑩的思想光彩。這種從民族根性出發的文學書寫,天然地帶有一種深度意識,有著接近真理的無限可能性,因為它不臣服于市場的利益驅動,不馴順于肉體的欲望法則,文學就是心靈的自由表達,在當下的文學語境中,這是至為稀缺的文學質素。
從民族文學的內在屬性來看,民族性是區別于他者的最鮮明的文化標識,是獨一無二的,可以對同質化的文學主潮形成對抗或矯正,它有著最堅硬的質地,亦是最能觸碰柔軟心靈的部分。民族性的表述離不開民族的文化符碼,它們體現在生產生活環境、器具、儀式、民俗中,通過小說敘事場景和詩歌意象群的表現,轉化成民族心理的探究與建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民族作家要有意識地向著更高的標準邁進,只有將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價值倫理接通人類共有的價值體系,經由文學形式的提煉與升華,民族的思維與觀念才能轉化為中華民族共同遵循的價值準則。這并非主動放棄自我的價值立場而消弭個性,事實上,任何一種立場如果不是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都容易走向偏狹和極端,我們需要的是通過作家的闡揚,將本民族與生俱來的那些優秀質素,化為共同資源,以豐富人類的精神寶庫,如鹽消融于水般無形,卻增加了水的鹽分。從全局來看,民族作家對世界變化的感知似乎比漢族作家要更加敏感,基于幾個角度審視:一是自然生態的惡化。作家們大都出生于鄉野之地,是典型的自然之子,人與自然是一種唇齒相依的關系,環境的惡化最能牽動他們的神經。二是人心的變異。全球化的潮流勢不可擋,地球日益變成了一個村莊,迫于現實生存的壓力,閉塞的村寨也將打開大門,村寨中人外出,同時也迎接外來之人,在此轉型過程中,難免受到不良風習的影響,有的甚至吸毒等,與古老的鄉村倫理相違背,村莊沒有守住底線而出現了價值坍塌,昔日的淳樸被激進的利益追逐所踐踏。三是文化消亡的感傷。從文化的自我屬性來看,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沒有貴賤之分,是各族人民在漫長勞動探索中形成的物質與精神的結晶,值得我們珍重。但從文化流布的范圍和現實影響來看,卻有著差別,在占有絕對優勢的漢文化面前,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不同程度地受到挑戰,作為藝術觸角敏銳的群體,作家率先感知到了這種困境。多篇作品明確揭示出,文化的危機從服飾的變異、語言的消亡、生產生活習俗的變更開始,直至鄉土倫理的崩潰。因此作家才會不遺余力地疾呼,甚至以近乎決絕的姿態來開展文化的保衛戰。
從情感體認到文學書寫,云南的民族作家們總是從家鄉開始他們對于世界和時代的理解,家鄉情結正成為傳統文化的最后棲息地,作家的文學夢想始終伴隨著故鄉情懷。對故鄉的守望,又常與生態問題相連接,生態元素往往占據著重要位置,而不僅僅是用來襯托人物的心理和作為背景。在一個人神共居的環境中生活,自然注重精神世界的建構,越是相信神靈的存在,便越是懂得敬畏和內斂,越能加持內心,注重修煉。他們以敬畏之心敘述生態的神圣性,以人與社會發展的復雜關系寫出人與自然的動態關系,這些從不同文化背景出發并進行多民族書寫的比較,可以使人們對民族文學的美學特質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在新的歷史時代,我們期望云南的民族作家能夠以豐厚的文化資源作依托,堅守民族之根性,對傳統文化進行吸收與接納,在批判性繼承的基礎上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文學本體上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從而產生更寬廣意義上的文化認同和審美價值認同。期望他們以創造新的藝術個性和美學品質,書寫出與這個時代、這片土地相符合的汪洋恣肆的生命氣象。
責任編輯 安殿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