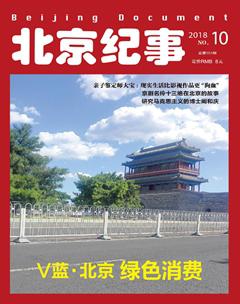滑竿隨想
師永祥
我坐過井岡山的滑竿,也坐過武當山的滑竿,但最有意義的還是在峨眉山上坐滑竿。
到峨眉山旅游,當你在報國寺下車后,從去伏虎寺路上開始,隨處可見滑竿等候在道旁。他們不斷打量行人,主動上前問:“坐滑竿不?坐起安逸啊!”“你沒有坐過滑竿吧?欣賞一盤嘛!”
他們熱情,態度溫和,無論你打聽山上什么,百答不厭,簡直是一部活字典。他們真正把你當作“上帝”捧抬在普通人之上,滿足你的好奇心理。

滑竿,最初見到它是在電影里: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在峨眉山辦軍官訓練團,由報國寺去新開寺來往都坐滑竿,前呼后擁,排場很大,十分威風。1935年8月,蔣介石攜夫人宋美齡去游金頂,弄來十多乘滑竿式大轎,在衛隊全副美式裝備荷槍實彈下,浩浩蕩蕩經清音閣直往仙峰寺、九老洞游憩。
解放后,有很長一段時期,峨眉山上不準抬滑竿,認為是人抬人不平等。現在抬滑竿的人并不這樣認為,他們說:“我抬你,你給了我報酬,合情合理。”“兩人抬一人,輕拋拋能掙的錢不掙,在家受窮,心情更難受。”“有了錢,我們同樣可以到城市去欣賞別人,看演出,進音樂茶座。”
峨眉山這支滑竿隊伍非常寵大,約有400多架,800多人。戰線之長,人員之多,在國內各大旅游勝地首屈一指。從山腳到金頂,沿途可見,招之即來。旅游旺季時,沒有一架滑竿放空過一天。他們非常彪悍,一個個都是“飛毛腿”。在1992年舉行的首屆國際登山大賽中,200多名中外運動員角逐,獲一二三名者都是抬滑竿的。第一名從清音閣到金頂,僅花了2小時56分。
你不要以為年老體弱,腳傷腿痛的人才坐滑竿;你不要顧慮坐上滑竿會遭惹議論;你不要認為他們的花言巧語是為了敲竹杠,就感到厭惡,他們都是本地村民,有的還是在職職工退職來抬滑竿的。他們都有檔案,一旦被客人舉報就會被取締。他們中的好人好事層出不窮。當你走得氣喘吁吁、大汗淋漓、腰酸腿痛時,會羨慕坐滑竿的,會把求助的眼光投向他們。你看,坐滑竿的有老有幼,有許多青年男女,還有外賓。為了減少旅途勞頓,那就請你坐上滑竿欣賞吧。
半仰半臥,閃悠悠,涼颼颼,山光水色眼底收,十分舒服,簡直是一種享受。漸漸入佳境,步步取勢。他們學著南腔北調同你搭訕,大多還會說幾句外語,抄各種口音說笑話,讓你坐上開心。他們或介紹風土人情,或講各個寺廟的動人傳說,笑談近幾天山上發生的軼聞趣事,讓你捧腹大笑。若抬上的是一位年輕單身女郎,見眉毛描得又黑又濃,唇膏涂抹得紅艷艷的,臉蛋粉白,兩人發出一句暗語,將滑竿輕輕向上一拋,有點坐秋千的味兒。這一拋逗惹得年輕女郎嬌滴滴道:“師傅,再來一次嘛!”“好,讓小姐再欣賞一次!”滑竿再拋高一點,年輕女郎又媚聲媚氣道:“好好玩啊,請師傅再拋一下!”“小姐,再拋就要加錢嘍!”“加就加嘛!”小姐從小皮包里用兩個小指拈出一張新票子。滑竿每向上拋一次,加一次錢,雙方心里都樂滋滋的。他們自己也說,天天抬滑竿,同各色人都打交道,增加了見識,獲得不少新信息。我想,他們是在參與社會。天天抬上抬下,走上走下。他們抬起的是一個小社會,走的也是一個小社會。
他們腿腳矯健,非常合拍,隨山道千回百轉,滑竿一上一下,閃悠閃悠,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韻。若是走在平地上,不晃不蕩,躺著觀山望水,飽覽風光。疲憊時可閉目養神,樂以忘憂,享有任何交通工具無可比擬的風趣。

你別看滑竿隊伍中有五六十歲以上的,他們同樣兩腳生風,可以從報國寺一口氣抬上山頂殿,顯示了峨眉山人的硬功夫。坐上滑竿,你還可以聽到詩一般的對話。前者說:“路窄一根線。”后者答:“騎得馬來射得箭。”(前者告訴后者要當心,后者答前者請放心。)前者喊:“明晃晃。”后者答:“水凼凼。”(前者暗示后者有水坑)前唱“青石在晃”,后和“穩踩不上當”。“路中一枝花”,“有屎莫踩它”;“左邊起了云”,“右邊站個人”。(有人迎面而來,提示后者讓路,走左邊)過木橋時前唱:“三木兩條縫。”后和:“穩踩中間腳不漏。”前唱:“懶洋坡。”后和:“慢慢梭。”坐在滑竿上聽起來,簡直是詩一般的語言,令人拍手叫絕。
唯有上陡坡,不坐滑竿領悟不出人生中某些真諦。九十九道拐、鉆天坡,非常險陡,坐上滑竿腳高頭低,看那天、那山、那樹木、那來往游客,全都顛倒過來了。你會驚嘆:抬滑竿的苦力人,竟有顛倒乾坤之力!雖然短暫,這會在你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不可泯滅的印象。
坐滑竿上峨眉山,才有感慨:“坐上了滑竿,方頓悟到有個‘顛倒的世界!”
(編輯·韓旭)
hanxu71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