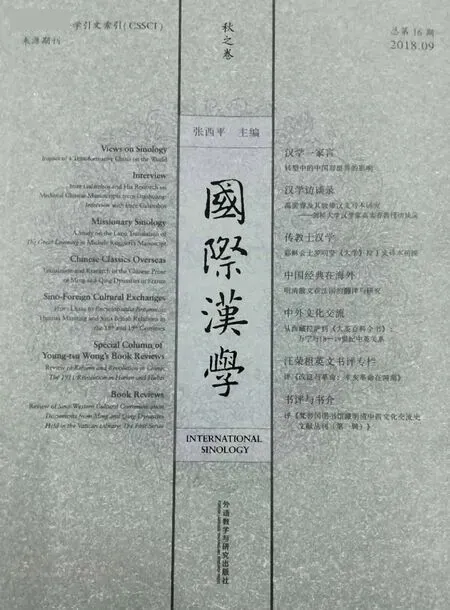《真光初臨》中的晚清潮州婦女形象*
□
簡 ·亨特(Jane Hunter)認為依據文獻來論述19世紀鄉村女信徒的經驗特別困難,因美國差會檔案中沒有中文檔案資料,也極少有中國基督徒寫的自傳材料。①1900年后有些官宦人家的女兒就讀于教會學校,通過她們留下的文字記錄,我們才能直接了解到,在世紀之交皈信基督教和傳教經歷對于中國女性有著怎樣的意義。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a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30.簡·亨特著,李娟譯:《優雅的福音:20世紀初的在華美國女傳教士》,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264頁。信教婦女常常以數字或一個模糊群體的形式出現在差會的報告、書信和各種記錄中,甚至在本地教會用中文編寫的歷史文獻中亦是如此。借用胡衛清的話,女性基督徒是群體性“隱身”和“失語”的。②胡衛清:《苦難與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經驗》,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69—105頁。美北浸信會(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簡稱 ABMU)③1845年,美國浸信會分裂為美南浸信會和美北浸信會。在汕頭傳福音的是美北浸信會。女傳教士斐姑娘(Adele M. Fielde,1839—1916)④又稱旨先生娘,因其過世未婚夫為Cyrus Chilcott。在《真光初臨》(Pagoda Shadows)⑤Adele M. Fielde, Pagoda Shadows: Studies from Life in China (3rd edition). Boston: W. G. Corthell, 1885. 中譯本:斐姑娘著,郭甦譯:《真光初臨·潮汕實錄一八七三》,香港:硯峰文化出版社,2016年。在郭甦譯本之前,學界一般將Pagoda Shadows稱為《寶塔的陰影》。在本文中,若無特別標明,提及Pagoda Shadows指的都是1885年英文版本。一書中以16位早期女傳道(Bible-women)⑥潮汕新教教會中的“女傳道”是指經過專門的圣經培訓,以協助外國女傳教士傳教的當地信教婦女。被派到世界各地的新教傳教會一般稱她們為“Bible-women”。參見蔡香玉:《晚清民國潮汕地區基督宗教女性研究》,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75頁。的證道詞(或稱生平自述)為主體,兼及其他婦女的記述,這些證道詞均由本人口述,由斐姑娘翻譯整理,⑦“These studies were made during a residence of ten years in China, with a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of the people, and an opportunity for close observation of their social customs. The autobiographies and the stories are exact translations of verbal narrations given to the author in the Swatow dialect.” 1885年版扉頁作者斐姑娘語。并加以必要的說明,是非常有價值的史料。在某種意義上,可彌補此前提到的資料缺乏境況。
斐姑娘于1873年進入潮州宣教,1889年以健康為由,永久辭去傳教士的職務和身份。她在潮州曾創辦明道婦學,主要從事培訓女傳道的工作。斐姑娘精通當地語言,且在潮汕地區居住十余年,常常走訪鄉間各處,可以近距離地體察當地的民情、社會風俗。因而,她能較準確地把握和理解當地社會和婦女的各種生活處境。斐姑娘出版了數本有關潮汕話、潮州社會、婦女和風俗的著述,①Adele M. Fielde, Dictionary of Swatow Dialect. Swatow, 1875; First Lessons in the Swatow Dialect. Swatow: Swatow Printing Office, 1878;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83; Pagoda Shadows. London: T. Ogilvie Smith, 1887; Chinese Nights’ Entertainment: Forty Stories Told by Almond-eyed Folk Actors in the Romance of “The Strayed Arrow”. New York & London: The Knickerbocker Press, 1893; A Corner of Cathay:Studies from Life among the Chinese. New York & London: McMillan & Co., 1894; Chinese Fairy Tales. New York & London:The Knickerbocker Press, 1912. (re-issue of Chinese Nights’ Entertainment)其中涉及當地婦女的有《潮汕夜話》(Chinese Nights’Entertainment)②斐姑娘著,郭甦譯:《潮汕夜話·潮汕老古一八七三》,香港:硯峰文化出版社,2016年。和《天朝一隅》(A Corner of Cathay)③斐姑娘著,郭甦譯:《天朝一隅·潮汕見聞一八七三》,香港:硯峰文化出版社,2016年。,而《真光初臨》則是以潮州婦女為主體。該書于1884年出版,在美國和英國教會界引起轟動,前后共出版六版。④第一版于1884年在波士頓出版,隨后又連續再版,1886年第五版。1887年,該書又在倫敦出版。本文主要關注斐姑娘在《真光初臨》中所塑造的晚清潮州婦女形象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此處需要說明一下,因斐姑娘接觸和觀察的對象主要是潮州婦女,故本文標題使用“潮州婦女形象”,但晚清中國社會有其一致性,斐的文字呈現而西方接收的實際也是某種“中國婦女形象”,因而后文亦會使用“中國婦女形象”。
中國教會歷史學界有關本土婦女信徒的研究中,郭佩蘭對中國婦女和基督教的關系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探討,⑤Kwok Pui-lan, 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 1860—1927.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2.魯珍晞(Jessie G. Lutz)則研究了廣東客家地區婦女信徒的皈依與經驗。⑥Jessie G. Lutz and R. Ray Lutz, Hakka Chinese Confront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1850—1900. New York: M. E. Sharp, 1998.胡衛清是首位利用《真光初臨》的學者,他強調《真光初臨》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并指出從中可以看出早期基督徒在信仰抉擇上的艱難處境,并提出嶺東地區女傳道與平信徒領袖在教會體制中的邊緣地位,造成了她們在教會活動中的“隱身”和“失語”現象。⑦胡衛清、姚倩璞:《圣俗之間:近代潮汕地區的基督徒與教會》,《韓山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第17頁。胡衛清:《苦難的模式:近代嶺東地區女基督徒的傳道與證道》,載陶飛亞編《性別與歷史:近代中國婦女與基督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3—303頁。該文后略作修改,作為第二章收于氏著:《苦難與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經驗》,第69—105頁。同時,他提醒在利用《真光初臨》中16位女傳道的證道詞時需謹慎,因為這些證道詞所表現出來的敘述方式很可能是信教婦女在斐女士等教會人士的現代性思想啟示之下所形成的一種特定話語模式。⑧胡衛清:《苦難與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經驗》,第104頁。此外,胡氏還將16位女傳道的英文證道詞翻譯為中文。⑨胡衛清:《附錄二:嶺東浸信會婦女傳道及女信徒傳記》,《苦難與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經驗》,第329—371頁。胡氏翻譯的是1887年版第106頁至190頁的內容。李榭熙和凌愛基則對晚清潮州女信徒皈信的經歷與女傳道群體各有論述。⑩Joseph Tse-Hei Lee, “Gospel and Gender: Female Christians in Chaozhou, South China,” in Pioneer Chinese Christian Women:Gender,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Mobility. Ed. Jessie G. Lutz.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Ling Oi Ki, “Bible Women,” in Pioneer Chinese Christian Women: Gender,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Mobility. Ed. Jessie G. Lutz.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2010.蔡香玉在其博士論文《晚清民國潮汕地區基督宗教女性研究》,即后來修改出版的《堅忍與守望》中,從地方史和女性史的角度,關注基督宗教進入潮汕地區后給當地社會,尤其是當地女性所帶來的影響。?蔡香玉:《晚清民國潮汕地區基督宗教女性研究》,2011年。蔡香玉:《堅忍與守望:近代韓江下游的福音姿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真光初臨》中的女傳道12位有英文名字,另4位則是無名,因熟稔潮州話,蔡香玉在其博士論文中對16位女傳道的中文姓名進行了考證。?《晚清民國潮汕地區基督宗教女性研究》,第99—107頁。
此外,杜娟華(Dusica Ristivojevic)曾撰文探討1884年至1885年婦女傳教雜志《婦女工作在中國》(Woman’s Work in China)中的中國婦女形象,她研究認為西方婦女對于中國婦女的評判是建立在中國婦女接受或拒絕西方婦女基督教教導的程度,①Dusica Ristivojevic, “They Are Just like the Generations Past: Imag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Women’s Missionary Periodical Woman’s Work in China (1884—1885),”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8. 2, 2008, pp. 143—161.其研究對筆者有啟發的意義。王秀云提醒運用女傳教士在中國所觀察、書寫的史料時,要注意史料與觀點的平衡問題。②王秀云:《有關西方女傳教士與中國婦女的幾個歷史問題:從文獻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000年第8期,第237—252頁。
總體而言,關于本土女信徒,尤其是女傳道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但在整個中國基督教歷史研究中仍有待拓展。檢視以往研究斐姑娘的著作(尤其是《真光初臨》)的成果,已涉及女傳道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婦女入教的原因、女傳道的地位、女傳道的培訓及其社會影響等方面,特別是胡衛清前引文已有對女傳道生平自述話語模式的反思,但該文畢竟只是從《真光初臨》中節選了部分個案做簡要分析。本文試圖厘清《真光初臨》在晚清基督教文本的流通與生產中的地位及意義,并結合斐姑娘的生平及《真光初臨》寫作的背景,檢視斐姑娘筆下的潮州婦女形象是如何建構與呈現的。
一、女傳教士有關晚清中國婦女信徒書寫的文字出版
最早來華的單身女傳教士是來自英國的獨立女傳教士艾迪綏(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她于 1843年將巴達維亞(Batavia,即雅加達)的華人女子學校遷至寧波,停留至1861年離開。③E. Aldersey White, A Woman Pioneer in China: The Life of Mary Ann Aldersey. London: Livingstone Press, 1932.斐姑娘是早期來華的單身女傳教士之一,是晚清首位到潮州宣教的單身女傳教士。對女傳教士的需求和這個群體的產生一方面是源于當時中國的性別隔離傳統,男傳教士不能直接與中國本土的婦女接觸,另一方面源于一些女性信徒的傳教熱情被19世紀初美國基督教發生的第二次宗教大覺醒(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喚醒。最初各傳教組織要求那些想赴海外宣教的單身女性嫁給單身傳教士以獲得傳教的機會。④李期耀:《失范與重構:潮汕浸禮差會女性傳教人員社會性別演變(1860—1903)》,《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 9期,第 83頁。Dana L. Robert, American Women in Missio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ir Thought and Practice.Mancon, Georgi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8.后傳教士夫人自覺無暇身兼照顧家庭和服務婦女的雙重重擔,遂向母會呼吁派遣單身女士。單身女傳教士在華主要從事與婦女有關的工作,如開辦老婦學、⑤當傳教士在汕頭為成年(甚至是老年)女性開辦圣經培訓學校時,當地教外人士對這種新鮮事物感到好奇,并戲謔地稱其為“老婦學”。李金強、陳潔光、楊昱升:《福源潮汕澤香江:基督教潮人生命堂百年史述》,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21頁。小女學,⑥潮汕人稱將為女童提供教育的學校為“小女學”或“女學”。去鄉村布道和探訪,舉辦祈禱會,在未有女醫療傳教士之前,有時也要充當醫生的角色施醫贈藥,傳教士夫人們則從旁予以協助。一般而言,女傳教士要服從男傳教士的權威和指導,與男傳教士掌握在地差會話語權和服務當地男性區別開來。因本國女性信徒貢獻大量的自由捐獻,各差會紛紛組建婦女會,派遣和支持女傳教士,因而來華女傳教士的人數持續增長。截至1890年,在華的西教士中60%是女性(包括傳教士夫人和單身女士)。⑦并非所有的女傳教士都是由婦女會派出,其中中國內地會早于1878年已開始派遣單身女傳教士到中國內地。R. G. Tidemann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1800 to the Present, Volume Two. London & Boston: Brill, 2010, p.182.
在華的傳教士需要定期寫信給差會匯報工作的情況。如美北浸信會要求所有傳教士每季度向委員會秘書匯報一次,每年至少寫四封信,而且要求內容最好具體化。⑧Overseas Letters: J. N. Murdock to M. E. Thompson, July 25, 1877. J. N. Murdock to Sophia A. Norwood, April 22, 1878. J. N.Murdock to C. H. Daniells, July 31, 1883. Overseas letters from the Corresponding Secretary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ABMU to missionaries, 1865—1891. The American Baptist Historical Society Archives, Mercer University, Atlanta, Georgia.這些信件常常全文或節選部分發表在傳教的有關刊物上。此外,傳教士還會寫信給支持其傳教的個人或團體匯報捐獻的用途和工作取得的進展。女傳教士多匯報其婦女工作的有關情況以獲得繼續的資助。如叔未士夫人(Henrietta Hall Shuck,1817—1844)于信中多次提及她在澳門和香港家中開辦學校的女學生的情況和她們的進步,以獲得繼續在家中辦學的經費,雖然常不足以維持。她的信中亦提及當時中國人主張女童不受教育以及纏足、訂婚的習俗。①Thomas S. Dunaway, A Pioneer for Jesus: The Story of Henrietta Hall Shuck. Nashville, Tennessee: Broadman Press, 1947,p. 57, pp. 73—74, p. 125.裨治文(Eliza J. Gillett Bridgman,1805—1871)夫人隨夫第一次回美國休假的間歇,完成《中國的女兒,或中國的家庭生活素描》②Eliza J. Gillett Bridgman, Daughters of China; or Sketches of Domestic Life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New York: Robert Carter &Brothers, 1853.一書,書中按時間順序記述了她抵中國后與丈夫一起在廣東、上海的所見所聞及傳教經歷。其中提到她在廣東先后得兩名本地女童Alan和Ah-yee,在家中教育她們,后帶去上海。裨氏夫婦在上海的家中開辦了裨文女塾,最初是走讀學校,后擴成寄宿學校,也接收走讀學生。1851年,女校有走讀生8人,寄宿生12人。③Ibid., pp. 178—194.書中對中國婦女的有關情況略有提及,如殺女嬰、纏足、婚禮等,還提及裨夫人在廣東時多次拜訪富商的女家眷。書的扉頁附了一張12歲的金妹的照片,1851年裨氏夫婦將其一同帶回美國。④Ibid., pp. 223—225.而同在潮州傳教的英國長老會第一位單身女傳教士李潔姑娘(Catherine Maria Ricketts,1841—1907)于 1878年抵達汕頭,在潮州傳教,直至1907年在當地去世。她于1881年在汕頭開辦的培德婦學與斐姑娘之明道婦學一樣,專門培訓女傳道,她在英會的地位與斐姑娘在美會的地位不相伯仲,都是負責婦女事務的領頭人物。李潔姑娘留存許多文字,多發表在英國長老會女教士協會(Women’s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的官方刊物《他邦的姊妹》(Our Sisters in Other Lands)⑤Our Sisters in Other Lands: A Record of Mission Work among Women (1881—1918).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藏英國長老會檔案,檔案號:PCE FMC Archive Series II Box 27 & 28.上,從1879年第1期直至1906年第108期,幾乎每期都有她的文章或消息,主要是定期匯報她的女傳道工作、鄉村探訪等,其中對她指導的女傳道們的個性、脾氣和家境有簡略介紹。她在《他邦的姊妹》上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悼念一位名為添弟嬸(Thiam-ti Sim,1835—1905)的女傳道,文章滿懷感情地記錄了她的生平和傳道經歷。添弟嬸曾任培德婦學的教師,協助女傳教士培訓女傳道,且赴鄉間傳道多年。⑥Catherine M. Ricketts, “The Only Precious Thing is Goodness,” Our Sisters in Other Lands, VII. CVIII, 1906, pp. 202—203.而另一位同在潮州的女傳教士娜姑娘(Sophia A. Norwood,1844—1918),先在美會服務八年,負責女傳道工作,后因成為傳教士夫人轉至英會,亦在《他邦的姊妹》上發表了許多醫院的女病人對福音有興趣或皈信基督的故事。⑦Sophia A. Lyall, “Story of Sok-Hi,” Our Sisters in Other Lands III. XL, 1889, pp. 98—100. Sophia A. Lyall, “A Visit to Chowchow-fu.” Our Sisters in Other Lands III. XLII, July 1889, pp. 136—138. Sophia A. Lyall, “Hospital Sketches No. I.—A Beggar Woman’s Story,” Our Sisters in Other Lands III. LI , 1891, pp. 40—42. Sophia A. Lyall, “Hospital Sketches—No. II. Story of Mrs. U,” Our Sisters in Other Lands IV. LII, 1892, pp. 58—59. Sophia A. Lyall, “Hospital Sketches, No. III—Mrs. Chun-hiang,”Our Sisters in Other Lands, IV. LV, 1892, p. 104. Sophia A. Lyall, “Hospital Sketches, No. V.—Mrs. Theng-hua Sim’s Story: Or How One Woman and Family Found the Light,” Our Sisters in Other Lands V. LXVIII, 1896, pp. 59—61.以上只是節選晚清部分女傳教士的文字來展現當時女傳教士有關中國婦女書寫的大致情況。
《真光初臨》的大部分內容是由斐之前寫作的一些小文章或報告匯集而成。就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早在《真光初臨》成書以先,其中五位女傳道的故事早以文章或小冊子的形式流傳,⑧為方便論述,本文提及的女傳道中文姓名統一據蔡香玉之考證。參見蔡香玉:《堅忍與守望》,第290—298頁。她們是:杜瑞(Aunt Luck,另譯為 A Tui),⑨Adele M. Fielde, “The Story of A Tui,” July 1874.吳 銀 花(Silver Flower),①Adele M. Fielde, Silver Flower’s Account of Herself. Boston: Woman’s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878.林 水(Keepsake, 另稱 Sui),②Adele M. Fielde, How One Chinese Woman Became a Christian. Swatow: Swatow Publishing Office Company, 1878.陸快(Speed,另稱 A Khue)③Adele M. Fielde, “A Khue and the Orange Garden,” The Helping Hand VII. 11, 1878.和黃寶容(Tolerance,又稱 Sister Yong)。④Adele M. Fielde, How “A Familiar Spirit” was Ejected from Sister Yong’s Family. Swatow: Swatow Publishing Office Company,1880; Adele M. Fielde, Sister Yong’s Family and the Familiar Spirit. Boston: Woman’s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881. 兩本小冊子的內容完全一樣。《真光初臨》前半部分有關中國婦女、阿四(Number Four,又稱A Si)童年生活、纏足、本土婚禮、未曾謀面的新郎、迷信的不便、灶神、佛教女尼、藥鋪的內容也在早前以小冊子或文章的形式出版,⑤Adele M. Fielde, Women in China. Boston: Woman’s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Adele M. Fielde, “Child-life in China: The Story of A Si,” Adele M. Fielde, “Foot-Binding,”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LX. 9 (September 1880), pp. 333—335.Adele M. Fielde, “A Chinese Wedding,”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LVII. 3 (March 1877), pp. 61—64; Adele M. Fielde,“How a Chinese Bride Saw Her Husband,”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LIX. 1 (January 1879), pp. 5—6. Adele M. Fielde,“The Inconvenience of Heathenism,”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LX. 3 (March 1880), pp. 64—65; Adele M. Fielde, “A Family God,”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LIX. 2 (February 1879), pp. 33—34; Adele M. Fielde, “Chinese Nuns,”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LVIII. 10 (October 1878), pp. 366—367; Adele M. Fielde, “A Chinese Drug-Store,”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LX. 8 (August 1880), pp. 301—302.最后一章有關科舉考試的內容亦曾發表在《浸信會傳教雜志》(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簡稱BMM),⑥Adele M. Fielde, “China as a Mission-Field III,”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LVI. 2 (February 1876), pp. 37—39.這些內容基本完整地保留在《真光初臨》中,只是詞句稍有刪減。另外,筆者比較1884、1885、1886和1887年版本的《真光初臨》,發現前三版本完全相同,而1887年版較1884年版則做了以下改動:(1)將1884年版的第11章和12章合為一章——《偶像的影響》;(2)1884年版第21章陸快的自述傳記的標題《竹龍》在1887年版中改為《陸快和竹龍》;(3)1887年版比1884年版增加最后一章《中國婦女工作的范圍》和倒數第三章《銀花的自述》;⑦Chapter XXXIII, “Silver Flower’s Account of Herself,” and Chapter XXXV, “The Sphere of Women’s Work in China,” Fielde,Pagoda Shadows (1887), pp.179—190, 203—208.(4)1884年版書中有16幅木刻版畫,1887年版沒有。由此可見《真光初臨》一書得益于斐姑娘平時的素材積累,比較其前后版本,1887年版做了較大改動。
二、中國女信徒在基督教傳統中的形象生產
恰如黎子鵬所指出的,晚清的基督教敘事文學作品(中文)表達了其作者所在年代獨特的意識形態和世界觀。⑧黎子鵬編注:《晚清基督教敘事文學選粹》,新北市:橄欖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xviii頁。筆者認為傳教士有關中國婦女的文字作品(英文)亦表達了他們當時的意識形態和世界觀。據美國歷史學家賀池遜(William Hutchison)所稱,傳教士們一般陳述其出任傳教士的目的是“為了服務和犧牲”,顯示他們對被傳教地人們視作其自己文化之一部分的宗教的“傲慢和輕視的態度”。⑨William Hutchison, Errand to the World: American Protestant Thought and Foreign Mission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 2.當時在傳教士中間廣泛流行“異端”或“異教主義”(heathenism)一詞,該詞含義甚廣,“既指非基督宗教,也指非基督教的文化、習俗和制度”。據姚西伊所言,在大部分傳教士看來,異教主義即等同“黑暗、野蠻、落后、迷信、腐敗分子的墮落”,非基督宗教不僅充滿錯誤,而且使信眾陷于奴役和壓迫之中。只有基督的福音才能帶給他們光明和真理,并使他們的社會和文化獲得進步和文明。他指出,隨著西方在海外勢力的持續擴張,傳教士們的這種心態在19世紀下半期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后更加強烈。⑩姚西伊:《基督新教傳教士對中國傳統宗教態度之演變》,《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2006年第41期,第15頁。此外,19世紀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大多具有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世界觀,以西方為中心來看待異族宗教文化的思想反映在他們的部分作品當中。①黎子鵬編注:《晚清基督教敘事文學選粹》,第xxii頁。薩義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指出,所謂的“東方”和“西方”觀念,是對于“他者”(the other)的斷定與確認,而“東方主義”則是在文化,甚至是意識形態的層面,將“異己”的部分,表現與再現為一種論述模式(discourse),而這一論述模式受到制度、字匯、學術、意象、教義,甚至是殖民的階層體制與殖民的風格等的支持。②薩義德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臺北:立緒文化,1999年,第2—3頁。晚清在華的傳教士所作的有關中國的基督教文本,包括書信、報告、文章、小冊子及著作等,即是在以上意識形態和世界觀的影響之下。除此之外,傳教士們的文字還要受制于用來獲取繼續傳教的經費。差會組織則要負責編輯傳教士們的書信、報告等發表以從信徒和慈善家處獲取資金支持其國外宣教事業。③Eric Reinders, Borrowed Gods and Foreign Bodies: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magine Chinese Religion. Berkeley, 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18—19.傳教士們的“在那里”(being there)賦予他們的文字直接和權威的印象,④Ibid., p.xiv.但其實這些文字背后有其特定的目的和選擇性,而受眾和讀者——母國差會、信徒、慈善家以及對海外傳教有興趣的人士等則視其所描繪的為“真實”的中國,從而無形中建構了一種特定的中國形象,其中包括中國婦女。
一些長于文字的晚清在華傳教士往往試圖對中國做通論式的介紹,包括地理、人口、語言、歷史、特點、習俗、宗教、政府等,其目的一方面是向西方介紹中國,另一方面是為增加基督教群體對在華傳播福音的興趣,促進在華的基督教文明。⑤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I. New York & London: Wiley and Putnam, 1848, p. xvi; 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 I.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65, p. ii; Arthur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th edition.New York, Chicago & Toront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4, p. 330.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和郭實蠟(Karl Gützlaff,1803—1851)是這方面文字的鼻祖,⑥Robert Morrison, 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 Macao: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7;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Boston: Crocker & Brewster,1838; Karl Gützlaff,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Vol. 1. New York: John P. Haven, 1834; Karl Gützlaff,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Vol. 2.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4.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倪維思(John Nevius,1829—1893)、 明 恩 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等亦有大部頭的著作貢獻。⑦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s. I. & I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3;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2 Vol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65; John Nevius, China and the Chinese.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869; Arthur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th edition.他們涉及中國婦女的文字有其一致性,對婦女地位的判定與郭實蠟一致,認為中國人輕視妻子,婦女受男性的宰制,地位低下,⑧Karl Gützlaff,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Vol. 1, pp. 45—46.他們在書中對有關性別隔離、殺女嬰、早訂婚、纏足、婚俗及婚姻生活的內容的記敘一般比較線條或概論性,盧公明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則處理得相對細致。⑨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 I, p. 46, pp. 65—141;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Vol. II, p. 239;Nevius, op.cit., pp. 237—256; Smith, op.cit., p. 179, 183, 189, pp. 201—203.而麥克納布(R. L. McNabb,1855— ?) 的《中國婦女》⑩R. L. McNabb, The Women of the Middle Kingdom. Cincinnati: Jennings and Pye; New York: Eaton and Mains, 1903.是筆者所見除斐姑娘《真光初臨》一書之外,專以中國婦女為主題的著作,作者坦陳參考了許多前人的著作,包括衛三畏、倪維思、明恩溥等。該書系統敘述了有關中國婦女各方面的內容,還簡介了基督教會在華有關婦女的教育、醫療和孤兒院事業。書中提到一對福州富商夫婦先后信教,富商夫人張謝氏(Sia Ahok)?姓名考證參尹翼婷:《近代中國婦女宣教運動研究——以東方女子教育促進會和英國圣公會女部為中心》,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第114頁。曾受邀赴英國為教會作宣傳,是上層階級的婦女基督徒,她信教之后致力于在富有的夫人們中間傳播福音。①McNabb, op.cit., pp.124—143.以上是傳教士有關中國的主要著作中書寫婦女形象的部分。
相對而言,1884年出版的《真光初臨》在傳教士有關中國婦女的書寫中比較特別。首先,作者是一位女傳教士,上面提到的有關中國的著作的作者都是男傳教士,正如男傳教士主導傳教地的工作一般,出版書籍一般也是男傳教士更多。同在潮州傳教的男傳教士留有著作的有:汲約翰(J. C. Gibson,1849—1919)著有《在華南的傳教問題與傳教方法》,②J. C. Gibson, Mission Problems and Mission Methods in South China: Lectures on Evangelistic Theology, 2nd edition. Edinburgh&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02.師雅谷(Jacob Speicher,1866—1930)著有《在華十字架的征服》,③Jacob Speicher, The Conquest of the Cross i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7.耶士摩(William Ashmore, Sr.,1826—1909)著有《在華傳教》④William Ashmore, Missions in China. Boston: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1907.等,以上三本皆與傳教有關,或偏重在華南傳道、布道的方法及問題,或結合自身在揭陽傳教的經歷,探討本土教會的培育及其存在的問題,或有關差會在華的歷史。斐姑娘是晚清在潮州的女傳教士中唯一一位出版多本著作的女士。⑤耶士摩的兒媳耶琳夫人(Lida Scott Ashmore)1920年出版關于美北浸信會在潮州 60年的歷史一書。Lida Scott Ashmore,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A Historical Sketch of Its First Cycle of Sixty Years.Shanghai: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1920.其次,《真光初臨》的特別之處在于書中的主角是16位為自己發聲的中國婦女,她們大部分有自己的名字,且《真光初臨》以第一人稱的方式陳述,仿佛16位婦女在讀者面前述說自己的故事,更能引起讀者的興趣,不同于一般傳教士的報告或文章以第三人稱呈現。傳教士當中像斐姑娘這般出版著作數本,甚至《真光初臨》還印刷至第六版的不多。同在潮州的英國長老會曾在《他邦的姊妹》上推廣和宣傳斐姑娘的這本書,⑥Fielde, Our Sisters in Other Lands, V. LXXVII op.cit., 1898, p. iii.因而《真光初臨》很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
三、《真光初臨》中的潮州婦女形象
斐姑娘對中國婦女的地位的判定與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如郭實蠟、盧公明的判斷一致,⑦Jessie G.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Michigan &Cambridge: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p.133.恰如胡衛清所言,具有典型的意義。⑧參見胡衛清:《苦難與信仰》,第103頁。斐姑娘在此書開篇專門用一章來介紹中國婦女的地位。在她看來,中國婦女的地位比印度、土耳其、緬甸、暹羅等國要稍好一點,但仍是十分低下的。斐姑娘的特別之處在于她書中呈現了表1中的16位婦女個體。下面我們通過其筆下的16位女傳道,檢視她如何塑造她所理解和把握的中國婦女。⑨表1所列為斐姑娘在《真光初臨》中提到的16位女傳道的中英文名字及其可能家世。關于女傳道的名字的資料可參照的有五份:(1)在1884年至1886年版本的《真光初臨》中,有四幅女傳道的肖像畫,畫下標出了她們的名字(1887年版本沒有),分別在第163、205、239、251頁;(2)斐姑娘1880年給西部婦女會的年度報告;(3)斐姑娘于1887年給西部婦女會的年度報告;(4)斐姑娘于1886年9月發表在BMM上的文章;(5)斐姑娘發表在《援助之手》上的一封信,其中提到20位女傳道的名字,受浸年齡、現在的年齡及在婦女學校學習的年限。后四份資料有提供女傳道中文名的音譯。女傳道的中文名字由蔡香玉辨證,她依據的是中文1860年嶺東浸信會創始至1910年會友姓名錄。該姓名錄載于1936年的《嶺東嘉音:嶺東浸信會歷史特刊》,共54頁。T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Woman’s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Held in Chicago, April 13 & 14, 1881. Chicago: James Guilbert, 1881,pp. 77—80. Seven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Held in Omaha, Neb., Wednesday & Thursday, April 18 & 19, 1888. Chicago: James Guilbert, 1888,pp. 73—75. Fielde, “The Bible Women,”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LXVI. 9, 1886, p. 375; Adele M. Fielde, “A Letter from the Swatow Bible-women to the Bible-women in Shanghai,” The Helping Hand, VIII. 2, 1879, p. 11;《嶺東嘉音:嶺東浸信會歷史特刊》,汕頭市檔案館藏嶺東基督教檔案,檔案號:C184。蔡香玉:《附錄一:美國浸信會所雇的女傳道》,見《堅忍與守望》,第290—293頁。(見表1)

表1 《真光初臨》中16位女傳道的中英文姓名及其可能家世
16位女傳道中,陳惠蘭28歲,陸快不到30歲,其他大多是中老年婦女,最年長的是杜瑞,64歲。陸快成長在基督教的家庭,“父親是最純正的基督徒和最優秀的布道員”,①Fielde, Pagoda Shadows (1887), p.108.《苦難與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經驗·附錄二》,第331頁。她14歲受浸。女傳道中有五位寡婦,李得金、陳惠蘭和吳攀惜的丈夫出洋掙錢,而林水和黃寶容的丈夫出國杳無音訊,林錦平的丈夫因參與械斗流亡新加坡,九年未歸。這一方面反映了斐姑娘多挑選家庭負擔小的中老年婦女或寡婦來做女傳道,因為性別隔離的傳統使得年輕女子不方便在外拋頭露面,而中老年婦女則可以在鄉間自由行走;另一方面也與潮汕地區的“過番”②潮汕方言中“過番”一詞指到海外,主要是去東南亞國家。相似的說法還有“過南”“過洋”,即乘洋船到南洋群島,而這些海外移居地被潮汕人稱為“番畔”“番邦”“外洋”,在海外的潮汕人則稱家鄉為“唐山”。林朝虹、林倫倫:《全本潮汕方言歌謠評注》,《過番之歌》第四輯,廣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第213—228頁,轉引自蔡香玉:《堅忍與守望》,第39頁。習俗吻合。自明末清初以來,由于人口增加導致耕地不足,又加上19世紀中葉持續不斷的社會動蕩,再加上19世紀50年代開始的外國人主導的苦力貿易,潮汕地區陸續有不少男性或主動或被動到南洋群島謀生,留下妻子在家鄉照顧家庭,并定期拜祭夫家的祖先,③蔡香玉:《堅忍與守望》,第39—44頁。這些女僑眷是女傳教士們積極爭取的對象。
斐姑娘筆下的16位女性大多貧苦而無知。如陳萍的父母很窮,全家靠做紙錢為生;④Fielde, Pagoda Shadows (1887), p. 154.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 352 頁。黃寶容記起生命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家庭的極端貧窮不幸。⑤Ibid., p. 160.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355頁。有的則是因為宗族之間的械斗而導致家道中落,如李得金的夫家、吳銀花家、林錦平家。⑥Ibid., p. 113, pp. 179—180, 138—139.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 334、365、345 頁。林老實的哥哥21歲時在宗族械斗中被射殺。⑦Ibid., p. 143.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347頁。吳真寶家因為宗族械斗打官司而一夜致貧。⑧Ibid., p. 173.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362頁。少數家境富裕,如林水的父親是個漁商,但在她三歲時父親就去世了;⑨Ibid., p. 117.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335頁。吳瑞蘭的父親比較富有,她記憶中唯一一次遭罪是她14歲纏足的那段日子⑩Ibid., p. 135.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343頁。。黃秀蓮的父親是青年紳士,她從小過著被人伺候的生活,婚后非常不習慣干家務和伺候公婆。?Ibid., pp. 169—171.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 359—360 頁。16位女性中,只有陸快是識字的,因為她的父親是一位布道員。林水的家里雖有兩位兄長是讀書人,但沒人教她讀書。據斐姑娘稱,除非女孩是家中獨苗,女孩的父親為高興才讓她識字。?Ibid., p. 118.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336頁。她們大多纏足,只有陸快、李得金和王美是天足。陸快曾希望像其他女孩子一樣纏足,但被她的父親嚇唬說,如果堅持要纏足,那么手也同樣纏裹才行才作罷。?Ibid., p. 111.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333頁。王美是客家女子,不用纏足。據斐姑娘所稱,富家的女孩在七八歲時便開始纏足,而貧家的女孩由于要幫助家里干家務和農活,一般推遲至13或14歲,即出嫁的前一兩年。如林水、吳瑞蘭是14歲纏足,丁鈴是13歲纏足。另一些丈夫或兒子在南洋謀生的女僑眷并沒有裹腳,因為她們需要下地務農。客家的婦女不裹腳,因為她們要在戶外工作。?Fielde, Pagoda shadows, pp. 39—47.
16位婦女傳道在信仰基督教以先,多是拜多神的。如杜瑞每月一至三次攜家人登山祭拜天地,有時也拜月亮、太陽和雷神,她每年要花10先令到2英鎊來買祭品。?Fielde, Pagoda shadows (1887), pp. 105—106.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 330 頁。李得金提到每年拜神的次數達40次之多。?Ibid., p. 114.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334頁。黃秀蓮婚后為了生育成為虔誠的佛教徒,房間內至少有20個每天參拜的神,常年有蠟燭燃點。①Ibid., p. 172.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361頁。而生在制作紙錢之家的陳萍,曾決定成為一個禁欲主義者,為此她堅持了10年佛教徒的生活,不吃肉,不戴耳環,亦不抹頭油,也沒穿過紅色的鞋。②Ibid., pp. 156—157.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353頁。有的婦女甚至曾經是神婆。黃寶容15歲時,她的母親被魔鬼附身而成了神婆。③Ibid., pp. 161—162.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355頁。婦女信仰基督教后,紛紛放棄之前的多神崇拜,但在她們的自述中可看到在其早期的信仰抉擇上,靈驗與否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與胡衛清的看法一致。如林水30年前曾接觸福音,但因不愿意放棄舊的偶像而沒有入教,后因丈夫在暹羅的生意失敗,她虔誠地四處求神問卦,沒有任何效果之后,她對那些神失望而轉投基督教。④Ibid., pp. 120—122.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 335—338 頁。而吳真寶的信道自述顯示出她由多神信仰轉變為一神信仰的反復搖擺而最終堅定不移的過程。⑤Ibid., pp. 173—177.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 362—364 頁。
絕大多數女孩都很早訂婚出嫁,有的甚至被賣作奴婢。杜瑞七歲時就被父母以兩鎊的價錢許配給南隴村的一個男人。陳惠蘭出生后兩個月就和婆婆住在一起了,因為算命先生說如果她不離開家,比她大兩歲的哥哥就會死去。⑥Ibid., p. 124.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338—339頁。林水、林錦平、吳銀花14歲出嫁。一般家庭女孩在家里只能待到15歲左右,之后她們必須嫁出去。⑦Ibid., p. 143.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347頁。吳攀惜、丁鈴和吳真寶是16歲。王美、林老實和黃秀蓮是17歲。陳萍和黃寶容是18歲。吳瑞蘭比較晚,20歲出嫁。黃寶容10歲時被父母典當給一個富有的寡婦作傭人,管吃管穿,父母得到兩鎊10先令。黃寶容因為想家常常整夜哭泣。幸好,五個月后,家人變賣家里所有的豬把她贖了回去。⑧Ibid., pp. 160—161. 中譯文《附錄二》,第 355 頁。
這些女性的婚姻在斐女士筆下大多是不幸的。她批評中國的婚姻制度,認為當時的中國人不能自由選擇伴侶,沒有浪漫的愛情,這阻止了中國文明的進步,也是機敏的中國人毫無發明和發現的原因之一。⑨Fielde, A Corner of Cathay, op.cit., p. 34.斐姑娘書中的女性都是通過媒婆來訂婚姻的,除那些從小做童養媳外,婚前都沒有見過未來的丈夫。李得金的丈夫在族內械斗中受傷,因聽信神媒的話,認為出國才能治好他的傷,僅帶了四先令就離家,從此杳無音信。⑩Fielde, Pagoda Shadows (1887), op.cit., pp. 114—115.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 334—345 頁。林水的丈夫在她34歲時,帶了一批貨物去暹羅,在那里他吸食鴉片,很快花光錢財,再也沒有回家。?Ibid., p. 121.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337頁。王美的丈夫去世了,留下她和兩個兒子相依為命。林錦平不喜歡第一任丈夫,曾想過自殺。?Ibid., p. 139. 中譯文參胡衛清:《附錄二》,第345—346頁。林老實的第一任丈夫在械斗中喪生,七個月后她生下遺腹子。幾年后,婆婆想要更多的子嗣,在沒有知會她的情況下,認了一個兒子來做她的丈夫。這個人品行很壞,賭錢輸光了錢,又以做生意為由借了更多的錢,然后跑掉了。同年,她的第二個兒子出生。后來,婆婆又做主把她嫁給了一個農民,雖夫妻恩愛,可貧病交加。最后為了養家,他們忍痛賣掉三歲的小兒子,丈夫一個月后卻去世了。?Ibid., pp. 143—146. 中譯文參胡衛清:《附錄二》,第 348—349 頁。吳銀花的婚姻波折多舛:她的第一任丈夫一見她就不喜歡她,婆婆對她也不好。丈夫甚至不讓她睡在床上,而且他恨她恨到睡覺都放一把刀在床邊,說是準備在晚上想要殺她的時候用。第二任丈夫是個賭徒,丈夫用贏的錢娶了她,很快他輸光了所有的錢,然后就開始打她。她被第二任丈夫賣給了第三任丈夫,雖然第三任丈夫勤勞節儉,但她們的孩子實在太多而不能養活,不得已賣掉第四個兒子。?Ibid., pp. 179—184. 中譯文參胡衛清:《附錄二》,第 365—367 頁。少數女子和丈夫的關系較為和睦,如吳攀惜和林錦平。但林錦平的第二任丈夫因在械斗中曾供應火藥,并參與射擊,為逃避懲罰,他逃往新加坡,已經九年未歸。①Ibid., p.141. 中譯文參胡衛清:《附錄二》,第346頁。婚后婦女們多數會溺殺女嬰,因為養女孩普遍被認為是一件不劃算的事情。杜瑞、吳瑞蘭、林老實、吳真寶、黃寶容的母親、吳銀花都坦誠自己曾經親手殺死自己的女兒,當時她們并不覺得這很罪惡。婚后婦女會有生男孩的壓力,但在家中生計實在無法維持的時候,賣兒子會在賣田地之前。如吳銀花將兩歲的兒子賣給了一位富人,換得一幢價值20英鎊的房子。②Ibid., pp.183—184. 中譯文參胡衛清:《附錄二》,第367頁。
《真光初臨》中所鋪陳的觀點是:在種種不幸婚姻和沉重的現實之下,基督教的福音才是中國婦女的唯一出路。由于當地的性別隔離傳統,婦女接觸基督教的機會比男性少很多,這是早期女性基督徒遠遠少于男性的原因之一。對女傳道的需求正是由于其可以協助女傳教士在廣大的鄉間傳揚福音,加快其工作的效率,而且花費要比聘請更多的女傳教士少得多。根據女傳道們的生平自述,多數女傳道是受到家族中男性或直接或間接的幫助和影響而入教。陸快的父親是一位傳道員自不用說;杜瑞和王美是受到侄子的幫助;林水最初從弟弟那里聽到福音;吳攀惜聞道雖然是因為姑姑吳銀花,但仍然得益于丈夫去教堂聽道,堅定她的信心。③Ibid., pp.129—130. 中譯文參胡衛清:《附錄二》,第 340—342 頁。然而,正如蔡香玉所說,男權是把雙刃劍,既能影響女性信教,也能阻礙女性信教。④蔡香玉:《堅忍與守望》,第139頁。例如,吳銀花的妹妹只有在丈夫不在家時,才敢去做禮拜,因其丈夫揚言,如果他的妻子去禮拜,他就會打死她。⑤Fielde, op.cit. (1887), p.189.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 370 頁。女性信教之后,還能影響身邊的男性親屬,如丈夫、兒子等入教,如陳雪花將兒子黃寶山送到汕頭去見傳教士;李得金的兒子受她的影響也信仰基督教。恰如李榭熙所言,年長的女信徒甚至能夠像家長一樣影響小孩子信教。⑥Joseph Tse-Her Lee, The Bible and the Gun: Christianity in South China, 1860—1900.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81.
然而,婦女在入教之后,也會遇到許多阻撓和困難,甚至對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如與祖先崇拜有關:林老實出國多年的大伯托表兄送給她五英鎊,因為大伯聽說只有林老實與其子祭祖,所以寄錢回來。當這位表兄發現她已成為基督徒時,他起初不愿意把錢給她,最后在鄰里的幫助作證下,表兄才把這筆錢交給了她。但他寫信告訴大伯,她已經是基督徒的事實,大伯從此就再沒有寄錢給她。⑦Fielde, op.cit. (1887), pp.147—148.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 349—350 頁。又如丁鈴在信教后,便再也不拜神,不燒香,不去廟里,只崇拜上帝。受洗之后,夫家的親戚因為丈夫不拜祖先而收回他所有的祖產,以致他們生活非常窮困。后來,當日子實在無以為繼,他們只好將三歲的女兒從光賣給城里的一位官太太當婢女,哪知從光被官太太極盡虐待,過著悲慘的生活。一年五個月之后,他們知道了女兒的苦況,向教會求助才得以將女兒贖回。但很長時間里,他們因為曾經將自己的親生女兒賣掉而為教會所不信任和不齒。⑧Ibid., pp.149—152.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 351頁。
入教或者做女傳道并沒有給女性信徒的物質生活帶來實質性改變,這是斐姑娘培訓女傳道的基本底線,即不希望婦女來擔任女傳道是因為“吃教”或女傳道這份工作的收入。女傳道每月有八先令(當時約兩美金)作生活費和旅費,但這些錢只能夠維持她們在家時的生活水平,不會讓她們更富裕。⑨據斐姑娘所稱,當時沒有手藝的勞動力每天工錢是10美分,手藝人每天20美分,每月工資分別為三美金和六美金。那么女傳道的工資屬一般水平。Fielde, A Corner of Cathay, op.cit., p. 22.她們的穿著和普通貧窮婦女并無二致,但她們行走在各個鄉間傳道站時,要忍受風雨,飽受饑寒和困乏之苦,這不是中國其他婦女所能理解的。盡管如此,據斐姑娘稱,沒有女傳道因為這個工作的困難而放棄它。⑩Fielde, Pagoda Shadows, op.cit., p. 149.1886年,同在汕頭的娜姑娘在給浸信會西部婦女分會的年度報告中指出,女傳道丁鈴多次因犯錯帶來危害而不改正,被暫時開除。①Fif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Woman’s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West. Chicago: James Guilbert, 1886, p. 70;The Helping Hand XV. 7, 1886, p. 53.雖然物質生活并未有改變,斐姑娘筆下的女信徒們似乎很享受福音帶給她們精神上的滿足和支持。如林水說:“我心只向往天國,我有很深的苦痛,但沒有這些苦痛,也許我不會得救,我很強健,也許我還能活許多年。如果能使眾人信主,我將非常幸福。”②Fielde, op.cit. (1887), p.123.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 338 頁。陳惠蘭這樣說:“從童年起,我就一直過著悲慘的生活,我從來沒有過過無憂無慮的日子。不過在過去一年里,盡管我的環境沒什么改變,我卻基本上是幸福的。我知道有救世主和天國,它們替我卸下了苦惱的重軛。”③Ibid., p.127.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340頁。陳萍如此說:“感謝主使我如此幸福。年輕時我的心中毫無希望,思想愚昧,但是現在我老了,神的光照耀著我,我的路是光明的。”④Ibid., p.159.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355頁。吳銀花則說:“直到三年前你(筆者按:斐姑娘)叫我到這里來學習識字,我的身體才好起來。我學習了四個月,這對于外出做婦女傳道已經足夠了。我差不多到100個村子傳過道。我今年51歲,神很眷顧我,如果我身體健康,能為主做工一直到死,我將非常滿足。”⑤Ibid., p.190. 中譯文參《附錄二》,第371頁。
綜上,斐姑娘筆下著重刻畫的16位女傳道多為寡居或丈夫出洋的中老年婦女,她們大多家境貧困,或因械斗而家道中落,不識字,拜多神,大都很小被纏足,婚姻多數不幸。在“三從四德”的儒家性別模式約束下,其中兩位婦女甚至先后嫁三任丈夫,另一位婦女因想自殺被婆婆嫁了出去。在斐姑娘的筆下,這些婦女極度痛苦而亟須救贖,基督教的福音雖然不能改變她們的現實生活狀況,但通過學習圣經知識,擔任女傳道,她們內心愉悅而滿足,女傳教士們的榜樣更給她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但從多神信仰轉向一神信仰的女傳道們很難一下子就成為純正的基督徒,她們難免會犯錯,比如丁鈴因生活所迫賣掉女兒從光。這16位女傳道的形象即是斐姑娘眼中的晚清潮汕婦女,是她刻畫的晚清中國婦女形象的縮影。
四、反思婦女形象
恰如阿布魯霍(Lila Abu-Lughod)的書《穆斯林婦女需要拯救嗎?》⑥Lila Abu-Lughod, Do Muslim Women Need Sav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標題的發問,筆者同樣想問:晚清的中國婦女確如斐姑娘之筆所描繪的需要拯救嗎?在拯救的邏輯中,拯救一個人意味著將她從某種情境中拯救出來。⑦Ibid., p. 47.同時拯救背后暗含施救一方凌駕于被拯救者之上,是對被救者的某種否定。斐姑娘在傳教過程中近距離地觀察潮汕婦女所遭遇的各種困境和問題。作為獨立的傳教士,作為與當地婦女截然不同的他者(the other),《真光初臨》呈現的是斐姑娘視角下的中國婦女的“苦難的模式”。⑧此處借用胡衛清之語。其文字明里暗里將中國的一切與西方相對照,以西方作為標準來評價她所看到的中國,是東方主義式的書寫,流露出她背后的西方文化、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優越和傲慢。如她評價當時大部分中國人住在“不通風,沒有屋頂,沒有地板”的房子里,“冬冷夏熱”“常年臭氣熏天”。⑨Fielde, Pagoda Shadows (1887), op.cit., p. 45.斐姑娘認為房子的不舒適不僅僅因為貧窮所致,更因為纏足限制了婦女本可以打掃房間的活動,再加上使用白色的禁忌和風水習俗的束縛。她指出只有等到基督教的真理滲透中國社會的基礎,中國人才能居住得舒適。⑩Ibid., p. 46.由此可看出她認為福音既來,文明將隨之而至。又如她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評價,她認為這些作品沒有在西方知識的基礎上有任何重要的增加,甚至指出數百年來,中國人“毫無發現,毫無發明,更別遑論進步”。①Ibid., p. 198.斐姑娘此言不可謂不傲慢和過于自信。對國人宗教信仰的抨擊則貫穿全書,祖先崇拜、風水、占星術、神婆、灶神等都分小節論及,在她看來都是異端、迷信,會帶來各種罪惡和不可挽回的后果。這種種文化上的優越感和對東方宗教的輕視正是始自19世紀初傳教運動的大環境所賦予斐的。因而,斐筆下的中國婦女是在特定條件下書寫出來的:在傳教運動的大背景下,在不對等的中西互動下,在異端(heathenism)與文明 (civilization)的對立之下。在諸多條件限定下書寫的中國婦女形象是斐姑娘向西方描述東方的結果。
《真光初臨》中的16位女傳道有著幾乎同樣的“苦難的模式”,書中其他地方提及的女性大部分也是不幸和痛苦的,如揭陽27歲的寡婦,因為叔伯爭奪她的家產和她10歲的兒子,她被繩捆綁以20鎊的價錢嫁給鄰村剛死了太太的老翁;②Ibid., pp. 5—6.很早訂婚,到婚嫁之年發現對方患有不治之癥,且樣貌恐怖,19歲的女孩試圖解除婚約失敗,出嫁后很快去世了。③Ibid., pp. 6—7.《真光初臨》中絕大部分是下層社會的貧窮婦女(盡管吳瑞蘭和黃秀蓮出生并成長在富有之家,但她們聞道信教時,吳瑞蘭的丈夫是個漁民,黃秀蓮的夫家是非常節儉的鄉紳,她們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上層社會的婦女),并未論及上層社會的富裕女信徒如何,這顯示其傳教過程中接觸婦女的層面較為單一或狹窄,或者說晚清時期女傳教士和女傳道很難接觸到上層社會的婦女。④沃倫李(Leonard Warren)亦指出斐姑娘的文字罕有提及受教育的中產階級婦女,她們事實上仍在傳教士的接觸范圍之外。Leonard Warren, Adele Marion Fielde: Feminist, Social Activist, Scienti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57.但筆者發現斐姑娘另有一篇女傳道的自傳并未被收入《真光初臨》中,該女傳道名為繡金(Siu Kein),她出生在富裕有權的家庭。⑤Adele M. Fielde, “The Autobiography of Siu Kein,”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LIX. 3, 1879, pp. 60—61. 凌愛基在其文中有提及。Ling, “Bible Women,” p. 246.而同在潮州的英國長老會的李潔姑娘1897年后從汕頭遷到潮州府,開始在上層社會婦女中擔任福音工作,因一位社會地位較高的女信徒(Tan-Sim)的牽線,她得到許多機會可以去府城富裕人家布道。⑥Catherine M. Ricketts, “Swatow: Report, 1895, to October 31st, 1896,” Our Sisters in Other Lands, V. LXXIV, 1897, p. 164.這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女傳教士逐漸得以接觸來自更多元階層的婦女。由此可見,斐姑娘提供的一幅普遍化的“苦難的模式”的中國婦女圖像是刻意為之,只能說是斐姑娘想呈現的中國婦女形象。
回到斐姑娘《真光初臨》的創作問題。收在該書中的文章,其讀者大概是母國差會總部、支持母會的各教會、浸信會東西部婦女會和支持斐姑娘中國傳道工作的美國婦女信徒們等。她的文字因要證明她的婦女工作十分必要且緊迫,所以需要強調中國婦女信耶穌之前如何痛苦、不幸,強調其深陷其中的各種苦難,并凸顯她們信主之后的愉悅和得救。雖然斐在《真光初臨》的前言中強調書中的自傳完全是從汕頭話的自述中翻譯而來,但正如傳教士用中文翻譯西方的基督教作品,常常對原著進行了大量改寫或改編,使得翻譯與創作的關系和界限有時顯得模糊不清,⑦黎子鵬編注:《晚清基督教敘事文學選粹》,第xxxiii—xxxiv頁。斐姑娘的翻譯難保沒有創作的成分。今天我們已經無從得知斐姑娘書中所記的16位女傳道的口述證道的真實程度,但我們可以結合其在潮汕傳教生涯,分析其寫作動機和意圖。斐姑娘是個擅長用文字表達自己、很有主見和決斷的女傳教士。1873至1889年在潮汕傳教期間,她寫了大量有關潮汕風俗、當地女性、女傳道等主題的文章,并發表在《浸信會傳教雜志》《援助之手》(The Helping Hand)等雜志上,或制成小冊子分發給女性讀者。美北浸信會委員會國外通訊秘書默多克1878年2月15日致信告知斐,她在《浸信會傳教雜志》上的文章反響不錯,鼓勵她多寫有關中國人的習慣、思維模式、習俗、家庭、社會以及宗教,他們如何接受基督教,如何背離舊習慣的文章。簡而言之,“去刻畫人們異教的狀態和再生的狀態”。⑧Overseas Letters: J. N. Murdock to Adele M. Fielde, February 15, 1878.斐姑娘的文章大體秉持這一原則。因這些文章比之前有關中國的文獻有更多細節,觀察更細致,再加上文筆優美,使斐姑娘獲得廣泛關注,從而為她贏得了大量針對中國女性傳教的定向捐款,這使得斐姑娘的傳教可支配金額遠遠多于主導傳教的男傳教士,甚至她在潮州服務的最后四年,總部不再為其傳教工作撥款,認為她手頭有足夠的款項可供支配。①Overseas Letters, E. F. Merriam to Adele M. Fielde, August 2, 1886.
尋求經費支持是斐姑娘寫作《真光初臨》的初衷之一,當然還有更深層次的意圖和意義。斐姑娘出身并不富裕,她的父親是個木匠和粉刷匠,屬美國社會的下層階層。斐姑娘的教師文憑是其教書三年后再去攻讀師范學院所得。當她成為女傳教士,雖然在差會的架構下,女傳教士在權利、薪資、住房等方面與男傳教士相比,都有不平等之處,但因斐姑娘著重婦女工作,在具體的工作中可發揮的空間較大,自由度較高。在華南教區的負責人耶士摩(William Ashmore)短時離開,或因眼疾被困房間長達六個月時,華南教區的各項傳教工作由斐姑娘負責暫為主持,可見她在潮州的傳教地位不可謂不高。她通過塑造苦難、亟待救贖的女傳道的形象,書寫她們因信奉耶穌而改變生命意義的故事,首先將自身建構成堅持、奉獻、有知識、有能力的創造者;其次通過與她筆下描繪的負面的中國婦女區分,樹立自己正面、積極的形象;最后強調中國婦女獲得了西方婦女正面、積極的形象,是她傳道努力的結果,顯示她作為榜樣的力量。受杜娟華研究總結所啟發,筆者發現斐姑娘在書寫和塑造亟待救贖的中國婦女的同時,也塑造了她在東方成功傳教的女傳教士的形象,進而進一步合理化、合法化自己的傳教教師職業和地位。1887年版《真光初臨》在最后增加了《中國婦女工作的范圍》一章,指出女傳教士和女傳道也可影響中國的男性信教,而差會應該有同等人數的男女傳教士,既合作又各自獨立,呼吁更多的女傳教士加入婦女工作。②Fielde, Pagoda Shadows (1887), op.cit., pp. 203—208.可見斐姑娘的書亦間接地為差會宣傳在華的傳教工作。
結語
19世紀中國教會歷史中的婦女信徒幾乎沒有聲音,斐姑娘的《真光初臨》一書留下了極為珍貴的16位中國女傳道“自己的”聲音。作為一部晚清基督教文本,其作者的女性身份和書中獨特的第一人稱的陳述方式,使其成為一部獨特的作品。傳記內容或文字本身很可能受執筆者和讀者群的影響,斐姑娘在《真光初臨》中翻譯的16位女傳道的生平自述雖可能存在創作的成分,卻未必不是真實的,她們或許的確是痛苦而亟待救贖的群體,但斐姑娘可能出于其復雜的傳教目的選取了這“苦難”的16位婦女,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強調了她們的苦難和需求,同時略而不提其他類型婦女的存在,以凸顯中國婦女的“亟待救贖”形象,這是作者的傳教士身份及當時的意識形態和世界觀的影響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