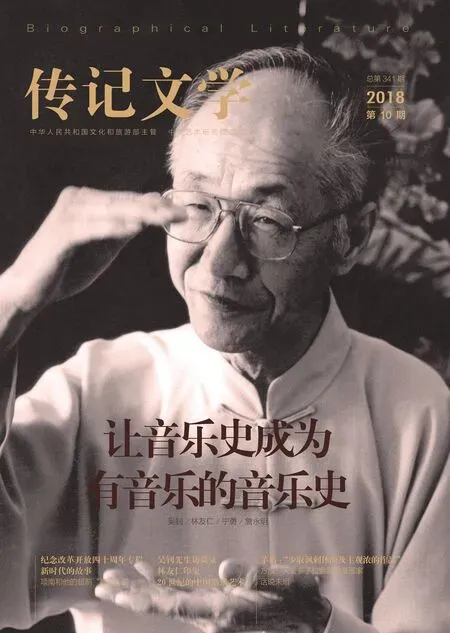心中有只不死鳥
——懷念恩師王富仁先生
何希凡
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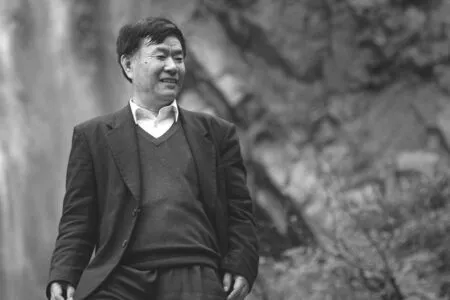
大約三十年前,曾在一個小報上讀到一篇中學生寫的短文,題目是《壯哉,不死鳥》,內容雖然早已記憶模糊,但“不死鳥”這個意象卻長久地吊住了我的胃口。我明知它不過是個比喻,但每當想起它,總是要追尋這世間究竟有沒有不死鳥。從古至今,多少癡心妄想者都在苦求著長生不老之藥,秦始皇、漢武帝等威加海內之輩都曾有過“服黃金,吞白玉”之舉,但到頭來不免是“劉徹茂陵多滯骨,嬴政梓棺費鮑魚”。看來,世間真的難以有不老不死之人了。如果真有不死鳥,那也算得上生命的奇跡,但后來知道那也不過是神話傳說而已。郭沫若長詩《鳳凰涅槃》篇首的小序就說:“天方國古有神鳥名‘菲尼克斯’(Phoenix),滿五百歲后,集香木自焚,復從死灰中更生,鮮美異常,不再死。”這其實就是中國人所謂的鳳凰,亦即“不死鳥”,在《孔演圖》和《廣雅》等文獻中都有記載。由此可知,鳳凰之能不死,必先經過死而“更生”。我想,鳥尚能如此,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怎么就不能創造同樣的生命奇跡呢?沒想到,在我平淡無奇的人生中竟有緣際遇了真正的“不死鳥”。
“不死鳥”之死
2017年5月2日傍晚,文學院領導傅學敏教授打來電話說,半年前曾擬定請王富仁老師來我校講學,現在可以請他老人家過來了。我拿著電話犯了躊躇,因為幾周前我曾給王老師打過電話,接電話的是他家的保姆,她告訴我說,王老師又去了北京。我知道,自從王老師被確診為肺癌后,就一直往返于北京與汕頭,只要北京的放化療結束,他就要回汕頭去給學生上課。雖然他一直對自己的身體很自信,曾對我說,除了醫生告知他患了癌癥,自己并沒有任何異樣的感覺。我也曾在心里期盼著奇跡的發生,但多次的放化療,這一次去到北京究竟是什么結果,誰也難以判定。我只得對傅學敏老師說,等我與王老師聯系上了再說。誰知我剛掛了電話,伏俊璉老師就發來信息:“著名現代文學專家、魯迅研究專家王富仁先生于今日19點20分在北京逝世。”噩耗來得如此突然又如此巧合,就在文學院師生幾個月的熱切期待即將實現之際,它卻瞬間變成了泡影!淚水潮濕了我的眼眶而沒有充溢,因為我不相信富仁師這么快就走了。
窗外突然間雨暴風狂,室內也有了陣陣寒意,我忽然想用王老師生前并不感興趣的俗套禮節為他撰寫一副挽聯,但我卻想寫出最不落俗套又最能契合他的生命本質的內容。只要讀他晚年的文章,那無比健碩而大氣的文筆,那強大的思維運動力量,你怎么能夠想象這是一個身罹絕癥的老人生命終結前夕的絕筆?只要深味他波瀾壯闊的學術生涯,你看他的身上可曾有“著書都為稻粱謀”的歷史回光返照?他雖然曾擔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但他何曾表現出絲毫的學霸氣與領袖欲?他是憑著自己著述煌煌的最誠實的學術勞作高擎起中國現代文學的獵獵大旗,他的思想鋒芒和學術個性不是為了逞一己之能,更不是為了獵取一己之名利,而是滿含著對國家和民族的深愛,滿含著對自己所獻身的學科命運的深切系念,滿含著對后學的萬縷仁愛!但他這一走,一個時代的稀有之音漸行漸遠,他所發出的振聾發聵的吶喊正如魏晉時代的嵇康臨終前之廣陵散絕!我沒有想到,撰寫一幅挽聯竟然伴著整個風雨長夜,當陜西師大的著名學者、書法家,也是王老師弟子的李繼凱仁兄見到我撰寫的這幅挽聯,當天就不吝他漂亮的筆墨書寫出來:
椽筆猶健碩,先生豈求一己富,長恨蒼天摧人哲;
大纛失飄揚,后學俱感萬縷仁,但悲學界絕廣陵。
“不死鳥”與我
當我來到大學教書之前,要把王富仁的名字和我聯系在一起,那簡直就是“吾不識青天高黃地厚”。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就略知王富仁,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位中國現代文學專業博士。他的博士論文改變了過去幾十年間魯迅研究的強大慣性,是學術界思想解放的標志,也是魯迅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成果。他名滿天下,也招來了慣性的嚴重質疑。我在給師范生講魯迅的時候,也偶爾謹慎地搬用了他的一些見解,但我從來沒有奢望有朝一日會直接面對他,還能聽他的課。1993年7月,我來到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當時的四川師范學院中文系),被安排任教中國現代文學課程,與此同時,學校同意我先到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進修。記得是年9月14號到了北京,我的導師是新文學史料學研究的名家朱金順先生,他向我介紹了即將開課的六位教授,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王富仁、童慶炳、郭志剛等先生。王富仁的名字已不陌生,因他是本專業首位博士,而且當時還算學術新銳,他的著述已凸顯出鮮明的個性鋒芒,字里行間流淌著學術主體的生命自信,我料想他一定是一個有些脾氣乃至有點傲慢的人,而像我這樣一個早已過了而立之年卻尚未學術起步的渺小靈魂,怎敢去擅擾一個大學者宏圖杰構、吞霞吐錦的滔滔思緒?我想早一點見到他,但他的課安排在1994年春天,我就把讀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和《先驅者的形象》等著作當作與他的提前會面。偶爾也能從老師和同學口中聽到他的故事,聽到他獨到深刻的見解,他的面影已經在我心中漸漸鮮活起來,但整整一個學期,盡管數度經過他所住的麗澤8樓下,還是不免有叩門無路之虞。

王富仁著《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
春節假期剛過,我就趕回了北師大,校園雖然還凜冽著寒意,殘霜還橫陳在道路左右,但圖書館前的草坪已經微吐綠意,迎春花也稀疏地開了,北京干燥的氣候與還算淡藍的天空已把暖意送到心頭。記得正月初九開學,在領略了朱金順、劉勇、李岫等老師的精彩講授之后,終于迎來了盼望已久的王富仁、郭志剛、童慶炳三位先生登臺,他們都是中國學界的頂尖級學者:郭志剛先生是老一代現代文學研究名家,尤以孫犁研究蜚聲學界,而且因為對孫犁的幾十年私淑,其高華雅潔的文筆似與孫犁同構,也因為他對我的多年錯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的學術文筆。童慶炳先生是中國文藝學的泰斗,不僅在文藝理論上著述等身,聲名卓著,而且還涉足文學創作,出版過兩部影響較大的長篇小說,培養過莫言、余華、畢淑敏等著名作家,被譽為“中國文學的教父”。童老師2005年來我校講學,十余年后我們師生重逢,童老師竟與我動情擁抱,當著我的眾多學生說我是他的老學生。王富仁老師給我們開了《魯迅小說研究》,這是他譽滿天下的專攻。他的精彩不是人們常見的精彩,從來沒有講稿,但口中飛珠濺玉,深刻的思想、獨到的見解、嚴密的邏輯常令我們猝不及防,他不斷顛覆著我們的慣性思維,撥開現象的花絮,撩開似是而非的面紗,讓我們看到了從未看到過的人性真相、文化真相和歷史真相。聽他的課你會感到新鮮而陌生的刺激,你也會感到自我的渺小。但即使如此,我對他積久存有的敬畏惶恐之心卻漸漸煙消云散了,你看他那一身老農民的打扮,你看他那剛過知天命之年卻已布滿溝壑的臉龐,你看他那一頭染過的黑發卻無論如何也掩蓋不住的調皮銀絲。雖然也穿著藍色的西裝,因為它并不筆挺而略顯褶皺,你仍然可以毫不費力地在頭腦中置換出他曾經被稱為“公社干部”的那一身老式中山裝。他接連不斷地抽煙更增添了人間煙火氣的質感與厚度,我們實在是在被他熏陶啊。神秘感一旦消失,他在我的心中漸變為親人和朋友,有些問題想和他討論也就再沒有了先前的心理障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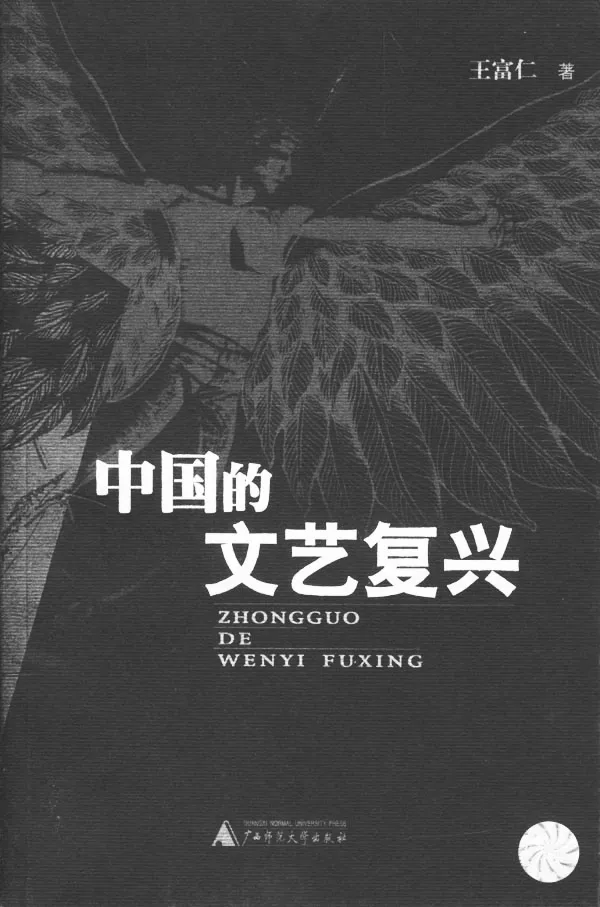
王富仁著《中國的文藝復興》
因為上一個學期我曾就茅盾1940年代的未竟長篇小說《霜葉紅似二月花》寫了一篇論文,得到過李岫老師的熱情鼓勵。在此之前我也讀到過富仁師的關于魯迅和茅盾小說比較的長篇論文,其中關于《霜葉》的一些觀點我深以為然。于是趁一次課間休息,我并沒有過多體諒他講課的辛勞而不失時機地湊上前去向他表達了自己的一點淺薄看法。我說,學術界都認為這部小說最大的遺憾是沒有按照作者的最初構想寫完,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半成品,而我卻認為這部小說好就好在沒有寫完,如果寫完了就一定不如現在的更好。沒想到富仁師對我大加贊賞,當即鼓勵我盡快成文。我自然大喜過望,連續熬了很多長夜反復修改,也請一同進修的同學幫我把關,然后我和富仁師約定在他家里交談。還記得先后有三個下午就在他家的飯廳,我和他在飯桌對面而坐,他還是那么隨和慈祥,但我能感受到他讀了我的文章已經沒有初次談話的激動。他首先問我究竟想表達一個什么意思,然后指出我的兩處引文說,你引用的這些話有什么高明之處?能幫助你有哪些獨特的思考?這些話你自己都應該說得出來,何必要引用呢?引用是為了推動你的思考和論述,讓你做出超越別人的表達,否則,為引用而引用有什么意思呢?你對小說原作做了那么多繁瑣的分析,自認為很精彩,你究竟是在寫講課教案還是在寫有自己獨到見解的論文呢?分析作品應該是為你的新鮮見解服務,與此無關的分析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連珠炮似的問題把我打蒙了,我表示還要繼續思考,繼續修改。然而,富仁師為我這篇匱乏學術品格的文章前后所花的三個下午時間并沒有打上句號,越到后來,我越是感到了富仁師那一連串問題所蘊含的價值,因為我知道了學術研究不僅僅是對研究對象有了濃厚的興趣,也不僅僅是對文學文本的爛熟于心,而是要有對于研究對象與眾不同的認識,而這種認識也要盡可能對已有的同類研究成果有超越性的進展,否則,我們就根本沒有在學術研究上取得發言權。我也深知,作品研究不是繁瑣濫俗的賞析,研究作品的過程也就是表達思想、揭示學術主體自我發現的過程。別人的見解再精彩,如果被我們去重復證明,那就是無效、無意義的勞動。后來,讀到富仁師更多的論述,我進一步知道了學術研究不能只靠靈感的閃現,僅僅讀了很多書或者很有學問,僅僅有了足可驕人的才華,這些都不等于學術本身,才華和學問要靠學術主體的生命和思想去照亮。但我們的文化傳統是一個特別重視才華與學問的傳統,正因為如此,當人們拿著這個標準去比較周氏兄弟的時候,總是想用周作人的才華和學問把魯迅比下去,而魯迅卓越的思想常常被人們忽略不計。富仁師并不輕視一個人的學問和才華,但他是希望我們這些想要吃“學術飯”的人更要有自己獨立的思想。有了這些感悟,我沒有放棄當年那篇文章,經多次修改,幾至十年辛苦,終于在2002年發表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富仁師當年嚴肅追問的意義也絕不僅止于砥礪我寫成了這篇文章,其更重要的意義則在于讓我懂得了學術研究的基本道理,這些并不高深卻為很多吃學術飯的人一再忽略的道理伴隨著我的學術生涯,我渺小的學術生命就靠這些道理而有了方向,與此同時,我也把這些足以終生受用的珍貴啟示滲透給我的學生。
“不死鳥”之不死
我是富仁師的學生,這是真實的,但作為他的學生我又是不夠格的。他早年的碩士生和后來的許多博士生都是中國學界的風云人物,如果我膽敢在他們面前自詡是富仁師的學生,他們一定會做出權威性的澄清,在王門弟子中誰也沒有聽到過我的名字,而一個僅僅聽過富仁師一學期課的進修生定會令他們嗤之以鼻。然而,他們何曾想到,一個渺小的靈魂與一個偉大靈魂之間就這樣不可思議地有了長達二十余年的精神牽連。我可以坦然地說,我與富仁師是純潔的君子之交。他有幾位博士生與我略有交往。劉殿祥就是當年我們在北師大進修的同學,當他知道我與富仁師的深交,不無歆羨地說,你比我們更幸運!這種幸運不只在于富仁師每出新書不但一定要寄贈給我,還會寄贈給我的學生,更令我感動的是,有一次他要我幫他把有關他的“新國學”觀討論的文章搜集出來,編輯成書,并與我商討了書名,他要私人出錢幫我出版,還口口聲聲說:“我完全可以幫你,我有這個經濟能力。”雖然后來種種原因,這部60余萬字的書最終流產,但富仁師的一番拳拳愛意永遠銘刻在我的心間!二十幾年來,我用心讀了他的每一篇文章,雖然多是長文,但沒有一篇不彰顯著他的原創和獨創,而且行文之間絕少學究氣、學霸氣,每句話都似汩汩清泉自心底流出,是那樣的明白曉暢,又是那樣的震撼人心,幾乎人人都能讀懂,卻很少有人能說得如此到位。我曾經多次對我的學生說,富仁師的文章都是“高水平的大白話”。我還發現,富仁師越到后來越是很少去研究令人眼前一亮的新話題,但老題目一到他的筆下你就不能如風過耳,你雖然聽到很多名人討論過這些話題,但王富仁一旦發言了你就得用心看看。比如,關于最受爭議的魯迅的《青年必讀書》問題,關于中國現代新詩的諸多問題,關于一再被人翻云覆雨的魯迅與顧頡剛關系問題,關于胡適與學衡派的歷史定位問題,等等,這些都經很多學人一再言說,但當富仁師重新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總會有令人嘆為觀止的深宏之論。

課堂上的王富仁先生
自然,富仁師不是完人,他也有自己的生命局限,也有自己的知識盲點,他的論著甚至也有些許的知識硬傷,同行中也有對他的這些并不完美私下非議者。我就曾聽到過一個年輕教授居高臨下、聲色俱厲地批評他的不是,甚至說他這也不懂,那也不懂,但當這些人面對他整體性強大的學術生命,面對他那些力能扛鼎的論著時,都不得不投以折服的目光。
就我個人而言,最幸運的是每次和他通電話都在不經意間作了沒有預謀的長談,一旦觸及到感興趣的話題,聽富仁師滔滔不絕的驚人之論實在是難得的精神洗禮,有時直到說得我的電話沒電了方才罷休。北師大的一學期聽課竟然延續到二十幾年的教益。
他初到汕頭大學又新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繁忙可想而知,但他卻在身患背瘡打著吊針的疼痛之中堅持為我的書寫了長達五千余字的序言,并發表在《魯迅研究月刊》。作為學術界作序最多的著名學者,他的拳拳之愛豈止于我,簡直可以說灑向學界都是愛!
如此生命健旺而具有凌云健筆的人怎么會死呢?但他卻實實在在地走向了生命的盡頭,只是他站在生死之門上比誰都顯得更加從容淡定。當我知道醫生已經確診他患了肺癌后心情很是沉痛,他反而還來勸我:“活得再長也不過是這世界的匆匆過客,歲數是給別人看的,一個人的生命價值不在于它的長度,而在于生命的質量。我王富仁活了76歲也不算短壽了,我此生只要對得起自己的事業,沒有做有損于民族的事,我就已經心滿意足了。”當我勸他不要在病中寫作,這樣會更加使病情惡化,他卻自有一番道理:“你不知道,寫文章使我分散了對病的注意力,相反有助于病情的穩定。”他的這些話不是強詞奪理,而是真正懂得生命意義的肺腑之言。聽了他的這一番話,我這個向來怕死的人也有了向死而生的生命啟悟。于是,我想起了他很喜歡的黃仲則的兩句詩:“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一個快要走到生命盡頭的老人活得如此清醒,如此不失生命的尊嚴,他那凜凜風骨撐起的挺拔身姿哪里就會倒下去呢?他怎么會真的死去呢?我相信,幾年之后,幾十年之后,乃至更長的時間,學術界不會停止對王富仁學術高度的瞭望,更不會停止對他的學術著述意義的闡釋,因為中國學術有了他和他的同道的介入,才有了不一樣的學術風貌和精神風景!當一個人的生命之光具有了歷史時空的穿透力,我敢確信他并沒有死,因為在我的心中,他實在是一只鮮活異常的不死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