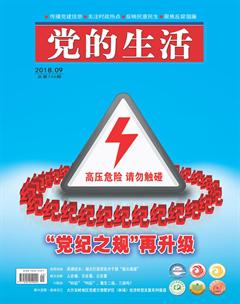一個司法局局長的“勇”與“謀”
牟軍 任紅禧
人物檔案:
劉勇,現任大慶市司法局黨委書記、局長。曾榮立個人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6次,先后獲得“全國優秀青年衛士”“全國優秀人民警察”等榮譽稱號;所在大慶市司法局被評為全國文明單位。
2018年6月21日,全國“堅持發展‘楓橋經驗 實現矛盾不上交”試點工作推進會議在大慶市召開,司法部部長傅政華出席會議并講話。
一個全國性工作會議,地點卻選在一個地級城市,且主會場就設在該市司法局四樓的會議室,這種情況實屬少見。此前一個月,省委書記張慶偉則在批示中將該局的調解工作稱為“大慶模式”。
知情人感慨,大慶市司法局今天的“有位”,與局黨委一班人的“有為”密不可分。而其中的領頭人,就是劉勇。
到司法局赴任時,劉勇47歲。
此前,他一直視自己為“職業警察”——從基層民警干起,36歲便任大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有著26年警齡的劉勇原以為會在公安系統退休,沒想到在2011年迎來轉折。
那一年,《人民調解法》剛頒布實施。對人民調解這項司法局的主要業務,劉勇很熟悉。他至今還記得自己剛參加工作時參與的一件事。
一天,他碰到一對夫妻吵架,了解情況后,他先批評男方,又勸說女方,看倆人消了氣,便說:“你倆握握手,就算言和了。”等他回家把這件事說給母親聽,母親笑了:“你連對象都沒處過,還能調解人家兩口子吵架?”劉勇的內心滿是成就感。
在派出所工作11年,他更是天天直面百姓難題;擔任市公安局副局長10年,他有8年分管信訪,其間還因妥善處理一起群體性事件而榮立個人一等功。
他太清楚調解的價值:及早調解,許多小矛盾可能就不會變成大問題。然而,當時司法局的人民調解工作與劉勇的預想相去甚遠。用副局長楊琦的話說:“以家長里短的小事為主,對處理大事難事沒有太大作為。”
工作多年,劉勇喜歡用座談的形式把那些思路不清的問題拿到桌面上,大家開誠布公,來一場“頭腦風暴”,在觀點碰撞中啟發思路。
幾次座談后,劉勇確定了工作方向——聚焦群眾關心的問題,針對交通、醫療等矛盾集中的領域引入第三方專業調解。原因顯而易見:私家車數量呈現井噴式增長,隨之而來的交通糾紛也成了群眾關切的難題。
但有人反對:“這些棘手的事兒,還是離遠點兒好!”
“鐵人說:‘不干,半點兒馬列主義都沒有!”劉勇態度堅決,哪里矛盾突出,就應在哪兒主動作為。
在無經驗可循的情況下,劉勇和交警部門、保險機構反復協商,于2012年5月在大慶成立了9個道路交通事故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聘請退休交警、律師等方面人士擔任調解員。經過幾年運行,9個調解委員會共調處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糾紛11 000件,涉案金額近4億元。此后,大慶市司法局順勢而為,陸續在校園、物業等10個領域成立96個專業性委員會,社會反響強烈;與媒體聯合創辦《說和》欄目,連續8年召開廣場“說和大會”,成功調處矛盾糾紛萬余件。2014年、2015年,劉勇連續兩年在司法部等國家五部委召開的會議上介紹經驗。
如果說專業化調解是常規工作抓出了新意,那么,信訪法律援助機制則是劉勇“撿”來的事業。在這件事上,劉勇不僅有擔當,更有智慧。
針對信訪難題,早在2013年10月,劉勇就在信訪局設立了集人民調解、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詢于一體的信訪人民調解室。
有人直言不諱:“信訪糾紛,別人躲還來不及,你還往上撞?”
大慶市司法局律管科科長史長青打了個形象的比喻:“別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他卻主動請纓,把燙手的‘包袱撿回來。”
而劉勇并不覺得這是“分外事”。他常談及自己在北京遇到的一個上訪10年的農民:因為遭遇簡單粗暴執法,控訴無門,走上上訪路,最終弄得妻離子散。類似悲劇,他聽過不少,也常常想:如果問題及早解決,情況也許大不一樣。
2015年,劉勇帶隊外出考察“把信訪納入法治化軌道”的探索。這期間,他發現有些地方只是依托某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幾個律師,這樣的力量顯然杯水車薪,他要做的是“把全大慶市的律師調動起來”。劉勇由此提出了創立信訪法律服務中心的構想。
然而,現實難點頗多。比如,經費從何來?服務中心以什么身份與訪民簽署協議?
劉勇創造性地提出一個方案:將信訪法律服務中心注冊為“民辦非企業法人”。
這是一步動一子滿盤皆活且一舉多得的妙棋——一旦注冊成功,便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形式化解矛盾,辦案經費也能得到解決。更重要的是,在與信訪人達成協議后,如果對方毀約,服務中心可作為獨立法人追究其法律責任,由此更具約束效力。
這個辦法也同樣適用于人民調解中心。2015年6月2日,兩個中心同日注冊成功。
在信訪法律中心,有四位專職常駐律師,市律師協會還定期選派律師輪值。三年來,該中心累計提供法律咨詢2301件,涉及5227人次,許多十年以上的“長年訪”得到有效化解。
大慶市信訪局局長巴小東評價:“司法局的主動作為,調動廣大律師積極參與,讓專業人辦專業事,促使全市信訪量明顯下降。”
大慶市的律師群體對此舉之所以積極擁護,不僅在于其社會意義,也源于他們把司法局當成了“娘家”。
劉勇甫一上任,便著手解決了律師們反映的“會見難”、進法院難等問題。2015年起,市司法局與律師協會向21位市領導推薦了42名法律顧問,在每位市領導接訪時,由兩名律師現場提供咨詢服務,既提高了領導決策水平,也提升了律師的專業地位。此外,劉勇還鼓勵律師參政議政,全市642名律師有49人當選省、市級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
所以,創立信訪法律援助中心,自然也就一呼百應。
眾所周知,一年一度的司法考試有“天下第一考”之稱,而承擔考務工作的正是司法局。
在2011年之前,大慶市并未設考點。因為這項工作難度大,如若出現作弊丑聞還會惹來麻煩,所以不少地方都敬而遠之。
劉勇覺得,考生到外地應試才是真麻煩。所以,他于2012年申請設立考區。2013年得到國家有關部門批復后,他舉全局之力積極籌備。籌辦第二年,大慶市便成為全國先進考區,第三年便承擔試點工作。
2017年,大慶市成為全國五個“機考試點”之一。面對新挑戰,劉勇帶頭做預案,“保電、保網、保轉場”,在“防替考、防雷同、防高科技作弊”上嚴防死守,全局提前一個月進行演練。當時租用大學教室,因白天學生上課,劉勇就帶大家利用晚上和周末時間演練。考試當天,一個考場的網絡突發故障,由于預案充分、演練到位,他們立即更換教室,確保了考試正常進行。
當年,大慶市司法局被司法部譽為“考出了大慶精神”,劉勇還應邀向全國同行介紹經驗。
當然,劉勇更為“知名”的不是當考官,而是當考生。
司法考試到底有多難?考生真正需要哪些服務?更為重要的是,劉勇在跟律師溝通案情時,發現自己還有一些法律盲區。出于這些考慮,2016年年初,劉勇毅然決定報名參加考試。
劉勇利用晚上、節假日緊張備考,還利用休息日參加培訓班,和一群比自己孩子還小的年輕人一起苦讀。
有好友開玩笑:“你就算考上了,別人也得說是作弊。”
為了避嫌,劉勇特意跑到齊齊哈爾市考試。
“結果不重要,這個過程很重要。”雖然最終功敗垂成,但這一年的努力,讓劉勇體會到了考生的酸甜苦辣,也拓寬了自己的法律知識面。
一次,他在和幾個律師研究案情時,有律師提到一個“善意取得”的概念。劉勇提醒說,“善意取得”的前提是非法,而當事人是合法取得。在場的律師很詫異——沒想到劉勇對法條如此精熟。
大家評價說:“五十多歲的人了,卻有二十歲的沖勁,三十歲的闖勁。”
劉勇的好學也帶動了全局機關干部。如今,每周一、三、五的早上,司法局都要進行晨講,“比學趕幫超”的氛圍十分濃厚。
劉勇的“有為”遠不止上述這些。比如,設立法律援助微信群,在線進行普法、答疑;帶隊到全省監獄走了一遍,對大慶籍服刑犯人開展延伸幫教……如今,大慶市司法局的各項工作已全面開花。
“往大了說,在其位謀其政;往小了說,現在不干,等退休了想干都沒機會。”劉勇的話很實在:今天的成績,屬于所有共事的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