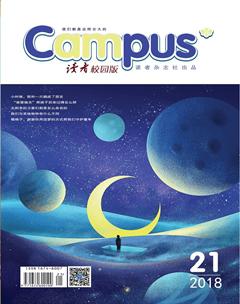一個沒落皇族的另類生活
宋夢寒
《紅樓夢》里有一段“鴛鴦抗婚”的故事,賈母的貼身丫鬟鴛鴦罵嫂子說:“你快夾了嘴離開這里,什么好話?宋徽宗的鷹,趙子昂的馬,都是好畫兒!”連民間歇后語都能“點名”的畫家,其影響力可見一斑。這里說的趙子昂,就是宋末元初著名的書畫家、詩人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是宋太祖趙匡胤的第十一世孫,1254年出生于浙江吳興,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身為皇親貴胄,并非只是享有優越的物質生活,也意味著要比普通人家的小孩付出更多的努力。據說他從4歲開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練字,要站著寫完一萬字才行。雖然無法考證這個傳說的真偽,但趙孟頫長大后博學多才,除了在書畫詩文方面有很深的造詣,對金石篆刻、音樂和文物鑒賞也極為精通,這絕不是光憑天資聰穎、過目不忘就能實現的。

如果說生在皇家是難得的幸運,那么生于走向末路的皇家則是不幸中的大不幸了。趙孟頫11歲喪父,25歲國亡,這樣的人生經歷不是“悲涼”二字可以形容的。但他的生母并沒有因為命運的捉弄而自怨自艾,她一直沒有放松對趙孟頫的教育,甚至在南宋滅亡、趙孟頫極度消沉的時候,她仍然鼓勵兒子:“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你不多讀書,如何超乎常人?”于是趙孟頫奮發圖強,精進學業,很快就名聲大振。在他34歲那年,元朝派人尋訪隱藏在江南的宋代文化名人,二十幾人中他位列第一。元世祖忽必烈見他儀表堂堂、氣度不凡,驚為天人,很快對他加以重用。
《紅衣羅漢圖》是趙孟頫的代表作之一,從畫上的題跋看,是他在江南做官時期所作。畫中一位身著紅色袈裟的僧人坐在菩提樹下,壽眉朱唇,目光深邃,神態靜穆安詳。僧人左手向前,掌心向上,右手藏于懷中。人物頭后有光環,說明不是普通僧人,而是已修成正果、了脫生死的羅漢。
趙孟頫在題跋中說自己對天竺和西域僧人都很熟悉,所以在畫中突出了“高鼻深目”、皮膚黝黑且毛發濃密等區別于漢人的特征。印度佛教在13世紀初就已消亡,加上元代推崇藏傳佛教,所以題跋中所說的“天竺僧”應該是來自西域的喇嘛僧。
《紅衣羅漢圖》中的人物造型及背景樹木均采用古代繪畫手法,人物的神態動作都具有唐代的審美格調。有學者認為這幅畫是趙孟頫借紀念一年前去世的高僧膽巴之名寄托憂思的。膽巴與趙孟頫并無交集,但與南宋最后一個皇帝宋恭宗,也就是瀛國公有過交往。瀛國公彼時遠在西南薩迦寺,所以有人認為趙孟頫是借題發揮,表達對故國故人凄涼境遇的哀嘆。

趙孟頫是歷史上少有的擅長人物、山水和花鳥走獸的全能畫家,他從理論到實踐的創新,使元代文人畫成為中國美術史上的一座高峰。蘇軾開創的文人畫強調的是以“墨戲”抒發文人士大夫的人生志趣。趙孟頫則主張“作畫貴有古意”“云山為師”,以書法入畫,使北宋以來日益瑣碎濃艷的院體畫風轉向質樸自然,在寫實的同時又不乏文人畫追求的高逸的品格。所以明代文史學家王世貞評價說:“文人畫起自東坡,至松雪敞開大門。”明代大書畫家董其昌更是贊其畫作為“元人冠冕”。
除了繪畫上的偉大成就,趙孟頫的書法和文學創作同樣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他獨創了“趙體”書法,與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并稱為“楷書四大家”。他的詩詞文章清邃高古,一掃南宋卑弱習氣,又旁通佛教與道家思想,開創了一代文風,讀來有飄然出塵之感。
然而,因為身為宋代皇族卻做了元代的官,幾百年來趙孟頫一直飽受詬病,連康有為都極力貶低他的書法。實際上,趙孟頫性格溫和、為人清正,他在朝堂之上敢于仗義執言、不畏強權,在民間做官時又懂得發展經濟、體恤民生,故而深得人心。再者,政權的更迭本就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文人的擔當應該體現在造福社稷民生、推動文明進步上,而不是糾結于“不食周粟”的迂腐情結當中。
好在今天我們已經能夠拋開迂腐的“忠君意識”和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念,讓藝術歸于藝術,在文明與開放的環境中繼承和發展傳統文化。趙孟頫,這位生逢變革時代的偉大的開拓者,也終將成為中華文化史上耀眼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