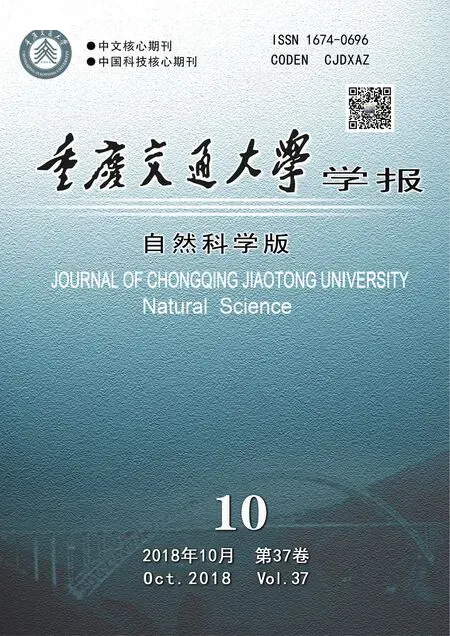道路環境對歷史街區自行車騎行速度的影響分析
王秋平, 王 凱
(西安建筑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學院,陜西 西安 710055)
0 引 言
歷史街區是城市交通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研究的歷史街區界定為:“位于歷史名城之中,保存有一定數量和規模的歷史建筑物、構筑物,能夠體現地方特色、文化風俗且風貌相對完整的地段,主要承擔交通、旅游、歷史教育等多種功能[1-3]。街區內部道路多為單幅路,以滿足慢行交通通行為主”。
近年來,在歷史街區的改造與保護中多引入“以人為本”等理念,彌補了以往僅考慮建筑與風貌的不足[4-5],是傳統道路向街道轉變的重要變革。在保證步行交通空間的基礎上,越來越多的歷史街區傾向于發展慢行或公共交通方式,而自行車能夠較好地與街區的發展理念相吻合,是歷史街區應重點發展的交通方式之一。以鄭州書院街歷史街區為例,其自行車在未來一段時間的出行分擔率將達到50%左右[6],并呈現穩步增長的趨勢,這對街區的道路環境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在共享單車、公共自行車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短距離出行中居民傾向于選擇自行車等綠色出行方式,加之“開放小區”提議的逐步落實,歷史街區的對外交通銜接功能會增強,騎行人數也將增加。另一方面,通過對西安、洛陽、張掖等地進行調研,歷史街區的自行車道寬多為1.0 m左右,但道路功能劃分模糊,道路環境較差,行人與自行車混行嚴重,成為制約街區發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有效保證街區人行交通空間、促進街區自行車發展是關鍵,而騎行速度是表征騎行環境的重要指標,有必要尋找影響騎行速度的主要因素,從而為改善街區騎行環境提供依據。
已有研究表明,歷史街區的自行車騎行速度與騎行者個人屬性、干擾、隔離、非機動車道寬以及非機動車流量等因素有關,各個因素對單輛自行車與自行車流的影響程度不同[7-8],對騎行環境的分析包括兩個方面:考慮騎行者心理承載力[8],計算街區道路合理的非機動車通行能力,以確定最優的慢行交通騎行空間;利用街區內部的支路來組織單向交通或交通微循環,以改善騎行環境[9-10],提高街區路網的可達性[11]。綜上所述,已有研究只是對騎行速度與影響因素的關系進行探討,缺少對兩者之間的變化規律及影響機理進行研究,不能分析出同等條件下哪類道路環境因素對騎行速度的影響概率最大。因此,擬采用Logistic模型[12-16],從概率角度出發來研究各道路環境因素與騎行速度的關系,并對其變化規律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可為歷史街區慢行交通規劃提供理論依據,有利于街區自行車騎行環境的改善。
1 歷史街區自行車騎行速度影響概率 的Logistic模型
1.1 Logistic模型原理
Logistic模型是研究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關系的一種概率型非線性模型。該模型通常先將取值在實數范圍內的值通過Logitic變換轉化為目標概率值,然后進行回歸分析。其中Logistic回歸參數的估計通常采用最大似然法,其基本思想是先建立似然函數與對數似然函數,再通過使對數似然函數最大求解相應的參數值,所得到的估計值稱為最大似然估計值[13]。即:
P=α+βX=α+β1x1+β2x2++βmxm
(1)
式(1)中,P為事件發生的概率;α為模型的截距項;β=(β1,β2,,βm)為待估計參數;X=(x1,x2,,xm)為解釋變量,即模型的自變量。
如果對式(1)作Logistic變換,則logit(P)與x1,x2,,xm間呈線性關系,即[13]:
logit(P)=α+β1x1+β2x2++βmxm
(2)
這是數學上的Logistic曲線,將式(2)描述的P與解釋變量間的回歸關系稱為Logistic回歸。進一步對式(2)進行轉化可得:
(3)
(4)
式(3)描述了因變量P與自變量X之間的一種函數關系。也就是說,對于自變量在(-∞,+∞)的任意一個取值X,因變量都有一個確定的值P=P(y=1/X)與它對應,且P值在[0,1]范圍內。統計學上稱式(3)為變量y在變量X上的一元Logistic回歸模型,因為y僅取1和0兩個值,所以y取0的概率P=P(y=0/X)=1-P,具體表達式見式(4)。
1.2 Logistic模型的自變量選取
1.2.1 騎行速度的影響因素分析
1)騎行者屬性
騎行者的年齡、性別、職業、出行目的、出行時間、出行距離等都會對騎行速度產生影響。通過前期調查,西安市大部分歷史街區的自行車騎行速度集中在12.1~15.3 km/h,其中男性騎行者的速度集中在12.5~15.3 km/h,女性騎行者的速度集中在12.1~14.3 km/h,且女性騎行者的速度更易受到外界環境因素干擾。
2)道路環境因素
道路環境是影響騎行速度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非機動車道寬、人行道寬、道路等級、道路長度、隔離情況、干擾、非機動車流量、行人數量等。
3)其他因素
其他因素包括天氣狀況、自行車特性、道路臨時施工等,考慮到這類因素多為偶然因素,且在共享單車、公共自行車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自行車車輛特征差異不斷縮小,在特殊天氣下(雨天、雪天等)街區選擇自行車出行比例會降低,故筆者在后續分析中暫時不考慮這類偶然因素。
對比城市其他區域,歷史街區道路普遍狹窄,行人與非機動車混行嚴重,隔離設施缺乏,出入口干擾較大,同一街區的道路等級差異不大且多為支路;騎行者屬性對騎行速度的影響主要局限于自由流與穩定流狀態,當飽和流狀態時其影響程度不顯著,而街區的慢行交通設施普遍缺乏,騎行速度相對較低,騎行環境普遍較差,很難達到理想的自由流與穩定流騎行狀態,故重點分析道路環境因素與騎行速度的關系。
1.2.2 自變量確定
通過對騎行速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從街區設施規劃角度出發,結合慢行交通出行特征,選擇與歷史街區相適應的道路環境因素作為自變量,并對其進行編碼賦值。具體結果見表1。

表1 自行車騎行速度的道路環境影響因素Table 1 Road environment influence factors of bicycle riding speed
由表1可知,出入口干擾、隔離情況2個變量為分類變量,根據分類標準進行編碼:對于二分類變量,用數值0與1編碼;對于多分類變量,按照虛擬變量進行處理,如果虛擬變量有k個分類,則將虛擬變量轉換為k-1個變量[17]。上述兩個變量均為二分類變量,故采用數值0與1編碼。
對自變量的篩選分為建模前檢驗和建模后檢驗,建模前檢驗采用比分檢驗(score test),當自變量計算的得分值(score值)對應的概率sig.值小于顯著性水平時,表明該自變量與因變量有顯著關系,可以代入模型進行迭代計算;當sig.值大于顯著性水平時,則剔除該自變量。模型后檢驗采用Wald檢驗法,當計算的wald值對應的sig.值小于給定的顯著性水平時,回歸系數顯著不為零且因變量與自變量關系顯著,否則,認為回歸系數顯著為零且需要剔除該自變量。
1.3 模型構建
以歷史街區自行車騎行速度為研究對象,并將其定義為因變量yi,考慮到騎行速度為連續型變量,首先進行分類處理。通過對西安、洛陽、遵義和張掖等地的歷史街區進行問卷調查,歷史街區自行車騎行速度的心理容忍閾值一般為8~10 km/h,從最不利角度考慮取臨界值8 km/h。當騎行速度小于8 km/h時,表明街區騎行環境較差,騎行速度受到較大影響,騎行者的騎行愉悅度顯著降低,容易產生緊張、煩躁等情緒;反之,則認為街區慢行交通設施完善,外界因素對騎行速度的影響較小,騎行質量較高。因此,可將騎行速度分為兩類:小于心理容忍閾值和大于等于心理容忍閾值。小于心理容忍閾值表示第i段道路的騎行速度受到較大影響,即yi=1;大于等于心理容忍閾值表示第i段道路的騎行速度基本沒有受到影響,騎行環境較好,即yi=0。
因此,假定模型的因變量為yi,7個自變量分別為x1,x2,,x7,結合Logistic模型,騎行速度受到影響的概率為
(5)
式中:α為截距項;β1~β7為待估計參數。
1.4 模型檢驗與評價
Logistic模型的檢驗與評價分為2類:回歸方程整體的顯著性檢驗;模型擬合優度評價。
1.4.1 回歸方程整體的顯著性檢驗
構造似然比統計量,SPSS軟件會結合統計數據給出似然比卡方統計量及對應概率sig.值,如果sig.值不大于給定的顯著性水平,則認為回歸方程整體顯著;反之,則認為回歸方程整體不顯著。
1.4.2 模型擬合優度評價
擬合優度評價的常用統計量包括Cox-SnellR2統計量和NagelkerkeR2統計量。Cox-SnellR2統計量的值越大,表明模型的擬合優度越高;NagelkerkeR2統計量的取值范圍為0~1,其值越接近于1,表明模型擬合優度越高,而越接近于0,表明模型擬合優度越低。
2 實例分析
以洛陽市東西南隅歷史街區為驗證對象,該街區的范圍為:中州東路—新街—九都東路—金業街(見圖1)。通過對街區內的40條主要道路進行實地調查,其中交通量的調查采用錄像法,選取早、晚高峰時段連續拍攝1 h;道路交通設施的調查采用人工實測法,限于篇幅這里僅列出10條道路的調查數據見表2。整理調查數據可得各個因素的統計分析結果見表3。

圖1 東西南隅歷史街區范圍Fig. 1 The range of historical blocks in the East, West and South
2.1 自變量篩選及模型求解
借助SPSS19.0軟件計算Logistic模型:采用反向逐步選擇法,設定置信水平為95%,將7個自變量代入模型,利用比分檢驗法篩選自變量,計算結果見表4,選擇出sig.值小于顯著性水平(α=0.05)的自變量代入模型重復迭代計算。

表4 Score檢驗結果Table 4 Score test results
由表4可以看出,隔離情況、出入口干擾、人行道寬及行人速度對應的sig.值均大于0.05,不滿足α=0.05的顯著性要求,需剔除這4個變量;其余變量的sig.值均滿足顯著性要求,故選擇自行車道寬、自行車流量、行人數量3個變量代入模型重復迭代計算。計算完成后參照wald值對應的sig.值檢驗要求,可得模型的最終計算結果見表5:
由表5可知:自行車道寬、自行車流量、行人數量對應的sig.值分別為0.046、0.008、0.030,均滿足α=0.05的顯著性要求,說明不同的自行車道寬、自行車流量與行人數量會對騎行速度產生顯著影響。

表5 模型參數估計結果Table 5 Estimation results of model parameters
2.2 模型檢驗
2.2.1 回歸方程整體的顯著性檢驗

2.2.2 模型擬合優度評價
通過計算,模型的Cox-SnellR2統計量的值等于0.639,NagelkerkeR2統計量的值等于0.611,接近于1,故模型擬合優度較高。
綜上所述,通過對模型進行檢驗與評價,可知該模型的整體性與擬合優度較好,模型通過檢驗。
2.3 結果分析
通過上述分析,自行車道寬、自行車流量、行人數量對騎行速度影響顯著,模型的整體性與擬合優度均通過檢驗。將表5的回歸系數B代入公式(5),可得歷史街區騎行速度受到影響的概率表達式為
(6)
式中:x1為自行車道寬,m;x5為自行車流量,輛/h;x7為行人數量,人/h。
由式(6)可得,自行車道寬對應的回歸系數為-1.748,表明自行車道越寬,騎行速度受到影響的概率越小;而自行車流量、行人數量對應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11與0.009,表明騎行速度受到影響的概率隨自行車流量、行人數量的增加逐漸遞增。這與歷史街區特有的風貌與交通特性有關,一方面街區內部支路較多,道路狹窄,行人與自行車混行嚴重。當自行車流量與行人數量增加時會占用自行車騎行空間,使騎行者容易產生緊張、焦慮等情緒[18],騎行速度會顯著降低;另一方面,自行車作為歷史街區最主要的交通方式之一,其與步行等慢性交通方式所占的出行比例達到70%左右[6],但街區內部自行車騎行環境較差,容易產生擁擠現象。騎行者出于安全性與舒適性方面的考慮,會適當降低騎行速度。當自行車道寬度增加時,道路阻抗降低[19-20],有效騎行空間進一步提高,騎行環境受到的影響減少,騎行速度趨于理想水平,其合理取值范圍約為8~15 km/h。
進一步分析式(6)可知:其他條件不變時,自行車道寬每增加1.0 m,騎行速度受到影響的概率最大減少0.352,當自行車道寬大于3.5 m(雙向)時對騎行速度的影響概率趨近于零。而CJJ—3790《城市道路設計規范》規定單條自行車道寬宜為1.0 m,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為:歷史街區的路網格局與城市道路不同,所承擔的交通功能也存在差異,以支路為主的街區路網格局限制了機動車發展,但有利于自行車等慢行交通發展,而慢行交通量的增長會對道路環境提出更高的要求,故模型計算結果偏大。同時,單位小時每增加100人可使影響概率最大提高0.250,當單條道路上的行人數量大于500人/h時對騎行速度的影響概率趨近于1。
因此,為了改善歷史街區的慢行交通出行環境,在街區的改造與保護中應結合街區風貌與交通特征,在保證行人交通空間的基礎上,提供足夠的自行車騎行空間,以減少行人流線與自行車流線的干擾,提高出行的舒適性與安全性。
3 結 語
從概率角度出發,分析了歷史街區自行車騎行速度與道路環境的關系,對完善歷史街區保障步行交通,促進非機動化交通發展的相關應用體系具有一定價值。
結合Logistic回歸原理,建立了道路環境因素對歷史街區自行車騎行速度的影響程度量化模型,結果表明:自行車道寬、自行車流量與行人數量對騎行速度影響顯著。其中,自行車道越寬對騎行速度的影響概率越小,騎行速度受到影響的概率隨自行車流量、行人數量的增加逐漸遞增。
歷史街區的改造與保護中,在保證步行交通空間的基礎上,應結合實際道路環境對自行車道寬度進行調整,調整幅度因街區而異。并對各種交通流線進行有效組織及疏導,以減少干擾,提高街區慢行交通出行質量。
文中的驗證對象僅為洛陽市東西南隅歷史街區,后續可增加驗證對象與樣本數據量,并針對不同時段采集交通數據,以進一步檢驗模型的適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