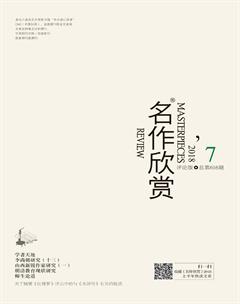《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風俗書寫
壽王菡 王芳
摘要:喬治·艾略特的前期創作主要是以英國鄉村為背景,以普通人的命運為題材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就是一大代表。該作品以英國的一個普通小鎮為背景,其對當地風俗的描寫展現了相關人物的生活狀態,暗示了文章情節的走向,蘊含著一定的生命哲思。本文將以“風俗”作為切入點,從風俗的概念、風俗在小說中的表現和特征、風俗書寫的功能,以及作家對風俗的態度這幾個方面入手,來深度探討該小說中的風俗書寫。
關鍵詞:風俗 概念 特征 功能 態度
小說以英國一個偏僻平靜的小鎮圣奧格鎮為背景,并在此背景下敘寫了英國鄉村一個磨坊主人一家的故事。故事中磨坊主人塔利弗先生的兒子湯姆和女兒麥琪作為主線人物,在經歷美好的童年時代后,不得不開始面對家庭敗落的現實,繼而展開一條曲折的成長道路。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遇到了一系列問題,彼此間也產生了一定的沖突,最終兩人一起沉入無情的洪水。這一結局有著滄海一粟的感覺和綿延深長的意味。湯姆和麥琪的故事只是人間世事運行的一個十分普通的分支,而將其作為一部小說的典型卻有著普遍意義。湯姆和麥琪這兩個人物的精神和行動內涵所投射的是他們所在群體的整體精神和行動,而研究文本所呈現的風俗便是為了深度了解弗洛斯河兩岸人們的生存狀態,并對文本所揭示的生命哲學意蘊有一個更好的體驗。
“風俗”是很多文藝評論都會運用到的一個概念,不同的學者對于“風俗”的界定和理解也不一樣。萊昂內爾·特里林在《知性乃道德職責》一書中對“風俗”有過自己獨到的闡釋:“我所理解的風俗,其實就是由一種文化所蘊含的各種含義所構成的喧囂場面。這部分文化由那些經過隱約表述,或未曾表述,或無法表述的價值話語所構成。這些表述會通過一些細小的行為來得到暗示,有時會通過衣著或裝飾藝術,有時通過語氣、儀態、重音、節奏,還有時通過具有特殊使用頻率或特殊意義的詞匯來得到暗示。”a可見風俗是復雜的、有層次的,如果將風俗單單歸于一些約定俗成的風尚,禮節和習慣等的總和,那么這只是風俗的外化的層次,而滲透在風俗里的深層的文化意識往往具有巨大的隱性力量。它內在地制約著人們的精神和行動,使人物在不同的個性中有著某種共通的特性。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多德森家族和塔利弗家族承載了風俗的烙印。通過文中相關人物的日常起居,行為習慣和處事態度等方面的自然表現,我們不僅能看到一幅幅具有象征意義的風俗畫,還能從這些畫卷中找到人物的定位,發覺故事情節的走向,窺見其中蘊含的生命意識。
一、風俗的表現和特征
文本主要描繪了多德森家族和塔利弗家族一貫而來的風俗,兩大家族雖然有時候會因為一些生活中的瑣事而產生矛盾,家族中每個人也擁有著不同的性格氣質,但是他們兩個家族的血管中都流淌著一種文化的血液。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共同享有著“一套傳統、世俗的想法和習慣”。
(一)機械單調的儀式習慣
文中的風俗書寫主要通過人物的一些日常行為和家庭儀式得以體現,其中多德森家族就有著一些奇奇怪怪的儀式。在喪事儀式中,“帽帶從來不用藍色的,手套在大拇指那兒也從來不裂開,凡是應該來送喪的人都來送喪,柩夫脖子上總有一條圍巾圍著”。在飲食傳統方面,“一個多德森家的女人,到‘陌生人家去,總是只喝茶,吃干面包,絕對不吃任何蜜餞的東西,她不相信人家的牛油,還怕那蜜餞因為糖太少和煮得不透的緣故而發酵了”b。在衣著裝飾方面,多德森家族所要求的儀式感則時時刻刻顯示著。塔里弗太太“是個地道的多德森”,所以當自己女兒麥琪隨意地“脫掉了帽子”,或者將自己的頭發搞得亂糟糟的時候,塔里弗太太總會難以忍受,覺得麥琪沒有遺傳自己的任何優點。可以說,不管遇到什么事,多德森家的人都十分重視自己的穿著和裝飾,力求保持外在的優雅和精致,其中浦來特太太的出場便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如果她帶了一顆破碎的心和一雙眼淚汪汪快看不見了的眼睛,步子偏斜地穿過大門,她會把她的硬麻布袖子碰壞的,她一感到這種可能性,聚精會神地筆直從門框里走進去了。當她感到眼淚很快地往外流,就把發針從帽帶上拔掉,沒精打采地把帽帶扔到后面去—— 一個動人的姿態,雖然在她心境最壞的當兒,這姿態卻表示出來將來一旦眼淚干了,帽帶還是有希望恢復以前的光彩。眼淚減少了一點,她把頭向后仰成一個不會碰壞她帽子的角度……” c
除此之外,多德森家族還有著“永遠保持木器和銅器的整潔、收藏將不流通的貨幣、為市場出頭等的商品和愛購買國貨等等”習慣,這些表層的風俗現象具有一定的喜劇色彩,傳達了多德森一家驕傲利己的心理模式。雖然多德森家的人有著許多對我們來說陌生而又新奇的儀式和習慣,但他們都愿意遵守著這些儀式,并且為自己是個多德森而感到驕傲和滿意。
(二)傳統沉重的家族觀念
多德森家族和塔利弗家族都有著忠于親屬的傳統信念和沉重的家族觀念,這一觀念是靠家族成員之間的親緣關系得以建構的。可以說親緣關系是兩家人處事和論事的基礎,甚至是一道防線。這一風俗要素在文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不僅緊密地維系著家族成員之間的自然關系,還成了人物面臨難題時的必要選擇。
多德森家族一方面表現出高傲的利己主義,“非常厭惡所有損害自己信譽或利益的事物,直率地批評那些對他們不利的‘親屬,但是決不遺棄他們或者不顧他們” d,葛萊格太太在這方面就是一個極為顯著的例子。比如在遺囑問題上,她就強調了好多次:“血統是最基本的條件,個人的品質卻是次要的;不把遺產按照親疏的比例來分配,而單憑意氣來決定財產的分配,她想象起來真是一個會使她終身苦悶的恥辱。”e 正是因為她對多德森素來就有的這一原則的堅決守護,塔利弗先生和她之間的矛盾并不能動搖所謂的宗旨。在文末麥琪離開斯蒂芬回到家后,葛萊格太太對麥琪的態度更是說明了她對“親屬”的極度重視性。“她決不讓自己的朋友幫著別人來破壞這個孩子的名譽,決不讓他們把她從家里趕出去受外人嘲笑,除非她真的變成一個無可救藥的敗壞門風的人。”f葛萊格太太一直盡力地袒護著自己的親屬,維系著自己親屬之間的關系,這也是她生活的基本原則和她一生要追尋的意義。
如果說多德森家族對親屬的忠誠是他們生活的一大原則和宗旨,那么塔利弗家族對于這個問題的信念感則來得愈強愈烈,甚至帶著一種毀滅性的傾向。塔利弗先生在處理自己和妹妹摩斯太太之間的關系時,慎之又慎,生怕影響到自己后代湯姆和麥琪之間的關系,所以當他已經下定決心要向摩斯一家要回自己借給他們的三百磅時,卻因為想起麥琪和湯姆將來的關系而妥協了。雖然塔利弗先生在債務方面有了更大的難題,但他覺得“自己逃過了一個危險”,并且覺得自己對妹妹的感情會影響著湯姆對麥琪的感情。
顯然,塔利弗先生就是如此引導著自己的兒子和女兒的,他和威根姆之間的恩怨一直刻在自己的孩子的心頭,未能得到化解,從而一種沉重的家族觀念得以傳承。塔利弗先生是這么“教導”自己的孩子的:“湯姆,你要記住——如果你真心要做我的兒子,你就永遠不饒恕他。也許將來有一天,你能讓他知道你的厲害。”這一在《圣經》扉頁寫下的復仇念頭就是一道沉重的枷鎖,以至于當后來麥琪和威根姆的兒子費利浦之間互生情愫時,湯姆進行了嚴厲的干涉,并要求麥琪和費利浦之間斷絕往來,給麥琪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在家庭尊嚴面前,湯姆就和自己的父親一樣,毫無動搖之心,毫無妥協的余地。
(三)狹隘滯后的生活法則
一個地域的風俗與當地的自然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塔利弗一家便是生活在一個充滿鄉村氣息的、與外面的喧囂世界隔絕的恬靜的環境里的。在這里,我們能看到滿是樹木的小山,一片片豐饒的牧場,聽到水的急流聲,磨坊的轟隆聲。而一年四季,生活在這片鄉土上的人們,每天都重復著同樣的生活,并且在這種周而復始的生活中感到安心和滿意。
當塔利弗一家出現變故時,他們對生活的原本面目就顯得極為渴望。家里的臺布,瓷器和一些家庭用具都必須賣出去來抵債,整個家變得空蕩蕩的時候,塔利弗先生一家的生活也變得更加空虛,尤其是塔里弗太太。這些原本象征著富裕和溫暖的家什突然沒有的時候,塔里弗太太那符合多德森家驕傲的氣質也受到了打擊,她始終反復地拿過去和現在做比較,一遍又一遍地沉浸于家庭變化帶給她的巨大困惑中,直到現在的生活將其摧殘成一個越來越脆弱的人。這種希望回到過去狹隘滯后的生活理念帶來的只是塔利弗一家更加頹廢的氣氛,他們沒有崇高的原則,沒有浪漫的幻想和積極的人生觀,有的只是一種單調固執的渴望奪回原本屬于自己東西的世俗心理。
而這種落后的生活法則在現代社會終究經不起考驗,就像那兜兜轉轉最后還是回到塔利弗家的磨坊一樣。磨坊是自耕農經濟的一種工具載體,它的存在和運動就意味著農業經濟的發展。小說中唯一出現的道爾考特磨坊是塔利弗一家的經濟來源,它就像是一個祖傳之物,在塔利弗家族經過了五代的傳承。看似穩定運轉的磨坊卻終究抵不過成為一種拍賣品的命運,經過威根姆和迪安先生之手的磨坊,最后又回到了塔利弗家族。但此時的磨坊已經不是作為一種經濟生產工具而存在了,它更多的是塔利弗一家所承載的一個執念而已。在自耕農經濟和工業經濟發生沖突的時候,磨坊漸漸失去了它的主體功能,而只能成為工業經濟的一項有利的投資。
二、風俗書寫的功能
在小說中,風俗的呈現不是作者書寫的純粹的目的,它主要為內在地制約人們的精神和行動而存在。寫風俗實際上是為了寫人,通過對一些風俗現象的分析,我們能對文中人物的生存狀態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對他們的人生觀和價值取向有一個基本的認識。用作者的話來說:“塔利弗和多德森兩家的生活可以是微賤的。在這兒,人們有著一套傳統、世俗的思想和習慣,這種習慣沒有得到指導和完善——千真萬確,這是一種最沒有詩意的生活方式——坐在老式馬車里也能感到驕傲、尊嚴,一種單調的世俗心理。” g而機械單調的儀式習慣,傳統沉重的家族觀念,狹隘落后的生活法則卻貫穿和滲透于這兩個家族里,并且世世代代地傳承下來,異常堅固。這樣的風俗是如何影響著湯姆和麥琪的性格,如何影響著他們倆的生活,我們可想而知。是選擇承受反抗的痛苦,還是被風俗所同化重演一遍歷史,湯姆和麥琪有著不同的態度。但是最終兩人卻共同走向了悲劇,這背后的生命哲學意蘊引人深思,風俗的多面性也由此可見。
(一)一條毀滅性的鎖鏈
特里林在《知性乃道德職責》中揭示了風俗“能將共享一種文化的人們結合在一起,同時將他們與另一種文化的成員相區別”的意義。也就是說,無論風俗是有利的,還是不利的,它寄托著一個整體的文化含義,并要求生活在一個風俗社會的人們都遵守它,內在地實踐它。不然,一個反抗風俗的人在風俗社會是很難生存下去的,會感到叛逆和孤獨的可怕性。
麥琪從小就有著逃避和反抗風俗的傾向。她隨意地對待自己的發型和穿著,行為舉止也和別人大不相同。比如說她總是胡亂放置自己的軟帽,頭發也總是亂糟糟的,衣服褲子很少有整潔的時候,總是挑最泥濘的地方走,等等。從她剪頭發開始,她就注定要品嘗一種被人嘲笑,不被人理解的孤獨的痛苦了。當麥琪不小心將露西推倒在爛泥地里,闖了大禍后,她萌生了逃跑的念頭。她跑到了吉卜賽人所屬的區域里,本想著融入吉卜賽人的生活,和他們進行愉快的交談,但是飲食上的風俗的差異性就讓麥琪感到自己根本不可能成為這個群體的一部分。她想著逃離原有的生活,而這種想法對于一個無知的小女孩來說是愚昧的夢想,她不知道吉卜賽人沒有足夠的飲食,所以對吉卜賽人的態度由熱情漸漸轉變成恐懼。后來,吉卜賽人將她送回道爾考特磨坊后,麥琪得到了一種歸宿感,并嚷嚷著“以后再也不逃走了”。如果說這次大膽的實踐已經讓麥琪嘗到了逃離風俗的可怕性,那么在后來她開始面對感情問題時所做出的犧牲便是刻骨銘心,難以忍受的。
在上文已經提及麥琪和威根姆的兒子之間互生情愫,而受到了湯姆的干擾這件事。湯姆為了家族利益,強迫麥琪斷絕和費利浦之間的來往。他對麥琪的約束不僅僅是外在的,還帶給她心靈上的沉重和煎熬。湯姆將自己承載的這份責任施加給自己的妹妹,并且讓麥琪毫無反抗的余地。麥琪面臨如此具有毀滅性的選擇,感受到了除了服從以外的徒勞性。她和費利浦之間的關系在家族尊嚴和親情面前顯得十分渺小,足夠不堪一擊。麥琪也深深地意識到所謂的愛情或是道德或是理智終究沖不破血緣的桎梏。雖然她覺得仇恨和敵視的延續是邪惡的,但她明白這是一份責任,她只能選擇犧牲而無力反抗。
艾略特認為:“通過遺傳鏈,人的命運是被過去決定的,甚至在他出生前就已經確定。因此家庭的義務和拘束都無可避免地壓在他身上。”h湯姆和麥琪的命運就被深深地鎖在這條遺傳鏈中,他們必須遵循著家族的已定原則,否則就會被視為背叛,感受到孤獨的痛苦。而麥琪在風俗的影響下也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她忍受著別人異樣的眼光,背叛了自己的愛情。她的悲劇是在風俗文化中犧牲的人們的共同悲劇,而這種悲劇正如那流不盡的弗洛斯河水,一代又一代地上演著。
(二)一條回歸過去的河流
風俗內部有著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它反映了一個群體的文化意識形態。處于一種風俗環境中的人們會感到理所當然,并且他們具備在這種風俗中所學到的經驗。但僅僅這些經驗是遠遠不夠的,隨著時代的變遷,局限于某個地域的風俗必然有著其弱點。多德森家族和塔利弗家族的很多人都有著回溯過去的傾向,當外部世界正發生著一定變化的時候,他們狹隘的個人經驗使他們只看得到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得失,而沒有對未來發展的認識。
塔利弗先生一家敗落之際,家里很多東西都必須拿出去拍賣,作為塔利弗一家的經濟來源的磨坊也逃不過被拍賣的命運。經過一次打擊之后,塔利弗先生和塔里弗太太的內心生活陷入了憂郁和痛苦思想的不斷循環中。塔里弗太太一直想要回到過去物質生活富裕的家庭環境中,而塔利弗先生自從破產后身體和精神遭受了雙重打擊,但一直都不乏要贖回磨坊的念頭。
湯姆作為家里的頂梁柱,理所應當地承擔起改變家庭命運的任務,并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努力。亨利·伯格森曾在一本書中寫道:“作為一個有意識的生命體,存在就是變化,變化就有成熟,成熟就是繼續不斷地創造。”i湯姆雖然有很強的能力,但是他缺乏一定的變化意識。他在迪安姨父的幫助下謀得了一份工作并辛辛苦苦地掙錢,以他優秀的業務能力還清了父親的債務。這是他邁出成功的一大步,連迪安先生也十分認同他的經營能力,希望能夠提拔他成為一個善于經營的人才。可是,在湯姆腦海中卻有一個幾年都揮之不去的承諾,便是買回失去的磨坊并進行管理。很顯然,當他對迪安姨父提出這一想法的時候,迪安先生感覺到了一種憂郁的意味。湯姆本可以擁有更加進步的生活,這一切卻成為一條回歸過去的途徑而已。湯姆的悲劇說明風俗中存在了許多不利因素,當傳統思想和新思想,傳統經濟和現代經濟發生沖突時,前者是脆弱不堪的,終將被淘汰。
三、喬治·艾略特對風俗的態度
作者花了大量的筆墨描繪了多德森家族和塔利弗家族的風俗,展現了弗洛斯
河兩岸老派家庭的生活面貌,而文中兩個主線人物的悲劇更是蘊含著無盡的哲思。兩個對風俗持有不同態度的人最終都走向了悲劇,這從隱性層面揭示了作者對于風俗的態度。
首先,《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在一些人物和細節設置上都帶有一定的自傳色彩。書中的塔利弗夫婦及其背景很大程度上是以作者的父母為藍本。而書中深深的父女之情和濃濃的兄妹手足情誼表達的正是失去親愛的父親,又被兄長拋棄的瑪麗安·埃文斯對昔日家庭溫暖的眷戀。作者設置湯姆和麥琪共同走向悲劇的結局讓一種純粹的兄妹關系得到了延伸,這也說明了作者對于風俗中的一些單純的因子是極其留戀的。
其次,一味地逃離風俗和一味地遵循風俗都存在危險。作者在小說中對多德森家族和塔利弗家族的風俗都進行了一定的批判,認為兩家的生活是微賤的,沒有崇高的原則,只關注自身的利益。但是麥琪作為文中風俗的反抗者卻做出了巨大的犧牲,這說明風俗的影響力之大。同時,湯姆堅定地遵循著家族的既有原則,堅持家庭的傳統慣例也是不可取的,這說明風俗存在著弱點,也是作者進行批判的一大原因。
總的來說,作者對風俗的態度是兩面性的。一方面她對過去童年生活中美好的回憶是深深地留戀的,并且揭示了風俗的不可抗性;另一方面她摒棄風俗中保守、狹隘和刻板的因子,同時肯定進步洪流所帶給人們的生活的變化。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作者希望風俗被徹底現代化,這之間作者更想去追尋的是一種平衡吧。
a〔美〕萊昂內爾·特里林.《知性乃道德職責》嚴志軍、張沫譯,譯林出版社,2011版,第107頁
bcdefg〔英〕喬治·艾略特.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祝慶英、鄭淑貞、方樂顏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頁,第50頁,第252頁,第117頁,第455頁,第250頁。
hJeannette King.Tragedy in the Victorian Nov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17.
iBergson Henry .Creative Evolution.Arthur Mitchell(trans.).New York:Random House,Inc,1994,p8.
參考文獻:
[1] 喬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M].祝慶英,鄭淑貞, 方樂顏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2]馬建軍.喬治·艾略特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3]王瓊.麥琪悲劇的成因——《弗洛斯河上的磨坊》解讀[J].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3,23(5).
[4]楊洋,胡文成.解析《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生命哲學蘊含[J].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11(6).
[5]李詠吟.風俗文學與生命的闡釋[J].文藝評論,1993(6).
作者:壽王菡,紹興文理學院人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師范專業本科生;王芳,紹興文理學院人文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荷馬史詩研究和英國小說研究。
編輯:趙紅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