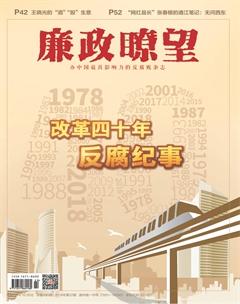華西壩,成都的“西南聯大”
曾勛
華 西壩在成都南門外一公里的地方,相傳為蜀漢都城的“中園”舊址。當年,劉備常常在此地游歷。五代蜀王孟昶更是將這里打造成了自己的后花園,陸游《故蜀別苑》有詩為證:“蜀王故苑犁已遍,散落尚有千堆雪。”
20世紀初,封建社會即將壽終正寢,曾經的“皇家園林”早已不復往日繁華,華西壩成了一片水田和墳地。1904年,經基督教四個差會確定籌建私立華西協合大學校后,1907年首先購地150畝,到1950年占地1200余畝。抗戰爆發后,中央大學醫學院、齊魯大學、金陵大學、燕京大學、金陵女大等大學內遷至華西壩,此地一時人文薈萃,有人稱這是成都的“西南聯大”。
華西壩的那段歲月,史稱“五大學時期”,英文叫“Big Five”。燕京大學新聞系是整個亞洲最好的新聞系;華西協合大學的人類學研究形成了影響至今的華西人類學派;金陵女大的女子教育培養了一批女科學家、女將軍、女教育家。
1941年春末,海明威訪問中國,在華西壩五校演講,一時成為了當時的文化熱點。據聽過他演講的人回憶,這位美國作家完全不像中國文人那般斯文,他身體壯實,吼叫一般地講演時,長滿汗毛的手臂不斷揮舞,倒像個“殺豬的黑漢”,不時獲得暴風雨般的掌聲。
香港的《大公報》報道,海明威的激情演講鼓舞了成都的學生。“上前線,則吾國士兵英勇,抗戰的偉大,當可揚名海外,長垂不朽”,成都許多大學生報名從軍,開赴前線殺敵報國。
知名作家譚楷在華西壩長大,他回憶:“那時候,徐悲鴻曾在女生院門外徘徊,等著讀金陵女大的廖靜文;經濟學巨擘吳敬璉還在華西后壩上初中;著名作家韓素音還在小天竺街的進益助產士學校學護理……”創辦華西協合大學的先驅們給中國西部的絕非是“滴水之恩”,他們帶來了當時最先進的醫療技術,拯救了成千上萬的生命。
“童年時的華西壩,其風光之秀麗,不比我后來在加拿大、美國見識過的名校遜色。一位加拿大教師曾觀察和研究過華西壩20多種奇異的鳥類,它們與壩上縱橫交錯的小溪、濃蔭如蓋的樹林組成了華西壩田園牧歌般的詩意境界。”譚楷雖然后來移居國外,但是對家鄉的真摯感情,卻從因物理距離而減弱,反而隨著時間的流失,愈加強烈。于是,他將華西壩的記憶和故事以及自己對故鄉的思念,傾注到了《楓落華西壩》這本書中。
在譚楷的記憶里,人民南路尚未將華西壩一剖兩半之前,在赫斐樓西北方向,是一大片黑壓壓的柏樹林。當年,華西壩的孩子們比誰膽子大有三個項目,一是敢不敢獨自一人半夜12點到鐘樓下聽鐘聲;二是敢不敢天黑之后鉆進二廣場的“野豬林”;三是敢不敢偷偷溜進一教學樓的解剖室去看尸體。
后來,譚楷聽父親說,赫斐樓前曾發生過一起兇殺案。被害者是華西的副校長、化學系系主任蘇道璞博士。
蘇道璞是英格蘭人,出生于1888年,于1913年到成都華西協合大學任教,此后在華西壩工作生活了17年。在中國期間,他出行從不坐轎子,他說:“坐轎子很不人道。我不愿把中國人當作牛、馬一樣使喚。除非有病走不動,否則我永不會坐轎子。”
由于不愿坐轎子,所以蘇道璞常騎自行車,成都人把自行車叫做“洋馬兒”,當時極少。1930年5月30日晚,四個氓流為了搶自行車,刺傷了蘇道璞。6月1日,他因肺與腎傷勢太嚴重而逝世,年僅42歲。他讓妻子瑪格里特·萊斯轉告中國政府:“兇手已使我家破人亡,成了一位不幸的寡婦,如果殺了他,他的妻子也將成為寡婦,懇請你們從輕發落吧。”這一消息令無數人動容。
在華西壩與蘇道璞有師生之誼,又同是公誼會成員的楊振華回憶:“自從我轉學到成都念青龍街廣益小學后,每星期日在公誼會禮拜堂里都看見蘇道璞博士。他穿著西服,對中國的男女老幼都很親切,毫無有些洋人的傲慢態度。”
在兵荒馬亂的年代,華西壩還有許多像蘇道璞這樣的洋學者洋醫生,用一次次治病救人詮釋人性的仁慈與寬厚。
因為華西壩與那些仁人志士,成都市民有了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使用牙刷;第一次種牛痘;第一次吞下西藥片劑;第一次接受外科手術;第一次通過顯微鏡看到了活動的細菌;第一次曉得心臟與血液循環……如今,華西壩的文化意義仍在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