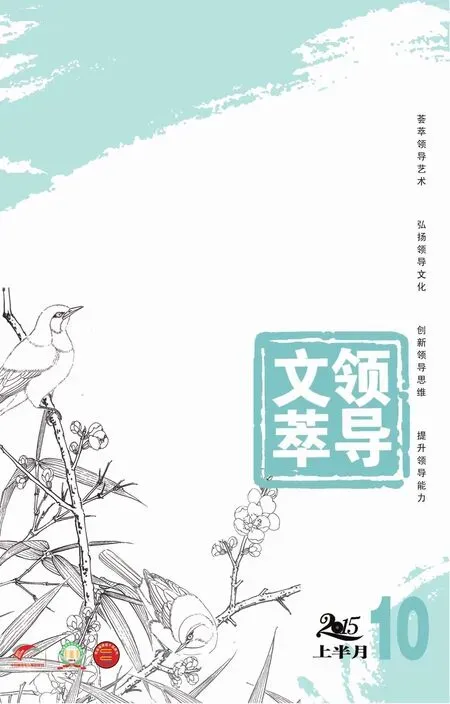我讀曾國藩
菊潭
曾國藩是晚清“中興名臣”,是極為引人關切的歷史人物。當今社會出于多種原因,以不懈的熱情出版他的日記、家書、詩文乃至奏折。這一文化現象,發(fā)人深省。曾國藩這位農家出身而逆襲于晚清社會的政治家,其志向、修養(yǎng)、人格、智慧,確乎值得揣摩和借鑒。
曾國藩生長于湖南的窮鄉(xiāng)僻壤,他雖覺得天分不甚低,但未離鄉(xiāng)前全被茅塞,孤陋寡聞。直到進京三番赴考,悉心而讀大家名家著述,才豁然開朗。在同鄉(xiāng)理學大師唐鑒的指導下,以朱子為正宗,開始梳理自己的學術理念,于義理中探求經世之術,取得了質的飛躍。他每日不拘何時,都力求在“靜”字上下功夫,以束檢身心,讀書明理。他的著力點在于格物、誠意,通經致用,不談過高之理,不行駕空之事。顯然他的讀書不在于使自己成為一個學問家,而是早有宏大抱負,“匣里龍泉吟不住,問予何日斫蛟鼉?”他懷抱著澄清天下,拯救世道人心的大志。他說“千言萬語,莫先于立志。”這應當是我們讀懂曾國藩的第一要義。
曾國藩一生中堅持以讀書的勤勉、深刻、學以致用,成就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風范。從他的日記、家書及詩文評述中可以充分感受到他的孜孜不倦和勤于思考。他在精研《朱子全書》前就博覽司馬遷、班固、李白、杜甫、韓愈、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他在繁忙的公務、應酬而外,讀書、寫字、下圍棋,成了必修課。讀書破萬卷的智者可貴的在于常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典籍,既不以博雅自詡,又自能堅持己見;從不一味崇尚空談,而以自強的信念、務實的態(tài)度,沖破傳統文化的藩籬,順乎時代潮流而有所作為。比如,他的倡洋務,是對西學東漸現實的正視。他的釆納容閎建議,奏請派送留學生出洋等,正是格物誠意的信條下合乎歷史邏輯的經世思想和開放意識。這使他與皓首窮經的“牧豬奴”的讀書價值有天壤之別。欲讀懂曾國藩,必須有這一層鮮明的價值評判。
曾國藩的一生實踐著他以圣賢為榜樣的自我完善。他的修養(yǎng)和人格魅力被人們所欽佩是理所當然的。他的反省之勤,改過之勇,慎獨和居敬,習勞不倦和自覺,言教與身行,都有著感人的事例。他自覺地探索人性與社會性的課題,提出了許多富有人生智慧和處世謀略的思考。他概括的天道三惡:惡乖巧、惡盈滿、惡不忠誠;人道四知:知命、知禮、知言、知仁,以及涼德三端:幸災樂禍、不安命與好議論,君子三樂:讀書聲出金石,飄飄意遠;宏獎人才,誘人日進;勤勞而憩息。這些可貴的思想收獲都是修身養(yǎng)性的真功夫,都與他的仁愛之心,軒昂志節(jié)乃至纏綿情致分不開的,是一般士大夫所不能達到的境界。敬以持躬,恕以待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戒惰戒傲,平實為歸,接物以亷,以至將敬畏師友、和睦家庭為大學問,克己自律,自我完善。他是將傳統文化履行于人生事業(yè)的仁人志士。因此能在艱難困苦中磨煉心靈的堅韌和自在。
我讀曾國藩也留意于他的豐富的情感世界,留心于他放大胸襟和游心物外的真知篤信。早年的思親詩句:“鄉(xiāng)思怕聽殘漏轉,逸情欲逐亂云飛”;懷友詩句:“碧樹哪知離別憾,青燈偏照故人書”;憶內詩句:“幾回南國思紅豆,曾記西風浣碧紗”;寄閑適之情,“蜉蝣身世知何極?蝴蝶夢魂又一場”;寓閑游之慨,“自笑此身何處著?笙歌叢里合閑游”,等等,可誦可感,亦是仁禮相隨、知命聞道的詩心文釆。此間韻味何其纏綿。他有過傷感和郁悒,有過閑適與曠達,卻以平實為旨歸,將文化精粹滲透于多彩人生。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以歷史唯物論評價一位歷史人物是一件異常審慎的功夫。史學界給我們提供了良好的思維空間。聯想近代以來,毛澤東、蔣介石、梁啟超等非凡人物對曾國藩的評述,恰恰說明我們更有讀懂他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