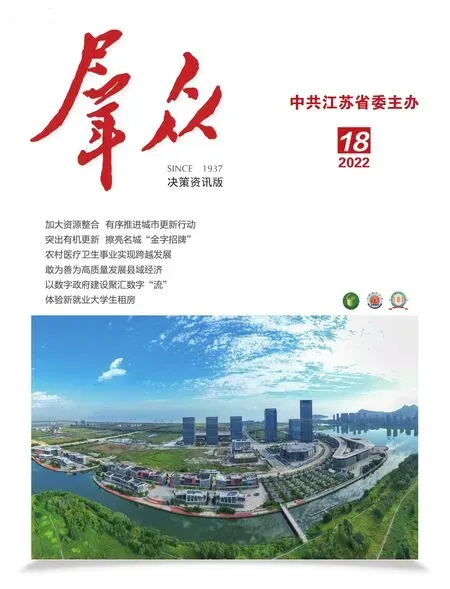曾國藩的“八本”之教
李澤昊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毀譽參半的著名人物,他在個人修養、品格及才能方面有過人之處。曾國藩死后,清廷賜謚“文正公”,這是清政府所能給予臣子的最高評價。中國近現代史上諸多有名望的人物,如李鴻章、梁啟超、蔣介石等等,都對曾國藩稱贊有加。
曾國藩的人生已然達到儒家的立德、立言、立功的高度,即古人所謂“三不朽”的境界。1917年8月,毛澤東給好友黎錦熙的信中,稱曾國藩為有“大本大源”之人,并說:“予于近人,獨服曾文正。”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給黨員干部講課時說:“中國歷史上不乏建功立業之人,也不乏思想品行影響后世之人,前者如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辦事兼傳教之人,歷史上只有兩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國藩。”毛澤東的二者兼有,乃是指其不僅“德業并進”,做到經世致用,而且能夠以身作則,思想可為萬世師表。
曾國藩常年在外行軍、為官,但卻絲毫不放松對身在家鄉的后輩子侄的教育問題。在給家人寫的1500多封家書中,他將一生的處世哲學融入其中,其文坦率、真誠、理通、意達,字里行間滿溢對后輩子侄的教誨、規勸、訓誡。而他對子弟后輩的教導是成功的。曾氏后人可以說是人才濟濟,其子曾紀澤、曾紀鴻,其孫曾文鈞,曾孫曾寶蓀、曾約農等等,在各個不同領域都很有成就。這一點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比較少見的。
曾國藩曾將其家訓要義總結為“八本”,并在老家富厚堂的一間屋子上,高懸“八本堂”橫匾。“八本”者,即“讀書以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戒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作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曾國藩將“八本”書之于匾,高懸門楣之上,足見對此的重視。他認為,只要能守此“八本”,不管世道如何,家運都能長盛。
第一,讀書為自強自立之本。“八本”以讀書做學問為先,可見曾國藩對其重視程度,他甚至將讀書放在“人生第一美德”的高度。
為何讀書?因為讀書是自強自立的基礎,只有讀書,才能成就內圣外王之業。曾國藩說:“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圣賢立言,必能明圣賢之理,行圣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為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于修己治人之道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強自立做出,即為圣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
訓導子弟讀書,學而優則仕,以此光耀門楣是傳統家訓的常談,但是,曾國藩卻強調讀書的目的是自立自強,各行各業做得好,都可以成為第一流的人才,不必非得走做官這一條路。在這種教育理念下,次子曾紀鴻后來就成為近代著名的數學家。曾國藩身居高位,如此見識,確實難得。
如何讀書?曾國藩認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志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有恒則斷無不成之事。”志,指的是堅定的信念,對自己人生道路選擇的明確性、目的性及高度的自覺性。他說:“人茍能自立志,則圣賢豪杰,何事不可為?……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于我哉?”識,是作出判斷及認識的能力,體現的是人的格局和胸懷。有識,則“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牛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曾國藩雖然學富五車,但仍將自然科學知識貧乏視為人生缺憾,甚至是自己“三恥”之一。“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恒星五緯亦不識認,一恥也”。因此,他主張子弟努力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這實際上是近代西學東漸這一客觀情勢在曾氏家訓中的具體反映。恒,是對既定目標堅持不懈的努力。曾國藩認為,讀書不可用力過猛,“讀書用心,亦宜儉約,不使太過”。讀書過于刻苦,不利于養生。其貴在持之以恒,好比溫火煮肉一般。“今日不能,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只要每日有常,自有進境。
第二,孝、靜、誠、勤為修身齊家之根。“事親以得歡心為本”,是曾國藩對孝的理解。百善孝為首,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孝敬父母,不僅僅需要物質贍養,還必須注重精神贍養。曾國藩強調,重厚人格是立身處事之基。他訓戒子弟,向平實處用力,做一個“篤實人”,即忠厚老實人而不是投機取巧者。
“不晏起”是曾國藩的治家之道。它看似簡單,實行卻不容易。他訓教子侄:“祖輩皆未明即起,竟日無片刻暇逸。”“勤”字功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恒”。曾國藩認識到,只有勤勞,才能知衣食之來之不易、父母養育兒女的辛苦,從而杜奢尚儉,心懷感恩孝敬之心。雖然自己常年在外,曾國藩卻不忘一再告誡妻子及長子,應起到組織和榜樣作用。“吾夫婦居心行事,各房子孫皆依以為榜樣,不可不勞苦,不可不謹慎”,“家之興衰,人之窮通,皆于勤惰卜之”。可見曾氏用心之良苦。
第三,不貪錢財為從政做官之道。作為湘軍最高統帥,曾國藩一年合法收入為白銀5400兩,帶兵12年,收入可達64800兩,何況在戰亂時期,他擁有絕對的財政權,湘軍軍費的發放,全靠他一支筆。戰事平息后,他又身任要職,主持洋務,由于當時沒有正規的財政制度,曾國藩如稍有貪念,完全可以上下其手、中飽私囊。但是,曾國藩并沒有因為當官而發財致富,他說:“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盡管官祿頗豐,但他將合法的工資收入也多用在軍隊開支、救濟百姓、捐獻公益等方面。他每年寄回家中的銀兩,只在100兩左右。
寧可把大量錢財用于公務,施舍他人,也不寄回家里,留給子孫。曾國藩有自己的考慮:一是為清王朝的中興事業。“作官不要錢、行軍不擾民”正是為挽救世道人心。導致太平天國運動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吏治腐敗,官場作風敗壞。在鎮壓起義軍的過程中,曾國藩認識到廉潔對于戰斗力的重要性,只有立定“不要錢、不怕死”之志向,才能組織起一支真正有戰斗力的隊伍。
二是他認為奢侈的生活環境不利于子孫的發展。曾國藩曾說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話:“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飯;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后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所以不多寄錢回家,是擔心家風因此而壞。“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后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疼愛子女,乃天下父母之心,而中國父母于此更甚。自己省吃儉用,卻要讓子女吃好穿好,還得為他們留下豐厚財產。但是,清貧常能激勵人去追求向上;過多的金錢,反而誘惑人走向墮落。曾氏家教嚴格,亦不留財產給子孫,其家人才輩出,余慶綿綿。而同時代許多“中興將帥”的子孫們,由于勛爵和財富的坑害,重蹈八旗子弟的覆轍,很快便把祖輩的家業敗落得一干二凈。今天,當我們重溫曾氏不蓄銀錢給兒孫的話時,不僅感悟到一種深遠的歷史智慧,更從中感受到一個長者對后輩的真愛大愛。
(作者系常州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