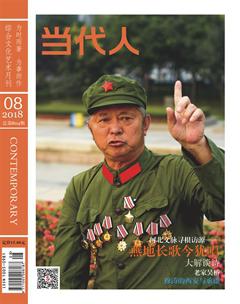戰(zhàn)地記者雷燁
安新麗
在抗日戰(zhàn)爭的艱苦歲月里,一位文采出眾、備受矚目的戰(zhàn)地記者,主動請纓深入環(huán)境極端險惡的冀東前線,轉戰(zhàn)灤河兩岸、長城內外。他用相機當武器、以紙筆作刀槍,為抗戰(zhàn)時期的新聞事業(yè)立下汗馬功勞。然而,他卻過早地犧牲在冀西抗日根據地太行山上,年僅29歲。他,就是八路軍總政治部前線記者團第一組組長、冀東軍分區(qū)組織科長——雷燁。
在華北軍區(qū)烈士陵園內,雷燁烈士的墓碑上寫著“青年詩人雷燁烈士之墓”幾個大字,沒有其他相關的碑文。60多年過去了,雷燁默默無聞地長眠在蒼松翠柏之中,他的墓前不曾留下過親人的腳印和淚水;雖然工作人員多方查找,但一直未能找到雷燁的家鄉(xiāng)和親人。他幾乎成了被遺忘的英雄。
在杭州,項秀文一家,60多年來一直苦苦尋找1938年去延安投身抗日的哥哥——項俊文,但始終杳無音訊。
讓我們把時間回溯到20世紀30年代,回到那段血雨腥風的抗戰(zhàn)歲月。
項俊文,出生在浙江金華的一個農民家庭,他自幼聰敏好學,曾考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學”。項俊文在剛剛讀完初二時,父母雙亡,不得不輟學,挑起養(yǎng)家的重擔。這期間,他在為生活而奔波的同時,仍關注著時事。國難的日益深重,使他心急如焚,熱血沸騰,經常教弟弟唱《國際縱隊之歌》《松花江上》等歌曲。項俊文在1934年給摯友許為通的信中表示:自己“不會于這世界上空跑一趟”。
1938年初春,項俊文變賣家產,安置好家人,奔赴延安,并改名為雷燁。為避免家人和好友受到牽連,他在給好友寫信時既沒有署名項俊文,也沒有署名雷燁,而是用了雷雨。就是這一字之差,卻讓他的家人苦苦尋找了半個多世紀。
在抗大第四期學習班學習期間,雷燁榮獲了“突擊隊員”的光榮稱號,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作為多家報刊的特約記者,他先后撰寫了《抗大同學畢業(yè)上前線》等通訊,拍攝了《抗大四期畢業(yè)歡送大會上毛澤東先生致訓詞》等照片,發(fā)表在武漢《新華日報》上,并配發(fā)毛澤東題詞,引起了強烈反響。由于表現突出,雷燁入選八路軍總政治部前線記者團,并擔任第一組組長,前往晉察冀根據地進行采訪報道。
1941年,日寇在冀東進行了野蠻大屠殺,雷燁聞訊后,義憤填膺,主動要求隨軍挺進環(huán)境極端險惡的冀東抗日最前線,他發(fā)起并創(chuàng)立了文化團體“路舍”,創(chuàng)辦了文藝刊物《路》《文藝輕騎隊》等,進行廣泛的抗日宣傳。在這期間,他用相機拍攝了數以百計的戰(zhàn)地寫真,記錄了那個大時代血雨腥風的片段。在他拍攝的《日寇燒殺潘家峪》組照中,大片房屋只剩殘垣斷壁,空地上是成堆的尸體;斷壁上置放著被大火焚燒的頭顱;燒焦的尸體成團地扭結著,掙扎般矗立。一幅幅慘烈的畫面,向世界吼出了悲憤的心聲。雷燁的一系列作品得到了《晉察冀畫報》社長沙飛的高度贊賞,當即決定出版專輯。
1943年1月22日,雷燁作為晉察冀邊區(qū)參議員到平山縣參加會議。邊區(qū)會議結束后,雷燁把他在冀東四年來的戰(zhàn)地攝影資料送到駐平山縣曹家莊的晉察冀畫報社,并應邀留下,選定照片和編寫說明。4月19日深夜,數百名日軍自南而北向曹家莊襲來。雷燁聞訊后,立即帶領兩名警衛(wèi)員查看村民的轉移情況,發(fā)現有幾百村民正聚集在一處容易遭敵炮擊的地方,便馬上指揮村民轉移。果然不出所料,日寇瘋狂地向村民所在地進行了炮擊,村民感激地說:“多虧雷燁的關照,不然還不知道死多少人呢。”
4月20日拂曉,畫報社的其他同志已經安全轉移。雷燁和兩名警衛(wèi)員走到南段峪石堂村時,與敵遭遇,雙方激烈交戰(zhàn),他們先后擊斃了10余名敵人,但雷燁卻不幸負傷,在生死關頭,雷燁毫不猶豫地對警衛(wèi)員說:“我來掩護,你們趕緊突圍!”警衛(wèi)員執(zhí)意不肯。雷燁斬釘截鐵地說道:“要死死一個,不能都死,你們快撤!不要管我!這是命令!”
看著警衛(wèi)員含淚突出了重圍,雷燁繼續(xù)與敵奮戰(zhàn),當敵人沖上來時,身負重傷的雷燁從容不迫地將心愛的照相機、自來水筆、望遠鏡砸碎,用最后一粒子彈結束了自己年僅29歲的生命。
戰(zhàn)斗結束后,警衛(wèi)員返回畫報社述說了雷燁壯烈犧牲的經過。畫報社的同志和村民聞悉后,捶胸頓足,無比痛惜。在沙飛和畫報社指導員趙烈?guī)ьI下,他們立即趕往出事地點,在清理遺體時發(fā)現一本血染的相冊,夾著雷燁的攝影作品。沙飛摩挲著相冊,朗聲誦讀雷燁在相冊上寫下的憤怒譴責日寇暴行的慷慨之詞,聲淚俱下,在場的人無不失聲痛哭。2000年5月,雷燁入選《正義與勇氣——世界百名杰出戰(zhàn)地記者列傳》。
讓我們把時間閃回到2001年8月。已經找尋哥哥達半個多世紀之久的項秀文,幾經周折終于確認了雷燁就是雷雨,也就是他的哥哥項俊文。
百感交集的項秀文哭了整整一天,項俊文離家后的傳奇經歷讓他震驚和感慨,哥哥的音容笑貌從未如此清晰地浮現在眼前,一如他毅然北上延安,奔赴抗日戰(zhàn)場時充滿希望的笑臉。
編輯:耿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