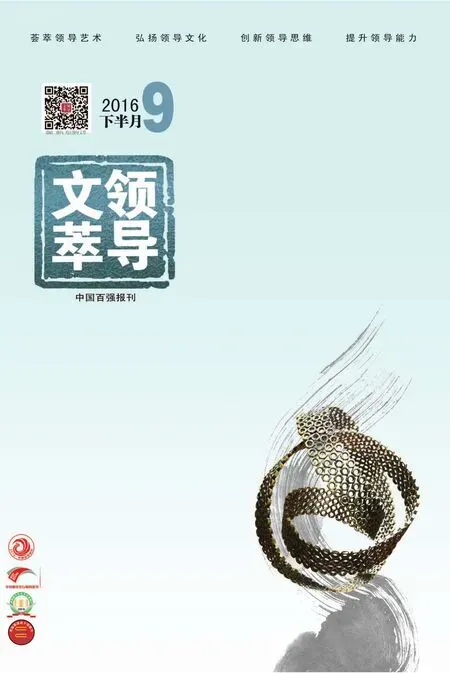還能一起愉快地喝酒嗎?
事情發生在湖南懷化。2018年5月5日,楊某參加初中同學聚會。席間,楊某與8位同學喝了米酒。當晚,楊某酒醉不醒,被同學送到家樓下。第二日中午,楊某在家中被發現已死亡。后來,在某司法所調解下,死者同學同意共同賠償死者家屬十余萬元。類似的案例時常見諸報端。例如2014年,在廣西某大學讀研的丁某和4名同學聚餐飲酒,結果丁某醉酒后死亡。現場監控顯示,當天飲酒,4名同學并不存在勸酒的情形。法庭判決死者同學對丁某的死亡損失承擔10%的賠償責任,共需賠償丁某家屬7.4萬多元。還能一起愉快地喝酒嗎?
正方: 2004年施行的最高法《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過失致人損害,或者雖無共同故意、共同過失,但其侵害行為直接結合發生同一損害后果的,構成共同侵權。在司法判例中,如果飲酒后出事,有4種行為同桌飲酒者需承擔法律責任:強迫性勸酒,比如用“感情深一口悶”等語言刺激對方喝酒,或在對方已喝醉意識不清無自制力的情況下仍勸其喝酒;明知對方身體狀況不行、不能喝酒仍勸其飲酒,誘發疾病;未將醉酒者安全護送;對酒后駕車、洗澡、劇烈運動等行為未勸阻。
反方: 成年人同桌飲酒理應自負其責。大家都是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應當知曉過量飲酒可能對其行為能力及身體健康產生不利后果,本人也應當比同桌更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如何、適不適合飲酒、能飲多少酒。在楊某一案中,同學在楊某醉酒后將其送至他家樓下,已經履行了醉后照看的義務。接下來照看的義務已交由其家人。楊某是第二天在家中被發現死亡的。如果楊某醉酒嚴重或醉后嘔吐物窒息氣管,其家人應該安排就醫或進行家庭急救處置。
正方:在楊某一案中,死者同學接受調解,共同賠償死者家屬十余萬元。雙方沒有走法院途徑。從賠償金額來看,死者同學承擔的應該是次要責任。畢竟,同學并沒有面對面將楊某交給他的家人。新疆楊某與兩位喝酒后醉酒溺亡,家人起訴同飲者。法庭判決是死者楊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對其過量飲酒造成的嚴重后果承擔80%的主要責任;同飲的兩位未完全盡到自己的安全注意義務,具有一般過失,應對楊某死亡的后果共同承擔20%的次要責任。
反方:司法實踐的一個趨勢是對同飲者施加了越來越大的法律負擔,這是值得商榷的。2014年,在廣西某大學讀研的丁某和4名同學聚餐醉酒后死亡。現場監控視頻顯示,4名同學在與丁某共同飲酒的過程中,不存在強迫勸酒的情形。但自斟自飲、各自隨意也不行,法庭認為,4名同學“應當對同飲人丁某的酒量和承受能力做出符合常理的必要判斷,并給予必要的勸阻”,4人未盡到注意義務,存在一定過錯,對丁某的死亡損失承擔10%的賠償責任,賠償丁某家屬7.4萬多元。從“勸酒要負責”到“不勸阻喝酒也要負責”,還能同桌飲酒嗎?
正方:中國的酒桌文化本就是一種陋習。狂喝濫飲傷害身體誰都知道,許多人本不想喝或不想多喝,但在各種言語、感情綁架之下,為了聯絡感情或對別人表示尊重而不得不喝。司法實踐讓同飲者負擔更大的連帶責任,可以殺一殺這種不好風氣。也能讓不想喝的人有了好的拒絕理由。
反方: 但應該設定一個合理的責任邊界。如果說醉酒后發生事故,勸酒者多少要承擔責任,但自斟自飲、沒有勸酒的同桌有什么責任?要是勸阻喝酒成了法定義務,那應該只由同桌飲酒者承擔呢,還是同桌不飲酒者也要承擔呢?經營餐館者要承擔責任嗎?難道同飲前要立生死狀?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