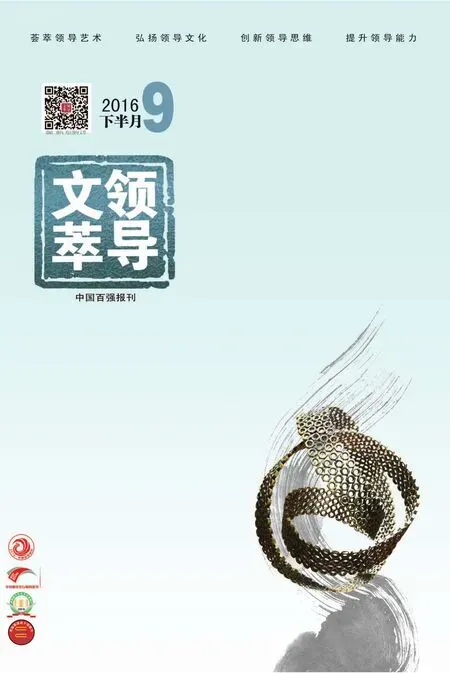愛因斯坦的人生哲學
李武祥
2017年10月16日,科學家們在多國宣布成功探測到第一例雙中子星引力波事件。人類首次窺見引力波源頭的奧秘,“聽”到宇宙的聲音,我國科研人員還借助引力波光譜解開了宇宙中金、銀等超鐵元素的產生之謎,預示著引力波天文學時代來臨了。什么是引力波?被譽為“時空漣漪”的引力波對我們的生活會有怎樣的影響?回答這些問題,首先讓人想起一百年前預測引力波存在的廣義相對論,想起天才的科學大師愛因斯坦。重讀《愛因斯坦傳》(沃爾特·艾薩克森著,張卜天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品味解密后的愛因斯坦閃爍著天才的智慧和詼諧的“語言”,可以從一個側面領悟這位科學大師的人生哲學。
“大”“小”論:沒有邊界,只有探索
愛因斯坦科學研究的領域,小到量子,大至宇宙。天地之間,他如一束光,將思想的光芒深入到浩瀚的宇宙和微小的量子,照亮了物理學探索前行的路。
時間和空間,我們每一個人每時每刻都面對,對一般人而言,從不需要為時間和空間問題操心,但愛因斯坦不一樣。他對時空的興趣自小而有、終生探求、樂此不疲。還在四五歲的時候,愛因斯坦病臥在床,爸爸給了他一個羅盤,羅盤小磁針竟然聽任一種看不見的東西(場)擺布,這與平日里通過接觸而起作用的力學方法完全不同,這種神秘的力量讓他激動得渾身顫抖!后來,愛因斯坦終身都致力于用場論來描述自然。引力是時空結構的彎曲,“一只瞎眼的甲蟲在彎曲的樹枝表面爬行,它沒有發現它爬過的路徑是彎的”。基于“引力會使光線彎曲”這個概念,他預言了從遙遠恒星發出的光經過太陽附近的強引力場時彎曲的程度。追趕一束光會是什么樣子?1895年,年僅十六歲的愛因斯坦就在想象自己如果與一束光并肩前行會發生什么情況。十年以后,他以研究論文回答了自己的設問,成為一名真正的光束騎士。
“非”“常”論:蔑視權威,敬畏規律
愛因斯坦的卓越在于他是一個孤獨者、反叛者和不循規蹈矩的思想者。他對自然規律充滿敬畏,相對逆道而行者,顯得那么反叛;他深切關懷人類,相對熱鬧的世俗者,他顯得那么孤獨。在“非”“常”之間,他如一個神,締造了科學史上一個劃時代的神話。
在愛因斯坦的個性中,也許最重要的是不愿意服從權威。他最大的思想激勵來自一個學醫的學生塔爾穆德,這個“家庭教師”帶給十歲的愛因斯坦一套配有插圖的《自然科學大眾叢書》、一本幾何學教科學,并向他推薦康德,介紹哲學。這套二十一本小書組成的叢書是亞倫·伯恩斯坦寫的。“這套書我是目不轉睛一口氣讀完的。”對自然科學和哲學親密接觸,培養了愛因斯坦對一切形式的教條和權威的反感。“盲目地迷信權威是真理的最大敵人。”愛因斯坦后來還發表了一條極有啟發性的評論:“為了懲罰我對權威的蔑視,命運把我自己變成了一個權威。”
對于任何可能束縛其自由的事情,愛因斯坦都退避三舍。他是冷漠超然與渴望友誼的矛盾體,他的超然態度甚至反映在他的婚姻和愛情上。只要女性不會對他有所要求,而且讓他覺得可以自由接近,或者不受他的喜怒無常所左右,那么就能維持一段“風流韻事”;一旦擔心可能失去某些自由,他就豎起盾牌。“我實在是一個孤獨的過客,我從未全心全意地屬于我的國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親近的人。”他年輕時與大學班里唯一的女同學米列娃因志同道合而結婚育子,臨近中年時又因雙方的無法理解或者講主要由于愛因斯坦處理個人事務時缺乏耐心而分手,轉而與大他好幾歲卻處處能容忍他的表姐愛爾莎結婚。他不擅長理解別人的處境,哪怕是他的妻子,沒有能力設身處地地為他人的感情生活著想。對妻子米列娃他是愛恨交加。他的朋友評價,他不會真正受到傷害,他的生活充滿了淡淡的愉快和冷冷的情感,他的溫文友善完全是不帶感情的,這些東西似乎來自另一星球。
但這一切,卻不妨礙愛因斯坦對人類的關懷,這種關懷集中體現在他的和平主義思想和行動中。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他為倡導建設一個全世界統一的政府組織、有效控制核武器而不遺余力,堪稱一個“世界公民”。當他越來越看到國際化和控制核武器的努力行將失敗時,有人問他下一次世界大戰會是什么樣子,他回答道:“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用什么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肯定是用——石頭!”晚年,他更加熱情地扶持年輕人:“我認為上了年紀的人已經沒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他們應當站出來為受到更多約束的年輕人說話。”
“動”“靜”論:若想平衡,唯有運動
愛因斯坦既不單調無趣,亦非性格保守的學究,而是一個年富力強、魅力十足的人。他風流倜儻,卓爾不群,神采奕奕,風趣幽默,有一頭亂蓬蓬的頭發,打扮不拘小節,常常妙語連珠。他在1930年2月5日致小兒子愛德華的信中說:“生活就像騎自行車,要想保持平衡,就要不斷運動。”
動靜之間,愛因斯坦如一個輪,在不停歇的運動中保持了思想和生命的平衡。愛因斯坦的基本信條是,自由是創造性的源泉。愛因斯坦終生都保有孩童般的直覺和敬畏,從未對自然現象的魔力失去好奇,這使他的思想永遠處于探索探究的運動之中。與一般科學家從具體至抽象的思維路徑不同,他的科學成就很多源于他的天才思想,從“思想試驗”起步。“我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天賦,只是極為好奇罷了。”在愛因斯坦看來,好奇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創造了可以進行質疑的心靈,使得我們可以欣賞宇宙。“我們生來就面對著許多偉大的奧秘,在它們,我們永遠都是一些好奇的孩童。”1945年是愛因斯坦的多事之秋,政治紛爭頻仍,個人事務攪擾不斷,在妻兒離開他前往蘇黎世之后,愛因斯坦搬到了柏林市中心一個“單身漢的庇護所”,但這些恰恰突出了愛因斯坦的平衡哲學及巨大的專注能力。“我常常專注于工作,以致忘記吃午飯”,最終奔向廣義相對論。
在工作和興趣之間,愛因斯坦也保持著優雅的平衡。他是一個天才的小提琴演奏家:“莫扎特的音樂是如此純凈甜美,在我看來,它映襯出了宇宙的內在之美。”對愛因斯坦來說,音樂不僅僅是消遣,而且可以幫助思考。在個人事務陷入困境時,科學和藝術成了愛因斯坦的慰藉,“因為它使我從淚水的苦海中無怨無悔地升至寧靜之地”。科學和藝術所帶來的愉悅將他從痛苦的個人感情中解脫出來:“把人們引向藝術和科學的最強烈的動機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厭惡的粗俗和使人絕望的沉悶。”
在腹部主動脈罹患動脈瘤之后,面對手術與否,愛因斯坦平靜而超然:“人為地延長生命是索然無味的,我已經盡了我的責任,是該走的時候了。我會走得很體面的。”1955年4月18日,動脈瘤破裂,七十六歲的愛因斯坦離開了這個世界。按照他的遺囑,當天下午即火化,并將骨灰撒入附近的特拉華河,以免他最后的安息之地成為眾人膜拜的場所。他就像一個普通的人,哭鬧著來,安靜地去,靜靜地守護著這個星球,牽動著后人的思念,就像探測到引力波時引發的喧囂,人們自然而然想起他,向他致敬!
(摘自《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