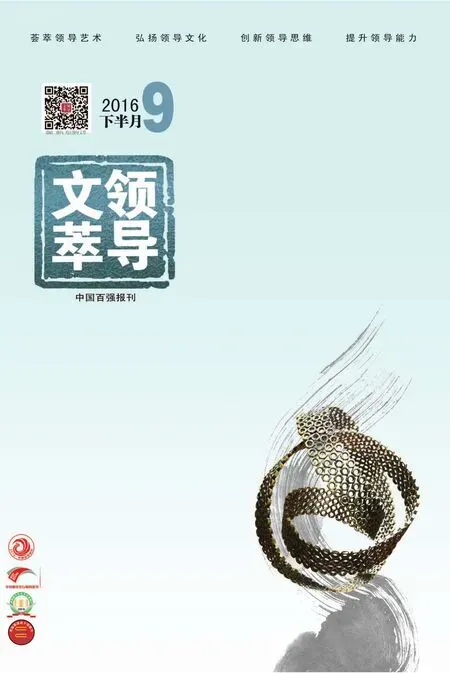以“新韜光養晦”應對新一輪“中國威脅論”
王文
“中國威脅論”,這一輪是“真”的
從1993年美國《外交》雜志第一次提“中國崛起”開始,關于“中國威脅”的國際言論就不絕于耳。然而,此前的形形色色“中國威脅論”或僅是學術假想,或僅是在部分外國利益集團中傳播,或是背后隱藏著不可告人的企圖。隨著事態變化,那些論調漸漸煙消云散。
比如,20世紀末,構陷“中國人將吃光全球糧食、耗盡全球能源”的理論假設,被中國現代化的發展現實所化解;21世紀初,渲染中國商品泛濫將沖擊全球市場的新聞報道,在物美價廉“中國制造”實際普惠各國民眾生活的事實面前變得失真;幾年前,誣告“中國將南海變成火藥桶”,在中國對南海諸國的外交誠意下化為烏有。
相比之下,這一輪的“中國威脅論”顯得真實很多,使西方國家真正感受到了中國的普遍威脅存在,使發達國家相當大部分人真切地開始恐懼中國了。這是我們必須要正視的國際事實。
第一,西方真正感受到中國經濟實力將不可阻擋地超越甚至替代發達國家的嚴重威脅。
2008年中國成功抵御全球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2011年中國制造業產值超過美國。更重要的是,中國抓住數字革命的技術浪潮,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方面呈現了對西方的全面“彎道超車”之勢。諸上事實使多數西方精英意識到,“500年來從未有過之大變局”正在發生。
第二,西方真正感受到中國外交對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強大號召力的嚴重威脅。
雖然發展中國家也曾在20世紀中葉運作過“不結盟運動”“萬隆亞非會議”等,但西方長期壟斷全球進程,只有西方才有實力召集全球各國政要聚首,設置并推進國際社會的各項發展議程。
然而,2016年主辦G20峰會,提出明顯比此前西方主導全球治理議程更受歡迎的“中國方案”;2017年中國連續主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全球政黨對話”,每次都有超過120個國家政要或高層代表參加,“中國方案”廣受好評。此時,西方意識到,“西方登高一呼、天下云集響應”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第三,西方真正感受到中國政治模式對后進國家、轉型國家、欠發達國家內生吸引力的嚴重威脅。
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多數精英驕傲地以為“歷史已終結”,以經濟私有化、政治選舉化、治理市場化的“華盛頓共識”打敗蘇聯模式,將成為未來歷史演化的唯一國家發展模式。但過去20多年,中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就,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開始著手“學習中國”甚至“復制中國”。
更重要的是,美歐國家在國內政治內耗上出現的“制度性的衰敗”,槍支、種族、移民、老齡化、階層固化等社會矛盾出現的“體制性的痼疾”,延續數百年的“西方優越論”走下神壇。于是,中國道路為世界提供了思想公共產品,成為全球各國發展的另一種選項。
西方欲借“中國威脅”再次團結起來
歐美國家智庫、媒體、政客近年來幾乎空前一致地對“中國威脅”發出了集體性的吶喊,代表著西方社會對“中國浪潮”的文化自覺與條件反射,更暴露了西方對中國經濟發展、外交感召、制度魅力等呈現“超越”苗頭感到無比恐慌后的反撲企圖。
這些“中國威脅論”多數體現在對中國引領全球治理與國力崛起的不滿與抹黑。比如,美國智庫炮制“銳實力”概念,假想孔子學院的中國文化入侵以及“不可告人的中國政治陰謀”;歐洲媒體攻擊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16+1”機制,虛構中國意在分裂歐洲的陰謀;詆毀中國對外推行的“雙贏”理念是等于“中國贏兩次”,等等。
還有不少“中國威脅論”則集中挑撥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比如,2017年底開始流行的“債權帝國主義”,意在勾勒中國通過債務強迫當地國出讓主權的負面形象;不少歐美議員則誣告“一帶一路”另造中國版勢力范圍,意在破壞國際自由秩序,等等。
更有一些“中國威脅論”企圖將中國定位為西方“假想敵”。比如,美國輿論不停地控訴中國竊取西方高科技與知識產權;英國媒體則通過春秋筆法,描述西方正在“神助攻”中國崛起;特朗普政府更是不惜與中國大打貿易戰,大造“聯歐抗華”貿易戰的對峙架勢。
事實上,西方的再團結并非不可能。2017年底美國開始推行“印太戰略”,提出新版基建與投資方案,試圖制衡“一帶一路”;法國、印度等40多國政要2018年3月正式組建國際太陽能聯盟,意在弱化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同月,日本主導與其他10國簽署被稱為“新版TPP”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進展協定》,平衡中國自貿區戰略。
種種跡象已表明,“中國威脅論”不再像過去僅是“論述”層面,而正在向“實踐”轉化。“中國威脅論”引起了一些西方集體行動,正在實實在在地威脅著中國發展。
謹防“斯奈德陷阱”
回想美國百年崛起之路,充滿著荊棘與坎坷,包括南北內戰、社會動蕩、種族沖突、鼠疫災荒、總統暗殺、洪災颶風、外部戰爭、核武訛詐、恐怖襲擊、體系設計、美元危機、金融風暴等,最終才“奇跡般”地造就了20世紀領銜世界的美國霸權。中國不走美式霸權之路,但民族復興的道路需要從美式崛起“百年磨難”中得出崛起韌勁的成功歷史經驗。
歷史上一度興起的西班牙、英國、法國、德國、蘇聯等陷入衰退,甚至國家解體的失敗歷史教訓,同樣也值得中國汲取。20多年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杰克·斯奈德在專著《帝國迷思:國內政治與對外擴張》中解釋蘇聯、日本、德國等在興衰中,國內輿論慫恿、國外戰略透支的歷史規律。他雖沒有論述中國,但中國須以史為鑒。
過去五年,中國崛起實力得到了全面檢驗,社會自信心不斷高漲,參與全球治理的積極性很強,效果也相當顯著。但從外部輿論集體警惕并出現“行動化”的趨勢看,中國崛起并非坦途,更非短途。
不妨采取“新韜光養晦”,夯實大國外交成果
在新時代,中國不妨采取“新韜光養晦”策略, 一方面繼續保持戰略自信,持續對內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對外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設想;另一方面也要學會用更長遠的眼光、更有恒心的戰略耐力,與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不友華勢力”斗智斗勇。
如果一些西方勢力以“拳擊”的方式對華進行貿易戰、金融戰、貨幣戰甚至軍事訛詐等,中國切不可心急。以當前的中國實力,與西方硬對抗,西方社會占不到大便宜,但中國多半也會“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但中國若運用古人智慧,以“太極”方式化整為零,讓對方的拳擊打空、打散,更無法通過“敵人化”中國而整合西方力量。這才是上上策。
在當前極其殘酷與復雜的國際環境下,中國須有更深的現代智慧與博弈城府,既要與西方現存力量強化合作,在中國投資走向廣泛發展中國家時引入歐美國家的第三方參與,繼續讓他們成為中國崛起的利益攸關方;也要與相關西方力量進行有效競爭,站在真正人類與全球利益的高度,創造新的國際標準與新型國際制度,實事求是,踏雪有痕,持之以恒,改革并優化目前以西方利益為中心的國際運行體系。
“新韜光養晦”絕不等于“新不作為”,而是要“巧作為”“深作為”“實作為”“長作為”,是要進行更精細化的對外作為。中國要深化落實過去五年來對國際社會的各項承諾,優化存量、擴大增量,通過企業合作、對外投資、貿易往來等方式做大中國發展的“崛起紅利”,塑造中國作為新型大國的崛起口碑,防止國內某些領域出現“改革空轉”“政策打滑”等跡象蔓延至國外。
(摘自《參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