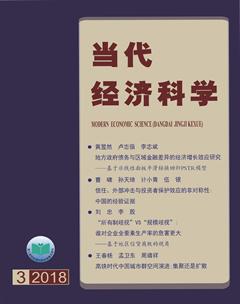高鐵時代中國城市群空間演進:集聚還是擴散
王春楊 孟衛(wèi)東 周靖祥
摘要:在闡釋高鐵建設(shè)影響城市群空間演進內(nèi)在機理的基礎(chǔ)上,基于2004—2015年中國五大城市群面板數(shù)據(jù),實證測度高鐵建設(shè)對城市群空間演進的異構(gòu)效應(yīng)。研究發(fā)現(xiàn):高鐵建設(shè)對城市體系空間格局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區(qū)域差異,在長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促進了人口與經(jīng)濟擴散,在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則促進了人口和經(jīng)濟集聚;高鐵促進了大城市的經(jīng)濟擴散,帶動了沿線中小城市的經(jīng)濟集聚。高鐵聯(lián)網(wǎng)已經(jīng)催生城市空間體系格局重構(gòu)的新動力,各地區(qū)應(yīng)因地制宜優(yōu)化城市群產(chǎn)業(yè)分工和城市功能布局,加快城際快速路網(wǎng)建設(shè)以彌合跨大區(qū)域空間尺度高鐵建設(shè)的聯(lián)動效應(yīng)。
關(guān)鍵詞:高速鐵路;城市群;空間結(jié)構(gòu);作用機理;依附指數(shù);社會網(wǎng)絡(luò)分析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1002-2848-2018(03)-0103-11
一、 引 言
世界發(fā)達(dá)國家的經(jīng)驗表明,高速鐵路的建設(shè)會對沿線城市乃至整個區(qū)域經(jīng)濟產(chǎn)生深刻影響。中國是世界上高速鐵路運營里程最長、在建規(guī)模最大的國家。截至2017年底,中國的高鐵營運里程已經(jīng)超過2.5萬公里,約占世界高速鐵路總里程的60%以上。高鐵正在成為越來越多中國人首選的出行方式,中國已經(jīng)進入“高鐵時代”。2016年,中國《中長期鐵路網(wǎng)規(guī)劃》中明確提出將建成“八橫八縱”高鐵干線,并加快城際鐵路建設(shè)以實現(xiàn)高鐵聯(lián)網(wǎng),將近鄰的大中城市納入1~4小時交通圈,城市群內(nèi)部則要構(gòu)建0.5~2小時交通圈。高鐵大規(guī)模的投資、建設(shè)和運營,不僅改變了中國的交通運輸結(jié)構(gòu),更將史無前例地重構(gòu)中國的城市與區(qū)域空間格局。
理論上講,高鐵會通過增強可達(dá)性來重塑區(qū)域人口和經(jīng)濟的空間結(jié)構(gòu);但因地理空間尺度的不同,可達(dá)性的意義也不盡相同。在國家和跨行政區(qū)層面,高鐵建設(shè)可以通過減少旅行時間,將邊緣地區(qū)拉近發(fā)達(dá)地區(qū),從而減少核心邊緣結(jié)構(gòu)的非均衡性,為區(qū)域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提供基礎(chǔ)設(shè)施機會[1-2]。高鐵建設(shè)可以帶來可達(dá)性在全局層面顯著的時空收斂,使各區(qū)域享受交通的便捷程度更趨均衡[3],特別是邊緣地區(qū)通達(dá)性的增加十分明顯[4]。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雖然有利于可達(dá)性的增加,但高鐵網(wǎng)絡(luò)發(fā)展對城市可達(dá)性的作用正在逐漸趕超空間區(qū)位的影響[5]。在城市群和大都市區(qū)層面,高鐵建設(shè)將帶來可達(dá)性變化和空間重構(gòu),不同級別交通網(wǎng)絡(luò)相互疊加改變原有城市群交通網(wǎng)絡(luò)特征。高鐵將擴展高鐵城市的等時圈范圍,形成非均衡的時間收斂,并擴大中心城市的腹地范圍[6-7]。高鐵建設(shè)能夠顯著提升通車城市的通達(dá)性,然而不連續(xù)的站點分布則會加劇高鐵城市和周圍非高鐵城市之間通達(dá)性的非均衡性,增加了空間極化的風(fēng)險。
城市群是世界各國尤其是發(fā)達(dá)國家城市化的主體空間形態(tài),其發(fā)展依托于發(fā)達(dá)的交通運輸體系和信息網(wǎng)絡(luò),而快速推進的高鐵網(wǎng)絡(luò)建設(shè)則進一步實現(xiàn)了城市群與城市群之間、城市群內(nèi)部各城市之間的“時空壓縮”,成為重塑城市群城市體系的重要因素[8-9]。高鐵能夠顯著促進沿線城市的經(jīng)濟集聚,有站點的城市比沒有站點的城市表現(xiàn)出更高的經(jīng)濟增長率。外圍地區(qū)特別是大城市之間的中等城市是高鐵開通后的最大受益者[10],專業(yè)會議、中等商業(yè)、咨詢服務(wù)業(yè)和旅游業(yè)等產(chǎn)業(yè)借助高鐵從大城市向周邊城市轉(zhuǎn)移[11]。高鐵提高了區(qū)域間經(jīng)濟增長的溢出效應(yīng)[12],從而有利于區(qū)域經(jīng)濟趨向均等化和平衡發(fā)展[13]。然而,也有證據(jù)表明,高鐵僅有利于所鏈接大城市的發(fā)展,犧牲外圍地區(qū)利益并擴大地區(qū)之間的不均衡。高鐵建設(shè)擴大了大型高鐵城市與非高鐵城市之間的工資差距以及高鐵城市與非高鐵城市之間的經(jīng)濟增長差距[14]。高鐵的溢出強度隨旅行時間的增加而衰減[15],高鐵網(wǎng)絡(luò)的擴張反而使得大都市圈集聚擴張的特征更為明顯[16],鐵路提速對沿線城市人口集聚的作用僅在長期顯著[17]。雖然政策和規(guī)劃在不同發(fā)展階段可以干預(yù)這種“天然影響”,但取決于區(qū)域內(nèi)完善的交通體系,從而能夠使高鐵的影響擴散到整個區(qū)域[18]。
可見,高鐵對于城市群空間結(jié)構(gòu)的影響并不確定。高鐵對城市群空間格局的影響,會因為高鐵開通的時間先后、被鏈接城市的類型以及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的發(fā)達(dá)程度等不同而存在顯著差異。對首位度較高的中心城市而言,高鐵的建設(shè)可能會繼續(xù)強化現(xiàn)有的城市等級,城市群將向著非均衡的趨勢發(fā)展;而對于規(guī)模等級較為均衡的城市群體系來說,高鐵可能會優(yōu)化區(qū)域內(nèi)的城市網(wǎng)絡(luò),促進城市間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19]。現(xiàn)階段,高鐵對可達(dá)性的改善是理論界研究的熱點,但這些研究并不能較為精準(zhǔn)地評估高鐵對城市和區(qū)域發(fā)展帶來的“利”與“弊”。事實上,面對大規(guī)模的高鐵建設(shè),政策制定者也面對一些反對的聲音,即高鐵建設(shè)是以一種高價的成本方式實現(xiàn)所謂的“收益”。中國地域遼闊,區(qū)域差異大,各地區(qū)城市化和城市群發(fā)展的道路和模式不盡相同。同時,與其他擁有高鐵的國家不同,我國是發(fā)展中國家,并且正處于高速的城市化時期,這使得高速鐵路對中國城市與區(qū)域經(jīng)濟的影響有可能區(qū)別于其他國家。因此,在高鐵快速聯(lián)網(wǎng)背景下,揭示城市群空間格局的演進規(guī)律,有助于更為全面地評估高鐵建設(shè)的經(jīng)濟空間效應(yīng),逐步完善城市群戰(zhàn)略制訂。
出于以上考慮,我們的主要工作將基于新經(jīng)濟地理學(xué)研究框架,將“高鐵建設(shè)”納入城市群空間結(jié)構(gòu)演進的分析中,實證檢驗高鐵建設(shè)對我國城市群空間格局演進的影響。接下來的內(nèi)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論基礎(chǔ)和計量模型的構(gòu)建,在闡釋高鐵建設(shè)影響城市群空間演進內(nèi)在機理的基礎(chǔ)上,構(gòu)建納入“高鐵建設(shè)效應(yīng)”的計量模型;第三部分是實證結(jié)果的分析和討論,基于中國五大城市群的面板數(shù)據(jù),實證檢驗高鐵建設(shè)對不同城市群的影響差異;第四部分是中國高鐵網(wǎng)絡(luò)下城市群聯(lián)動發(fā)展的空間特征分析,把城市群放置在全國中心城市聯(lián)動的背景下,對中國城市群現(xiàn)狀與未來發(fā)展趨勢進行分析;最后是文章的結(jié)論和政策建議。
二、 理論基礎(chǔ)、方法選擇與數(shù)據(jù)說明
(一)理論基礎(chǔ)
新經(jīng)濟地理學(xué)理論認(rèn)為,交通運輸成本的下降將通過“價格指數(shù)效應(yīng)”和“本地市場效應(yīng)”等傳導(dǎo)機制引發(fā)地區(qū)間工資、要素價格差異,進而影響地區(qū)間的要素轉(zhuǎn)移和經(jīng)濟增長差異,城市體系的空間格局將呈現(xiàn)收斂或者發(fā)散。在高鐵出行條件下,勞動力和生產(chǎn)要素的區(qū)位選擇,可以看作是在運輸成本(包括時間成本)與其在新的區(qū)位下所獲得的真實收益之間進行的比較和權(quán)衡。但是這種影響并不是自動或普遍的,而是具有明顯的區(qū)域異質(zhì)性[20-21]。就具有相對地理邊界的城市群來說,一方面,高速鐵路建設(shè)縮短了城市群內(nèi)部各城市之間的旅行時間,特別是提高了沿線城市的可達(dá)性,從而引發(fā)生產(chǎn)要素在不同城市間的重新配置;另一方面,高鐵建設(shè)縮短了各城市群之間的時空距離,即借助于全國跨大空間尺度的高鐵網(wǎng)絡(luò),各城市群市場范圍得以突破原有的地理邊界,生產(chǎn)要素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內(nèi)流動和配置。從這個意義來說,高鐵建設(shè)正是通過進一步壓縮城市群內(nèi)部和外部的時空距離,從內(nèi)外兩個空間維度上加速了全國城市體系的一體化進程。
高鐵促進沿線人口與經(jīng)濟集聚的一般機制可以描述為:首先,高鐵建成后會降低交通成本,這會給企業(yè)帶來生產(chǎn)的增長效應(yīng),從而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同時,增加的高鐵會給居民生活和就業(yè)帶來便利,從而增加地區(qū)勞動力供給。如果勞動力需求大于供給就會導(dǎo)致地區(qū)工資上升,從而引發(fā)勞動力流入,產(chǎn)生勞動力就業(yè)引致的區(qū)域分工和人口集聚效應(yīng)。其次,高鐵建設(shè)帶來地區(qū)區(qū)位條件和市場可達(dá)性的變化,會促使企業(yè)或家庭搬遷,以便獲得更優(yōu)的生產(chǎn)或生活環(huán)境,從而產(chǎn)生消費引致的人口集聚效應(yīng)。無論是哪一個過程一旦產(chǎn)生便會自我強化,形成“循環(huán)累積”和“路徑依賴”。一方面,人口和生產(chǎn)集聚,會擴大本地市場規(guī)模,強化“本地市場效應(yīng)”;另一方面,產(chǎn)品種類的增加會進一步降低本地的價格指數(shù),強化“價格指數(shù)效應(yīng)”,進而提高勞動力“真實工資”。無論是哪一種機制,高鐵建設(shè)都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地區(qū)的產(chǎn)業(yè)集聚和經(jīng)濟增長。
然而,高鐵對城市群空間結(jié)構(gòu)的影響還取決于城市群的一體化程度。集聚租金本身具有倒“U”型的變化特征,即隨著要素集聚的加強,不可移動要素如土地價格和擁擠成本將會抵消集聚經(jīng)濟效果,意味著政策的邊際變動不一定導(dǎo)致經(jīng)濟產(chǎn)生相同后果。正是這種差異,使得沿線城市在要素的流入或流出方面會呈現(xiàn)不同的空間特征。當(dāng)對外開放程度較低時,經(jīng)濟傾向于向某一地區(qū)集聚,但隨著開放程度的增加,集聚和分散都將成為穩(wěn)定的均衡[22]。城市群內(nèi)的一體化進程不僅會減弱向心力,同時也會減弱離心力,要素的轉(zhuǎn)移則取決于向心力和離心力的力量對比[23]。同時,城市群內(nèi)部的經(jīng)濟分布,還取決于城市群周邊地區(qū)的發(fā)達(dá)程度,如果臨近經(jīng)濟發(fā)達(dá)地區(qū),經(jīng)濟傾向于集聚在通達(dá)性較好的城市,反之則會向邊緣遷移以規(guī)避市場競爭[22]。因此,對于城市群的空間結(jié)構(gòu)演化而言,人口與經(jīng)濟是向沿線城市集聚,還是會向周圍地區(qū)擴散,既取決于通達(dá)性提高對沿線城市向心力的提升,也取決于城市群的發(fā)達(dá)程度。對于一體化程度較低的城市群,高鐵的建設(shè)帶來的集聚效應(yīng)會大于擴散效應(yīng),這將促進城市群繼續(xù)向著非均衡的態(tài)勢演進;對于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城市群,高鐵建設(shè)帶來的擴散效應(yīng)可能會大于集聚效應(yīng),借助于產(chǎn)業(yè)分工和轉(zhuǎn)移,市場規(guī)模擴大和成本節(jié)約的紅利將擴散到整個城市群中。
(二)方法選擇
1.城市群空間演化特征的測度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科學(xué)評價高鐵建設(shè)對城市群空間格局的影響,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如何把高鐵的影響與其他因素的影響分離開來。如果把高鐵建設(shè)看作是在高鐵城市和非高鐵城市間所做的一項政策實驗,那么檢驗高鐵建設(shè)的影響即是檢驗這種政策沖擊所帶來的影響。高鐵開通后,其空間影響主要來自兩部分:一部分是隨時間自然增長或經(jīng)濟形勢變化而形成的所謂的“時間效應(yīng)”部分,另一部分是隨高鐵建設(shè)而引起的所謂“政策處理效應(yīng)”部分[14]。本研究把“高鐵城市”作為處理組,“非高鐵城市”作為控制組,并且假設(shè)兩組城市在高鐵建設(shè)之前具有相同的“時間效應(yīng)”趨勢,那么高鐵建成通車后兩組城市的差異變化就是“高鐵建設(shè)效應(yīng)”。參考已有研究,本文設(shè)計的高鐵效應(yīng)評價模型如下:
其中,Yit為所要考察的城市i在時間t的經(jīng)濟特征;Hit為城市i在時間t是否開通高鐵的虛擬變量,高鐵開通當(dāng)年和通車之后的年份取值為1,開通之前取值為0;其系數(shù)β1即是高鐵開通對處理組和控制組的影響差異。Xit是影響城市增長變動的一組控制變量。μi為城市的固定效應(yīng),反映兩組樣本城市之間不隨時間變動的空間差異;λt為時間趨勢效應(yīng),反映若沒有政策變動,兩組樣本隨時間變動的趨勢;εit為隨機干擾項。為進一步檢驗高鐵開通對城市群空間格局的影響隨時間演進的趨勢,本文在上述計量模型的基礎(chǔ)上引入時間效應(yīng)虛擬變量,定義HT為高鐵開通第T年的虛擬變量。高鐵開通的第T年HT的取值為1,其他年份取0。如果HT的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正且隨時間呈現(xiàn)不斷增加的變動趨勢,則說明高鐵開通的時間越長,其帶來的城市增長效應(yīng)越明顯,或者說越早開通高鐵的城市,其獲得的時間累積效應(yīng)越明顯,反之則不然。
2.城市群空間聯(lián)系特征的測度
在以往的研究中,城市間開行的鐵路客運車次數(shù)量在一定程度能夠反映出城市間聯(lián)系的緊密程度。本文構(gòu)建了城市間鐵路客運的依附指數(shù),用以刻畫城市之間的聯(lián)系強度和方向,具體形式設(shè)定為:
考察城市聯(lián)系影響因素的計量模型設(shè)定基于經(jīng)典的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城市間的相互作用不僅取決于起點城市和終點城市的經(jīng)濟特征變量,還取決于反映空間屬性的特征變量如城市間的地理距離等,在此基礎(chǔ)上,設(shè)定的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Dep為依附指數(shù),pop為2016年城市常住人口數(shù);dis為城市a與b之間的地理距離,以兩地間最短鐵路距離來衡量;dis2為地理距離的平方項,用以刻畫城市依附關(guān)系隨地理距離的變動特征;h為高鐵是否開通的虛擬變量,t為高鐵開通的時間;lon和lat分別為起點城市的經(jīng)度和緯度,具體以該城市政府所在地的經(jīng)度和緯度來表示;hu為2007年城市戶籍人口數(shù),由于在中心城市樣本中沒有城市在2007年之前開通高鐵,因此該變量的回歸系數(shù)能夠側(cè)面反映城市間依附關(guān)系受高鐵開通影響的大小。
(三)數(shù)據(jù)說明
樣本選擇。中國在2004年審議通過《中長期鐵路網(wǎng)規(guī)劃》,提出建設(shè)“四橫四縱”客運專線以及環(huán)渤海、長三角和珠三角城際客運系統(tǒng),自此中國進入規(guī)模空前的高鐵建設(shè)時代。因此,本文以2004年作為評估高鐵效應(yīng)的基期,以2015年為評估高鐵效應(yīng)的終期。通過比較高鐵開通時間、城市群規(guī)模和全國影響力等方面,最終選取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五個城市群進行比較分析。截至2015年底,五大城市群共通車高鐵線路(包含城際鐵路)18條,納入分析的城市樣本為129個。城市樣本的選擇原則首先納入國家相應(yīng)城市群發(fā)展規(guī)劃中包括的城市,在城市樣本較少的地區(qū),如京津冀地區(qū),則將周邊城市加入分析樣本,地理空間上在300公里的半徑左右。
被解釋變量方面。本文分別從城市人口規(guī)模和城市經(jīng)濟規(guī)模兩個方面刻畫高鐵對城市群空間格局變化的影響,具體選擇城市市轄區(qū)人口的對數(shù)(lnpop)和城市GDP的對數(shù)(lngdp)來衡量。參考相關(guān)研究,最終選擇的控制變量包括城市的市場潛力、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特征、工資水平、城市開放程度、基礎(chǔ)設(shè)施水平和城市教育發(fā)展水平,相應(yīng)采用城市人均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的對數(shù)(lnpgdp)、第三產(chǎn)業(yè)比重的對數(shù)(lnser)、職工平均工資的對數(shù)(lnsala)、實際利用外資數(shù)的對數(shù)(lnfdi)、城市人均道路面積的對數(shù)(lnroad)和城市高等學(xué)校在校教師數(shù)的對數(shù)(lnedu)來衡量。基礎(chǔ)樣本數(shù)據(jù)來自2005—2016年《中國城市統(tǒng)計年鑒》;城市實際客運車次數(shù)據(jù)來自旅行服務(wù)網(wǎng)站“去哪兒網(wǎng)”和中國鐵路客戶服務(wù)網(wǎng)站“12306網(wǎng)站”。
三、 實證結(jié)果及解釋
(一)高鐵建設(shè)的人口集聚與擴散效應(yīng)
如表1所示,從全部城市樣本的回歸結(jié)果來看,變量H的回歸系數(shù)為負(fù)但不具有顯著性,因此需要對各城市群分別考察。首先,高鐵建設(shè)對城市人口規(guī)模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地區(qū)差異,在長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表現(xiàn)為顯著的擴散效應(yīng),在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表現(xiàn)為顯著的集聚效應(yīng)。這一結(jié)果說明在長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人口有向高鐵城市集聚的城市群演化傾向,呈現(xiàn)出顯著的人口集聚效應(yīng)。高鐵引發(fā)的城市人口增長,增加了原有城市群在人口分布方面的非均衡性。此實證結(jié)果支持高鐵通過提高高鐵城市的可達(dá)性、改變城市集聚租金,進而引發(fā)人口就業(yè)和生活向高鐵城市集聚的邏輯推理;而那些沒有高鐵通過的城市,由于可達(dá)性和集聚租金的相對變化,人口集聚則呈現(xiàn)比較劣勢,甚至?xí)霈F(xiàn)人口和就業(yè)流出。此分析結(jié)論與董艷梅和朱英明的研究結(jié)論相一致[14]。對于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變量H的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負(fù),說明在這兩個城市群,高鐵建設(shè)的人口擴散效應(yīng)十分明顯,人口有從高鐵城市向非高鐵城市擴散的城市群演化傾向,這有利于高鐵城市與非高鐵城市之間人口分布的空間結(jié)構(gòu)優(yōu)化與協(xié)調(diào)發(fā)展。隨著城市群內(nèi)部交通環(huán)境的持續(xù)改善,以及高鐵城市生產(chǎn)生活成本的增加所帶來的集聚租金下降,高鐵城市在人口就業(yè)和生活方面呈現(xiàn)比較劣勢,城市群內(nèi)高鐵城市的擴散效應(yīng)大于集聚效應(yīng)。長三角是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則是幾乎全部城市處于同一個省級行政區(qū)內(nèi)部的城市群,兩個城市群的城市密度大,城市之間的空間距離較近,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十分發(fā)達(dá),在高鐵開通之前就已經(jīng)形成較為便捷的城際交通網(wǎng)絡(luò),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高鐵開通對沿線城市的擴散作用十分明顯。在京津冀城市群,高鐵建設(shè)對城市人口規(guī)模的影響并不顯著,北京和天津兩大直轄市強大的吸附能力可能弱化了高鐵沿線城市經(jīng)濟集聚作用的發(fā)揮。
(二)高鐵建設(shè)的經(jīng)濟集聚與擴散效應(yīng)
如表2所示,從全樣本來看,變量H的回歸系數(shù)為負(fù)但仍不具有統(tǒng)計意義上的顯著性,仍需要對不同的城市群進行分別考察。首先,高鐵建設(shè)對城市經(jīng)濟規(guī)模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地區(qū)差異,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表現(xiàn)為顯著的擴散效應(yīng),在京津冀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則表現(xiàn)為顯著的集聚效應(yīng)。此結(jié)果說明了高鐵建設(shè)顯著改變了高鐵城市的經(jīng)濟規(guī)模。在京津冀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高鐵建設(shè)促進經(jīng)濟向沿線城市集聚,增加了原有城市群各個城市發(fā)展的經(jīng)濟規(guī)模差異。此結(jié)果支持高鐵建設(shè)通過改善通達(dá)性,進而引發(fā)需求增加和就業(yè)增長效應(yīng),通過價格指數(shù)效應(yīng)和本地市場效應(yīng)的共同作用,最終帶來城市的經(jīng)濟增長的邏輯推理。除了京津冀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分別位于中國的中部和西部地區(qū),高鐵建設(shè)對中西部地區(qū)沿線城市的經(jīng)濟集聚效應(yīng)更為明顯,此結(jié)論與李紅昌等[13]的研究結(jié)論相一致。從變量H的回歸系數(shù)的大小來看,高鐵建設(shè)對城市經(jīng)濟規(guī)模的影響要顯著的大于對人口規(guī)模的影響。同高鐵對城市人口規(guī)模影響一致,高鐵對城市經(jīng)濟規(guī)模的影響在長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表現(xiàn)為顯著的負(fù)效應(yīng),即表現(xiàn)為高鐵城市對非高鐵城市的擴散效應(yīng)。對于這兩個城市群來說,接入全國的高鐵網(wǎng)絡(luò),促進了經(jīng)濟活動的擴散,城市群經(jīng)濟向著更為均衡的方向發(fā)展。高鐵建設(shè)所帶來的通達(dá)性的提升和市場規(guī)模的擴大使得整個城市群受益,這同樣依賴于兩個地區(qū)內(nèi)部發(fā)達(dá)的交通運輸網(wǎng)絡(luò),以及相對完善的城市功能分工體系。不同的是,在長三角城市群,高鐵建設(shè)對城市經(jīng)濟擴散的影響要小于對人口擴散的影響,而在珠三角地區(qū),高鐵建設(shè)對城市經(jīng)濟擴散的影響要大于對人口擴散的影響,并且長三角人口擴散效應(yīng)大于珠三角,而經(jīng)濟擴散效應(yīng)則小于珠三角城市群,反映了兩個城市群在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城市規(guī)模分布、交通網(wǎng)絡(luò)建設(shè)方面的差異。
此外,本文還以城市建成區(qū)面積為被解釋變量,考察了高鐵建設(shè)對城市空間擴張的影響。結(jié)果發(fā)現(xiàn),高鐵建設(shè)對城市空間擴張的影響在京津冀、長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具有顯著的正效應(yīng)。在這些城市群,高鐵建設(shè)擴大了沿線城市的城區(qū)規(guī)模。并且,H的回歸系數(shù)要大于人口增長模型的回歸系數(shù),說明高鐵建設(shè)的城市土地擴張效應(yīng)更為顯著。一般來說,高鐵通過城市引發(fā)的高鐵站點建設(shè)可以被視為一項“外部沖擊”,除了經(jīng)濟活動自身的前后向關(guān)聯(lián)所引發(fā)的城市集聚增加帶來對土地利用的需求,城市政府則往往會抓住高鐵建設(shè)的大好時機,在城市周邊新建的高鐵站點周圍加快高鐵新城建設(shè)和房地產(chǎn)開發(fā),呈現(xiàn)“高鐵造城”的城區(qū)擴張景象。
(三)高鐵建設(shè)影響的時間趨勢效應(yīng)
高鐵影響隨時間的演進趨勢方面,綜合表1和表2的計量結(jié)果顯示,HT的回歸系數(shù)在大部分模型中均顯著為正,但存在顯著的區(qū)域差異。首先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內(nèi),高鐵建設(shè)對人口和經(jīng)濟的擴散效應(yīng)隨時間則呈現(xiàn)顯著的增加趨勢。人口方面,高鐵開通第1年對長三角城市人口擴散的影響系數(shù)為-0.065,影響系數(shù)隨時間不斷增加,到高鐵開通的第6年,影響系數(shù)達(dá)到-0.252,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高鐵的人口擴散效應(yīng)在珠三角地區(qū)僅在高鐵建設(shè)開通的前4年表現(xiàn)出顯著的增加趨勢,到第5年之后則不明顯。經(jīng)濟方面,無論是在長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高鐵開通對經(jīng)濟擴散的影響,都呈現(xiàn)隨時間逐漸增加的變化趨勢。即隨著高鐵開通時間的增加,高鐵的人口和經(jīng)濟擴散效應(yīng)更加顯著,說明高鐵建設(shè)對城市群空間格局的影響存在顯著的“時間累積效應(yīng)”。在京津冀城市群,高鐵開通對城市人口規(guī)模和經(jīng)濟規(guī)模的影響顯著發(fā)生在高鐵開通的第4年和第5年左右,而其他年份的影響則不顯著,且在某些年份出現(xiàn)人口與經(jīng)濟的擴散效應(yīng)。在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高鐵的人口集聚效應(yīng)和經(jīng)濟集聚效應(yīng)也呈現(xiàn)不同的隨時間演變特征:人口方面,在高鐵開通的第3到5年,高鐵的人口集聚效應(yīng)較為明顯,之后則不具有顯著性;而在經(jīng)濟方面,高鐵開通對城市經(jīng)濟集聚的影響則隨時間呈現(xiàn)顯著的增加態(tài)勢。也說明那些越早開通高鐵的城市,越能夠優(yōu)先捕捉發(fā)展機會,從高鐵建設(shè)的增長效應(yīng)中獲益。總體上,高鐵建設(shè)的時間效應(yīng)更多的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集聚或者擴散方面,而對于人口分布的影響則沒有表現(xiàn)出隨時間特定的演進趨勢,除了在長三角城市群之外,高鐵對城市群人口分布的顯著影響僅發(fā)生在高鐵開通的前幾年。
(四)高鐵建設(shè)對不同規(guī)模城市的影響
在這些開通高鐵的城市中,既包含了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也包含了其他各種規(guī)模類型的城市,這些不同類型的城市在高鐵開通后,其帶來的“擴散—回流”效應(yīng)可能也存在差異。
表3的回歸結(jié)果顯示,高鐵對不同規(guī)模的城市確實存在不同的影響。首先,對大城市來說,隨著高鐵的建設(shè)開通,在高鐵開通的第6年和第7年則出現(xiàn)顯著性,表現(xiàn)為明顯的擴散效應(yīng)。對中等城市來說,擴散效應(yīng)出現(xiàn)較早,在第2年表現(xiàn)出顯著的擴散效應(yīng)。對小城市來說,高鐵對城市人口的影響則表現(xiàn)為顯著的集聚效應(yīng),從時間上來說,集聚效應(yīng)在高鐵開通的前幾年表現(xiàn)出顯著性。其次,高鐵對不同規(guī)模城市經(jīng)濟的影響表現(xiàn)出更為明顯的特征。高鐵對大城市的影響表現(xiàn)為顯著的擴散效應(yīng),對小城市則依舊表現(xiàn)為顯著的集聚效應(yīng)。該結(jié)果說明,高鐵建設(shè)顯著地促進了大城市的經(jīng)濟擴散,有利于城市群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在這個過程中,小城市的獲益最大,對小城市經(jīng)濟集聚的影響最為顯著。從時間趨勢上來說,無論是大城市的擴散效應(yīng),還是小城市的集聚效應(yīng),都是在高鐵建成開通的前幾年表現(xiàn)最為明顯,隨后則不顯著。結(jié)合前面的實證結(jié)果,可以認(rèn)為,在我國東部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大城市的規(guī)模較大并且數(shù)量較多,在高鐵的沖擊下,經(jīng)濟由這些大城市借由發(fā)達(dá)的交通運輸網(wǎng)絡(luò)擴散到區(qū)域內(nèi)中小城市的趨勢明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城市群的均衡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在中西部地區(qū)的城市群內(nèi),如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內(nèi),大城市的規(guī)模小并且數(shù)量較少,經(jīng)濟擴散的特征不明顯,僅帶動了高鐵沿線中小城市的發(fā)展,城市群的經(jīng)濟有向高鐵沿線城市集聚的發(fā)展傾向。
四、 高鐵網(wǎng)絡(luò)下中國城市群聯(lián)動特征
前述研究結(jié)果表明了高鐵建設(shè)對城市群空間演進帶來的顯著影響,深層含義是將各個城市群發(fā)展置于全國聯(lián)動的開放格局之中。借助于全國的高鐵網(wǎng)絡(luò),各城市群中心城市的腹地范圍也因此快速向外拉伸,城市群發(fā)展已突破原有的地理邊界,其空間形態(tài)不斷被重塑。從局部到全局,從中心到外圍,分析高鐵聯(lián)網(wǎng)下中心城市的聯(lián)動特征,可以進一步刻畫中國城市群的未來發(fā)展方向和空間格局。
(一)高鐵聯(lián)網(wǎng)下城市群的空間聯(lián)系特征
高鐵運營,使得不同規(guī)模大小和行政層級的城市從競爭走向合作,謀求協(xié)同和聯(lián)動發(fā)展。聯(lián)通東西南北中的高鐵網(wǎng)絡(luò),將會有助于增強內(nèi)與外、東與西、沿海與內(nèi)地、東北邊境與西南邊疆等多層次的時空聯(lián)系緊密程度。因此,從全國層面分析高鐵聯(lián)網(wǎng)對城市群聯(lián)動格局的影響,可以側(cè)面反映高鐵聯(lián)網(wǎng)對城市群整體發(fā)展的影響。由于每一個城市群都依托于幾個強大的中心城市,所以本文基于全國36個中心城市(31個省會級城市、5個計劃單列市)的鐵路客運數(shù)據(jù),通過測算城市間依附指數(shù),側(cè)面刻畫城市群結(jié)構(gòu)特征和空間范圍。城市間依附指數(shù)的測算結(jié)果和空間分布體系格局見圖1。
通過測算結(jié)果可以發(fā)現(xiàn),全國中心城市之間鐵路客運聯(lián)系存在顯著差異,其空間分布呈現(xiàn)沿京滬、京廣、京哈、滬昆、隴海、滬漢蓉、滬深等“四橫四縱”主要客運專線分布。高鐵不僅串聯(lián)起各大城市群,同時城市群內(nèi)部的主要鐵路客運聯(lián)系也依托這些線路。總體上,全國鐵路客運聯(lián)系呈現(xiàn)南方強北方弱、東部強西部弱,而且南北的聯(lián)系要明顯強于東西走向的空間聯(lián)系特征。借助于社會網(wǎng)絡(luò)分析方法,可以對中心城市空間聯(lián)系和網(wǎng)絡(luò)特征進行刻畫,主要包括點度中心性和中間中心性兩個指標(biāo),前者可以測度城市在網(wǎng)絡(luò)中的“影響范圍”,后者則可以測度城市在網(wǎng)絡(luò)中的“資源控制”程度,測算結(jié)果見圖1和圖2。在圖1中,北京、天津、沈陽、鄭州、武漢、長沙、廣州、上海和南京是客運鐵路網(wǎng)絡(luò)的關(guān)鍵節(jié)點,這些城市節(jié)點與其他城市的直接聯(lián)系數(shù)目最多,空間聯(lián)系更為緊密,是整個鐵路客運網(wǎng)絡(luò)中的運輸樞紐。在圖2中,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鄭州和長沙是鐵路客運網(wǎng)絡(luò)中起決定作用的中間節(jié)點城市,處于樞紐地位,依托于高鐵聯(lián)系將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和長江中游城市群等多個國家級城市群串聯(lián)起來;特別是貫穿北京、鄭州、武漢和廣州的京廣鐵路運輸通道,是中國最為重要的中介軸帶。
當(dāng)給定不同的依附指數(shù)門檻值,可以刻畫不同城市群之間的聯(lián)動關(guān)系和空間格局。圖3分別給出了依附指數(shù)大于100、大于200、大于300和大于400的城市群聯(lián)動關(guān)系。發(fā)現(xiàn)當(dāng)依附指數(shù)大于100時,中國的主要城市群都被連接起來,特別是依賴于“哈爾濱—北京—廣州”的中國鐵路客運中軸線以及“北京—上海”軸線,各城市群中心城市的腹地范圍得到顯著擴張和交叉。當(dāng)依附指數(shù)大于400時,聯(lián)系只存在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城市間依附關(guān)系最為密切,也即在此三個“三角地區(qū)”,城市的吸附能力最強,環(huán)繞北京、上海和廣州的三大中心城市的全球性大都市圈形成的可能性更大。
(二)高鐵網(wǎng)絡(luò)下城市群聯(lián)動的機制
表4的計量結(jié)果顯示,首先,城市間依附關(guān)系與城市人口規(guī)模的分布格局相一致,即城市間聯(lián)動關(guān)系顯著的受起點城市和終點城市人口規(guī)模的影響,呈現(xiàn)出“強強聯(lián)動”的空間發(fā)展格局。其次,地理距離顯著影響城市之間的依附關(guān)系,但二者呈現(xiàn)非線性的變動關(guān)系。地理距離dis對城市依附指數(shù)的影響顯著為負(fù),而地理距離的平方項dis2對城市依附指數(shù)的影響則顯著為正。圖4表明了城市依附關(guān)系與地理距離之間更為直接的變動關(guān)系,城市間鐵路客運的依附關(guān)系隨地理距離的增加呈現(xiàn)出先減小后增大的變動趨勢。同時,用同樣方法計算的城市航空依附指數(shù)隨地理距離的增加則呈現(xiàn)先增大后減小的變動趨勢。從兩種交通方式的影響半徑來看,鐵路聯(lián)系在2500公里左右,航空聯(lián)系則是在3500公里左右(圖5)。由此看來,鐵路尤其是高鐵會在1500公里之內(nèi)擠占航空,與航空的競爭較為激烈。空間特征方面,lon的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正,說明東部城市的對外聯(lián)系相比與西部城市更為緊密;lat的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負(fù),說明南部城市的對外聯(lián)系較北部城市更為緊密,因此城市聯(lián)動格局在全國呈現(xiàn)東強西弱、南強北弱的分布特征。h的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正,說明開通高鐵的城市與其他中心城市的聯(lián)系更為緊密;t的回歸系數(shù)顯著為負(fù),說明越早開通高鐵的城市與其他中心城市的依附關(guān)系越強。hua和hub的回歸系數(shù)均不顯著,說明城市間依附關(guān)系與高鐵開通之前的人口空間分布并不一致,反過來也說明,高鐵對中心城市人口增長具有顯著影響,高鐵已然成為重塑區(qū)域空間結(jié)構(gòu)的重要變量。
五、 結(jié)語
城市群是城鎮(zhèn)化的主體空間形態(tài),在區(qū)域經(jīng)濟發(fā)展中起著重要作用。在當(dāng)前中國經(jīng)濟增速放緩、有效供給不足的背景下,高鐵成為拓展區(qū)域發(fā)展空間的全新舉措。高鐵建設(shè)提高了城市之間的通達(dá)性,并由此改變?nèi)说膮^(qū)位選擇和要素流動方向,區(qū)域空間結(jié)構(gòu)得以加速重組。高鐵建設(shè)將如何影響城市群的空間格局,這是本文關(guān)注的中心問題。文章構(gòu)建了高鐵建設(shè)影響城市群空間格局的分析框架,并進行實證檢驗。本文的主要結(jié)論包括:高鐵建設(shè)對城市體系空間格局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區(qū)域差異,在長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促進了人口與經(jīng)濟擴散,在長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則促進了人口和經(jīng)濟集聚。高鐵開通對城市體系格局的影響存在明顯的時間趨勢特征,除了在長三角地區(qū)和珠三角地區(qū)呈現(xiàn)顯著的時間累積效應(yīng),整體上高鐵對城市群體系格局的影響在高鐵開通的前幾年更為明顯。總體上,本文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高鐵聯(lián)網(wǎng)已經(jīng)催生城市空間體系格局重構(gòu)的新動力,在全國高鐵聯(lián)網(wǎng)的背景下,中心城市的腹地得以快速擴張,城市群協(xié)同聯(lián)動發(fā)展趨勢明顯。
從本文的研究結(jié)論可以得到以下啟示:第一,城市群的協(xié)同聯(lián)動依賴于快速便捷的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網(wǎng)絡(luò),而當(dāng)前快速推進的高鐵建設(shè)則加速了城市群的經(jīng)濟重組,或?qū)⒃僭斐鞘腥旱目臻g格局。但是人口、要素的流向和區(qū)位選擇具有不確定性,要審慎揣測高鐵通車的時空效應(yīng),杜絕借助高鐵建設(shè)盲目擴張基礎(chǔ)設(shè)施。第二,高鐵建設(shè)明顯改善了高鐵城市的區(qū)位條件,城市群應(yīng)以高鐵城市為基點,整合區(qū)域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形成以高鐵為紐帶的城市產(chǎn)業(yè)分布格局;通過整合高鐵城市與非高鐵城市、高鐵城市之間的產(chǎn)業(yè)分工和空間布局,促進城市群經(jīng)濟轉(zhuǎn)型升級。第三,高鐵建設(shè)帶來了發(fā)展契機,但如何增強吸附能力以及與其他城市的聯(lián)動發(fā)展,是高鐵城市能夠借助高鐵實現(xiàn)經(jīng)濟增長的關(guān)鍵。高鐵城市應(yīng)因地制宜,挖掘自身比較優(yōu)勢和發(fā)展特色,強化與其他高鐵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分工與合作,以避免“過站效應(yīng)”和空間極化的風(fēng)險。最后,高鐵對部分城市群的影響在現(xiàn)階段表現(xiàn)為集聚高于分散、極化強于擴散的演化特征,但并非這種格局會持續(xù)不變。隨著城市群高鐵和城際鐵路的不斷聯(lián)網(wǎng),城市群各城市的通達(dá)性將不斷趨于均衡,經(jīng)濟重組或?qū)⑾蚓獾姆较蜓莼6?dāng)前,非高鐵城市應(yīng)主動接駁高鐵城市,以城際鐵路網(wǎng)和快速交通體系來彌合跨越大區(qū)域尺度空間的高鐵建設(shè)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參考文獻(xiàn):
[1] Gutiérrez J. Location, economic potential and daily accessibility: an analysis of the accessibility impact of the highspeed line MadridBarcelonaFrench border [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01, 9(4): 229-242.
[2] Gutiérrez J, González R, Gómez G. The European highspeed train network: Predicted effects on accessibility patterns [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1996, 4(4): 227-238.
[3] 馬穎憶, 陸玉麒, 柯文前, 陳博文. 泛亞高鐵建設(shè)對中國西南邊疆地區(qū)與中南半島空間聯(lián)系的影響 [J]. 地理研究, 2015, 34(5): 825-837.
[4] 馮長春, 豐學(xué)兵, 劉思君. 高速鐵路對中國省際可達(dá)性的影響 [J]. 地理科學(xué)進展, 2013, 32(8): 1187-1194.
[5] 鐘業(yè)喜, 黃潔, 文玉釗. 高鐵對中國城市可達(dá)性格局的影響分析 [J]. 地理科學(xué), 2015, 35(4): 387-395.
[6] 蔣海兵, 徐建剛, 祁毅. 京滬高鐵對區(qū)域中心城市陸路可達(dá)性影響 [J]. 地理學(xué)報, 2010, 65(10): 1287-1298.
[7] 汪德根, 牛玉, 陳田, 陸林, 唐承財. 高鐵驅(qū)動下大尺度區(qū)域都市圈旅游空間結(jié)構(gòu)優(yōu)化——以京滬高鐵為例 [J]. 資源科學(xué), 2015, 37(3): 581-592.
[8] 孫陽, 姚士謀, 張落成. 長三角城市群“空間流”層級功能結(jié)構(gòu)——基于高鐵客運數(shù)據(jù)的分析 [J]. 地理科學(xué)進展, 2016, 35(11): 1381-1387.
[9] 王姣娥, 焦敬娟, 金鳳君. 高速鐵路對中國城市空間相互作用強度的影響 [J]. 地理學(xué)報, 2014, 69(12): 1833-1846.
[10] Allport R J, Brown M.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European highspeed rail network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 1993, 1381: 1-11.
[11] Urea J M, Menerault P, Garmendia M. The highspeed rail challenge for big intermediate cities: A 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perspective [J]. Cities, 2009, 26(5): 266-279.
[12] 王雨飛, 倪鵬飛. 高速鐵路影響下的經(jīng)濟增長溢出與區(qū)域空間優(yōu)化 [J]. 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 2016(2): 21-36.
[13] 李紅昌, Linda Tjia, 胡順香. 中國高速鐵路對沿線城市經(jīng)濟集聚與均等化的影響 [J]. 數(shù)量經(jīng)濟技術(shù)經(jīng)濟研究, 2016(11): 127-123.
[14] 董艷梅, 朱英明. 高鐵建設(shè)能否重塑中國的經(jīng)濟空間布局——基于就業(yè)工資和經(jīng)濟增長的區(qū)域異質(zhì)性視角 [J]. 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 2016(10): 92-108.
[15] Ahlfeldt G M, Feddersen A. From periphery to core: measuring agglomeration effects using highspeed rail [R]. Serc Discussion Papers, 2015.
[16] Kim K S. Highspeed rail developments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A case study of the Capital region in South Korea [J]. Cities, 2000, 17(4): 251-262.
[17] 宋曉麗, 李坤望. 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質(zhì)量提升對城市人口規(guī)模的影響——基于鐵路提速的實證分析 [J]. 當(dāng)代經(jīng)濟科學(xué), 2015(3): 19-26.
[18] Chen C L, Hall P. The wider spatialeconomic impacts of highspeed train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Manchester and Lille subregions [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2, 24(4): 89-110.
[19] 陳彥, 孟曉晨. 高速鐵路對客運市場、區(qū)域經(jīng)濟和空間結(jié)構(gòu)的影響 [J]. 城市發(fā)展研究, 2013, 20(4): 119-124.
[20] 楊開忠, 董亞寧, 薛領(lǐng), 等. “新”新經(jīng)濟地理學(xué)的回顧與展望 [J]. 廣西社會科學(xué), 2016(5): 63-74.
[21] 曲創(chuàng), 李曦萌. 經(jīng)濟發(fā)展還是要素流失: 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經(jīng)濟作用的區(qū)域差異研究 [J]. 當(dāng)代經(jīng)濟科學(xué), 2015, 37(1): 32-38.
[22] Krugman P, Venables A. Integration, specialization, and adjustment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6, 40(3): 959-67.
[23] Crozet M, Soubeyran P. EU enlargement and the internal geography of countrie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4, 32(1): 265-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