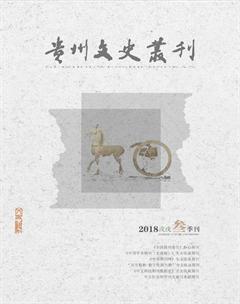抗戰初期貴州土地清查及其對抗戰的貢獻
翁澤紅
摘 要: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貴州憑其極為特殊的戰略地位,成為支持八年抗日戰爭的戰略基地和抗戰大后方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拱衛陪都重慶的重要前哨。為支持和支援抗戰,人貧地瘠的貴州作為戰時土地清查的重要省區,在抗戰初期進行了土地清查,整理地籍,以求增加政府田賦收入,并取得較大成效,貴州賦額為當時全國增加最多的省份,對抗戰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關鍵詞:抗戰 貴州 土地清查 貢獻
中圖分類號:K2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18)03-60-65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國開始了長達八年之久的全民族抗戰。抗戰伊始,國民黨軍隊便喪師失地。隨著東部及中部大部分地區相繼淪陷,南京國民政府為接受長期抗戰的事實,同年11月始被迫向西部遷都重慶。“以四川為中心 ,以西南其他省區為重點包括西南與西北的抗戰大后方成為支持八年抗日戰爭的戰略基地”。1貴州地處云貴高原東部,東、南、西、北分別與湖南、廣西、云南、四川等省毗連,為“西南三省中樞,又是陪都重慶聯絡華南及東南亞各國的國際交通線的必經之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2貴州憑其極為特殊的戰略地位成為抗戰大后方及戰略基地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拱衛陪都重慶的重要前哨。為支持和支援抗戰,人貧地瘠的貴州作為戰時土地清查的重要省區,在抗戰初期進行土地清查,整理地籍,以增加政府田賦收入,并取得較大成效,使貴州的賦額為當時全國增加最多的省份,對大后方抗戰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一、抗戰初期貴州土地清查成因
(一)南京政府財政收入銳減
中國歷來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民占總人口的80%以上。農業國家的主要財源為土地稅,其中以田賦最為悠久、普遍。歷史上,相對其他稅收而言,田賦長期成為歷代中央政府比較穩定的最大財政來源。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為體現孫中山 “平均地權政策”,“使耕者有其田,勞者得食”的主張,同年7月,南京國民政府將田賦由中央稅轉為地方稅,田賦收入遂成為各省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
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后,我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直到民國時期,全國經濟發展仍極不平衡。其主要表現為:較富裕的農業區域基本分布在中部和東部,且全國新式工業主要集中于東南沿海、沿江及東部重要鐵路沿線城市。東部整體經濟較為發達,而西部地區經濟以農業為主,且甚為落后閉塞。西部各省絕大部分地區農業長期采用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且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體,土地貧瘠,耕地面積少。而西南各省中的貴州直到 20 世紀 30 年代,“全省絕大多數地區仍然處于‘刀耕火種‘輪歇丟荒‘廣種薄收的原始型農業生產階段”。1加之,西部“新式工業僅占全國總數的6%”。西南、西北地區工業生產能力十分薄弱,農業經濟原始,西部整體經濟極度滯后。
基于上述原因,抗戰前夕,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并非田賦,而是主要來自于東部地區的關稅、鹽稅、統稅三項稅收。“僅以1937年預算數來看,三項稅收收入合計為7.72億元,占財政收入的77.29%。沿海地區的三稅收入又占總額的80%以上”。2然而,至南京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時,因日軍占有了“中國土地的1/3,農業生產基地的40%,工業生產能力的92%”。東部及中部地區的淪陷,使中國工業集中區和農業富庶區被日軍侵占,導致政府稅源枯竭,收入驟減,國家陷入經濟困境的局面,對于堅持長期抗戰造成嚴重影響。
(二)確立戰時土地政策,促進西南農業經濟發展
面臨戰區不斷擴大和日本對中國海陸交通封鎖的嚴峻形勢,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僅能依靠其所控制的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西部地區。又由于北洋政府及南京國民政府長期以來對農業的重要性認識不夠,致使1912-1937年間,全國農業的增長十分緩慢。為保證戰時軍民物資供應,增加抗戰力量,以適應抗戰需要,南京國民政府于1938年3月在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戰時經濟方針政策。此次會議決定,不僅要將經濟建設重心向西部后方轉移,以建立鞏固的抗戰后方基地;而且針對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所控制的西南、西北地區社會經濟狀況,會議著重強調了抗戰時期農業的重要性,把發展和建設西部后方農業經濟納入戰時軌道。“采取以西南為中心,先西南后西北的經濟發展戰略,明確地把經濟建設的重點放在西南地區”。3并把發展大后方的農業生產置諸工業、交通等各業之前,作為南京國民政府的當務之急。
此次會議,南京國民政府對土地政策進行了較大的調整。大會認為:“戰事發生后,環境突變,生死存亡之間不容再循常規,循序漸進,故非另定戰時土地政策,不能應時代之迫切要求”。通過了代表抗戰初期國民黨對于土地問題的基本主張和政策的《戰時土地政策案》,列出了“戰時土地政策大綱”九條。隨后1939年1月、4月分別召開了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及第一次全國生產會議,再次強調后方農業的重要性。提出:為彌補戰區的損失,需積極發展后方生產;要增強戰區抗戰力量,必須力謀戰區農業的復興。
(三)整理地籍,增加田賦收入
1938年確立的戰時土地政策的中心目的,以解決土地問題為前提,發展以西南為主的抗戰大后方農業生產,“提高土地利用之精度,增加生產面積”,以“足食”;“增加人民之納稅能力,平均人民對義務之負擔”,以“足財”。4即,增加田賦收入,使之成為抗戰主要經濟支撐力量,以保證軍需民用,維護社會穩定。要實現這一目的,必須以地籍整理為基礎,進行土地清查。民國初期至抗戰前夕,貴州征收田賦的依據仍沿襲明清舊制。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將田賦劃為地方稅,田賦成為各省主要財政收入。“田賦劃歸地方后,各省基本按土地肥瘠劃等定率,按畝征收。征收期限仍分上忙下忙兩期,統一折銀元征收”。5但因無確切的土地冊籍可查,全國普遍存在著土地實數不清,上田、下田不分,土地等則與納賦等級不符,土地集中、隱匿現象嚴重,各地畝法十分混亂的現象。地籍不清使“賦稅更無從稽核”。6加之,“軍閥混戰不息,更是賦斂無度,竭澤而漁。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繁雜、沉重的田賦已成為困擾中國農村的一個重要問題”。7當時田賦附加稅不僅種類繁雜,而且在農村稅捐中最為繁苛。附加稅超過正稅額至少一倍,甚而高達幾十倍,田賦混亂的局面十分嚴峻。據1934年對全國30個省田賦附加稅的調查,“共計有附加稅673種,最多的江蘇省竟達147種”。1
為了整頓田賦,南京國民政府首先不同程度地進行了地籍整理。1941年以前,整理地籍事宜是由各省自辦,或側重清丈,或采用航空測量,或采用土地陳報,實無定數。但因“土地測量,非長時巨費莫辦”,2雖然土地陳報精確程度與土地測丈相比相差甚大,但鑒于其節省時間、經費,南京國民政府大規模地推行土地陳報方法,“即由土地所有者自行陳報土地畝數產量之意”。1931年,蔣介石曾指出:“辦理土地陳報,為中央既定政策,不特藉以整理田賦平均人民負擔,即凡土地與糧食政策之實施,亦賴于奠其初基,意義至為重大”。3直到抗戰時期,除少數地區繼續辦理土地測量外,土地陳報已成為南京國民政府普遍認可的整理地籍的重要途徑。在此背景下,抗日戰爭爆發后,作為西南大后方省區之一的貴州,便以土地陳報為土地清查之主要途徑。1938年10月,武漢、廣州淪陷,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為了有效解決軍糧民食問題,1941年4月,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通過《為適應戰時需要擬將各省田賦暫歸中央接管以便統籌而資整理案》,貴州根據國民黨中央政府精神加大以土地陳報為途徑進行土地清查的力度。
二、抗戰初期貴州土地清查的概況
(一) 貴州耕地面積狀況
1939年,貴州“全省耕地面積占全省總面積之比例,所占百分率極低,最少者尚不及總面積百分之八”。4而在耕地面積中,貴州荒地面積在全國所占比例較大。根據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至1941年,“省內占總戶數的67.5%忙忙碌碌地努力農耕。然而,其耕地面積尚未達到全面積的20%。其中已耕地占12%,未開墾約為8%,大部分屬于荒地或森林”。5貴州每戶、每個農民平均攤得耕地面積比全國較低,且相差甚大。如1945年,中國地政學會所編《中央日報·中國土地問題特輯》載:貴州與廣東相比,貴州每人耕地畝數9.17畝,廣東每人耕地畝數為1018畝,相差900余畝。
雖然有關文獻記載難以全面、完整地反映出貴州全省耕地面積的實際情況。至解放前,貴州耕地面積統計多不統一、不準確,尚無可靠數據。但貴州耕地面積少,土地貧瘠,荒地面積比例較大,確為不爭的事實。整理地籍,進行土地清查,增加田賦收入,成為抗戰時期增加貴州財政收入的重要途徑。
(二) 抗戰前貴州地籍狀況
因貴州土地長期缺乏清查,即便有之,也因種種原因,導致地籍十分混亂,其主要表現為:畝法不一、耕地畝數不明、瞞報耕地面積、土地集中等。
畝法不一、耕地畝數不明。是因貴州巖溶地形十分發達,全境幾乎都是山地丘陵,是全國唯一沒有平原支撐山區農業省。貴州“跬步皆山,丈量不易”。就農業耕地面積而言,貴州民國初期至抗戰前夕的地籍基本上沿襲明清舊制,“故無畝分,不足言畝法也。唯有少數縣份,為課賦計值,亦有相沿之法:如以種,以稨,以出谷之挑數石數計”;6或以丘、塊、幅、股、型計等等。到1927年出現了又一種計畝法,即:“升科計畝,系以營造尺丈量,六十方丈為一分,六十方尺為一厘”(修訂升科章程第五條)。畝法不一,使田畝核算數不準確,甚至一些地區無法核算。
瞞報耕地面積、土地集中。為逃避賦稅,瞞報耕地面積時常發生,人為地使耕地面積數減少的現象十分嚴重。據1939年《貴州省農業概況調查》載:乾隆至光緒一百多年間,田畝數幾無多大增加,大致在260萬畝左右,至1915年反而減少,計130余萬畝,其實恐相差甚遠。1此外,土地高度集中。至抗戰時期“盡管貴州社會經濟發生了較大變化,但農村的生產關系基本未受觸動。據各地調查資料,占農村人口4—5%的地主,通常占有全部耕地的50—80%。占農村人口一半以上的貧雇農,只占有全部耕地的7—8%”。2據統計,1937年,廣大農民很少甚至根本沒有土地,地主采取物租、力租、錢租等地租形態對佃農進行剝削,佃農50%以上的勞動果實落入地主手中。這不僅增加了農民的負擔并導致其生活進一步貧困化,減少政府田賦收入,還阻礙了“增加人民之納稅能力,平均人民對義務之負擔”。
(三) 抗戰前貴州田賦狀況
“清末貴州田賦收入在全省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僅次于協款而占第二位。民國初期,也僅列于鹽稅收入之后居第二。至民國七年鴉片開禁后,田賦收入才退至鴉片、鹽稅、厘金等稅收之后,但仍不失為省財政一大收入。尤其是征收糧米實物,供應軍需民食所起的作用,更非任何其他稅收所能替代”。3作為中國田賦史上的一次大變化,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將中央稅轉為地方稅。為保證田賦收入的正常進行,1928年修正公布了《劃分國家收支地方收支標準案》《限制田賦附加八項辦法》,1933年制定了《整理田賦附加辦法十一條》,1934年制定了田賦稅則及附加章程6項。但由于長期以來貴州地籍混亂,田賦積弊深重,軍閥統治的23年間,政府政令更多有不達,從清末到1935年國民黨中央政府接管貴州,乃至抗戰前夕,田賦征收制度紊亂紛繁。田賦出現短征,每年逐減現象,且各縣拖欠田賦的情形極為嚴重。
1937年以前,貴州田賦包括地丁、秋糧、官租、雜課四種,其中田賦正額只有地丁、秋糧兩種。長期以來,貴州田賦“均是攤派認納,久未整理,飛灑隱匿,處處皆是,有糧無田,有田無糧,糧少田多,糧多田少,科則復雜,冊籍失散”,導致田賦收入較少。清末貴州田賦收入雖在全省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僅次于協款而居第二位,但僅占全省財政年歲收入的20.63%。4其間,貴州全省田賦糧額收入雖曾高達過70多萬元,但此現象實為罕見。直至抗日戰爭爆發前,“全省每年最低尚缺糧食三個月”。5如何進行田賦整理,增加貴州田賦收入,以保證軍糧民食和社會穩定,成為貴州農業中心工作的最重要問題。
(四) 貴州的土地陳報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召開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制定《整理全國土地計劃》,要求各地對土地進行陳報,整理田賦以增加收入。1930年,作為貴州地方稅的厘金被政府明令撤消,貴州財政收入明顯減少。為增加地方收入,在全國整理地籍、推行土地陳報的背景下,貴州自1930年到1932年,以土地陳報的方式對全省81個縣同時進行了土地清查,其可謂是抗戰以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貴州一次較大規模的土地清查。此次土地清查“由于重在自報,實際升科者寥寥無幾。當年實收556839元,僅占原額的76%,為歷年收入之最高額”,6然“猶不及江浙一縣之收入”。7由于地籍混亂、征收制度腐敗,制賦攤派隨意性強、輕重不均,或局勢動蕩、尚無秩序,或一些縣份少數民族較多填報困難等諸多原因,沒有達到實際效果。到1931年,實收田賦560727.69元,亦未收足。此次清查田畝行動歷經14個月,雖耗資巨款,而實際推行的縣份為數不過十之五、六。8因收效甚微,1932年4月被下令裁撤,貴州田賦仍舊混亂,田賦實際收入逐年總計減少。
1934年,國民政府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通過了《辦理土地陳報綱要草案》。此次會議后,土地陳報進入了省自為政的階段,并強調土地陳報必須因地制宜。1935年國民政府接管貴州,面臨著民國建立后,北洋政府廢除調劑給貴州的鄰省協銀,及南京國民政府取消貴州財政稅收中的厘金,田賦成為貴州最為可靠、最為重要稅源。1936年秋,國民黨中央財政部派員到貴州,催促以土地陳報方式首先整理地籍,以達到田賦整理的目的。貴州根據國民黨中央土地陳報綱要精神,制定貴州省土地陳報各項章則,擬定貴州各縣厘清田賦暫行辦法19條,設立各級土地陳報處,并于1936年12月通過《貴州省財政廳土地陳報處組織規程》17條,以推進土地陳報工作的開展。為慎重起見,全省81個縣分期陸續進行陳報,決定以貴陽縣為第一期作為試點進行。并按照實施準備(包括人事配備、宣傳及訓練、通知業戶插牌)、劃界分段、土地編查等程序和辦法進行操作。陳報后比陳報前全省土地面積幾乎增加3倍。1
當貴陽土地陳報工作進行到4個月左右,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貴州土地陳報進入到抗戰時期的土地陳報。隨著抗戰爆發,貴州人口從1936至1937年增加了38.37萬人,至1938年增加了40.75萬人。隨著貴州人口巨增,造成糧食供應緊張。根據國民政府相關精神,貴州采取以擴大耕地面積、增加單位面積產量為主要措施,以解決難民及前線軍用食糧問題。抗戰初期,從政府層面來講,貴州擴大耕地面積仍以陳報已開墾的土地為主要手段進行土地清查,同時加快了土地陳報工作的步伐。
在以貴陽縣為試點舉行土地陳報取得成功的基礎上,貴州其余各縣按照貴陽縣的實施程序與辦法先后分期陸續舉辦。到1938年8月,第二期、第三期共有7個縣份完成土地陳報工作,賦額最低增加二倍,最少也增加一倍以上。2此后至1940年有39個縣開展了該項工作。從1936年起,歷經4年零5個月,到1941年,貴州全省82個縣(1941年增加金沙縣)土地陳報工作全部完成。
三、抗戰初期貴州土地清查對抗戰的貢獻
(一)取得的成效
1. 在全國土地陳報中占有重要地位。從1934年根據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行政院頒布 《辦理土地陳報綱要》,在全國舉行土地陳報開始,到1941年止,各省遵照舉辦者先后有14省297縣,還有正在辦理的30縣,共327縣。3從舉行土地陳報的各省來看,貴州全省不僅各縣都完成了這一任務,而且數量巨大,在全國辦理土地陳報的縣數中比例最高,占36.2%。據《貴州財經資料匯編》載:貴州陳報后耕地面積共有1821.6萬畝,比陳報前增加了0.8倍,賦額為全國增加最多的省份。貴州土地陳報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展開大規模的土地陳報工作中無疑占有重要的地位。
2. 節省時間,節約經費。土地陳報在整理地籍方法中的程序雖為簡易,但在戰爭情況下,貴州仍對整理地籍極為重視。抗戰時期貴州土地陳報從1937年以貴陽為試點開始,到1941年82個縣全部陳報完畢,僅用了4年有余的時間。所用全部經費“共支1688065.48元,共計土地18216313畝,平均每畝費用不及一角”。4貴州積極使用土地陳報的手段進行地籍整理,不僅節省時間,而且節約經費。
3. 畝分有數,大致弄清了全省各縣地籍的基本情況。貴州田地原無畝分,各縣完成土地陳報后,大致弄清了地籍的基本情況,各縣田地有了畝分,使田賦征收有據可依。
4. 田額顯著增加。抗戰初期,貴州土地陳報從1937年起到1941年止,在耕地面積比陳報前增加0.8倍的基礎上,田賦收入得到顯著增加。田賦數額由“陳報前的73.2萬元,增加到516.5萬元,增加了7倍”5。根據1943貴州省政府編《黔政五年》統計:“全省增加數最多的是都江縣,陳報后較陳報前增加了168倍;增加最少的紫云縣,僅增加1倍;超過全省平均增長數的有36縣,占全省總縣數的43.4%;達不到平均數的有33縣,占全省總縣數的39.6%;越過平均數的縣多于達不到平均數的縣”。1隨著耕地面積大幅度的增加,貴州的賦額為全國增加最多之省份。2
(二)對抗戰的貢獻
在抗戰爆發的最初的一年里,全國“因農業收成不錯,糧價并不高……糧食問題并不突顯。但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由于農業生產停滯,糧食短缺,投機商人乘機囤積居奇,引起食價物價高漲,社會心理恐慌,對于軍民糧食的供應及社會秩序的穩定造成嚴重威脅。中央政府需要直接掌握實物(糧食),才能解決軍需民食,平穩物價,安定民生”3。鑒于這一情況,1941年4月,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通過了《各省田賦暫歸中央接管以便統籌而資整理案》,決定由國民政府直接掌握田賦征收,并實行田賦征實政策。在這一背景下,貴州土地陳報雖然存在著眾多的不足之處,但卻利大于弊,為田賦征實在貴州的實行奠定了較好的基礎。自1941年度全國各省田賦改征實物,截至1942年2月15日止,貴州成為征收實物達九成以上的三個省份之一,與浙江、江西、綏遠、云南、福建、湖南、河南、湖北、江蘇等9省,因“征收數額均在八成以上,成績優秀,10省財政廳長兼省田賦處處長均由財政部頒給財政獎章,副處長記大功一次”。4據統計,“八年抗戰中,貴州全省負擔的戰費,總數為609000000元。按當時全省人口總數1050萬計,每人平均負擔戰費為58元”,5為全國抗戰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貴州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統治控制得最為嚴密的極少數省區,對役政高度重視的貴州省政府既嚴格奉行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旨意,又采取了一些適合于省情的其他措施”6,使以土地陳報為途徑的土地清查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并取得較大的成效。
Abstract:In July 1937,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broke out in an all-round way. Guizhou, with its extremely special strategic position,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rategic base which supported the eight-year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large rear par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t was an important outpost for the southeastern side of the capital of Chongqing.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war of resistance, Guizhou, as an impoverished mankind and an important province of wartime land surveys, which carried out land inspection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orted out cad astrals to increase the revenue of the governments land taxation, and achieved great achievements. All of these have made Guizhou become the province, whose tax rate has increased most. Moreov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has benefited a lot from this province.
Key words: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Guizhou; Land inspection ; Contribution
(責任編輯:林建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