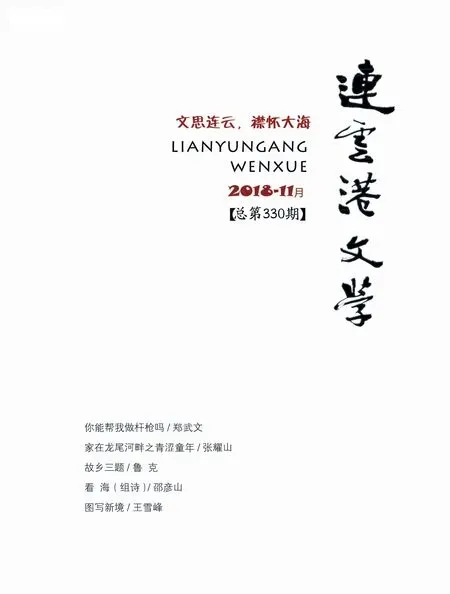十六歲的告別
來山
一
21世紀初年,在夏蔚鎮唯一的中學里,我進入了一個叫作青春的時期。中學坐落在省道的北面,每天有成百上千輛裝滿貨物的卡車從大門前經過。那些卡車帶著轟轟隆隆的聲音來,帶著隆隆轟轟的聲音去,只留下一陣陣濃煙和遙遠的回響。道路南邊是一個水庫。學校只有一棟三層的教學樓,其余的教室皆是平房。進入校門,一圓形花壇明顯地住在校園的中軸線上,花壇中間矗立著一棵雪松,周邊種以月季。學校的布局和構圖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印記。
站在學校的三樓,向南望去,近處的水庫和遠處的丘陵盡收眼底。白色的風吹過水面,粼粼波光泛起耀眼的金黃,一條孤獨的小船在漂浮搖動著。遠處起起伏伏的丘陵像海上的波浪,搖曳中講述著關于青春的故事。我們以迎風的姿態,推開青春期紅色的大門,享受著青春所帶來的澎湃激情。
在那所中學里,我從少年跨入了青年,我的身體開始發生一些莫名的變化:喉結開始凸起,過去熟悉的聲音消失,稀疏的胡子像是一首前奏。那些變化伴隨著新世紀的鐘聲,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學校離家有十幾里路。住校從那時開始。周日,花一塊錢,乘上屁股噴著濃煙的小客車來到學校。下周六,再坐上擠得滿滿當當的客車回家。學生像是沙包,被胡亂地堆積在車里,每一個學生就是一塊錢,堆得越多,就是更多的一塊錢。周六的乘車就像打仗,少年的身體在擠壓中得到了淬煉。
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步行回家。從學校向南行進,走過水庫的大壩,穿過幾個村莊,翻過兩座山,全程大約需要三四個鐘頭。山路上,桃樹、杏樹、梨樹、櫻桃樹和柿子樹,一年四季變幻著不同的風景。春天,山花開滿兩路,蜜蜂圍著花蕊震動翅膀騰起透明的小霧;夏天,蟬鳴響徹山間,路上走累了捧起一掬山泉消掉半路的炎熱;秋天,柿子高掛枝頭,身手矯捷的同伴會攀上高枝炫耀摘取的成果;冬天,寒雪覆蓋山嶺,天地之間一片茫茫我們走在其間像是朝圣的信徒。
走過四季,我感受著時間的觸角帶來的震動,觀察著輪回產生的代謝枯榮,聽著少年的骨骼如春筍破殼般生長。在那條山路上,我從13歲走到了16歲,在那條山路上,我度過了獨一無二的中學時代。
宿舍只能用簡陋這樣的詞匯來形容。木板搭建起的大通鋪,上下兩層,一個宿舍擠著三十多人。我運氣還不錯,睡在僅有的兩張鐵床的下鋪。開始,腦袋正對著門口,風吹得我腦袋發蒙。后來調換了方向,身體和門口成了直角。然而,無論如何躲避,到了冬天,寒風還是會順著夸張的縫隙擠進來。班主任給窗戶和木門釘上了塑料布,意圖將宿舍打造成塑料大棚,把我們當成蔬菜一樣培養。
一切都是徒勞!風的刁鉆勝過人的智慧。那擁擠、逼仄、透風的屋子,簡陋地承載著三十多人的青春。我們就在那混合著汗臭、腳臭以及飯菜味的空間里,進階到生命的一個新的階段。
我所在的班級是四班。初一入學時,班里有60人。進入初三,退學的人越來越多。那些自知中考無望或是厭倦了讀書的同學,會漸漸地離開。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同學,他們安靜地收拾被褥、書本、臉盆,像貨郎一樣把東西掛滿全身。他們和幾個要好的朋友道個別,有的甚至連道別也沒有,就悄悄地從那個班級消失了。我目送著他們離去的背影,開始感受到:青春并不全是光彩炫目的亮麗,青春還有著殘酷無情的一面。
從此,我們將仿若繁花,四散天涯。那些寫在同學錄上的話語,那“勿忘我”的錚錚誓言,都湮沒在了無邊的歲月中。自那以后,直到我研究生畢業,很多人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們過早地進入了那個叫作社會的地方,從事著五花八門的職業。他們過早地結婚生子,在自己還沒有長大的時候,就已經撫養孩子了。
二
王寶是初三時到班里的。他是復讀生,在中考中失敗了,對求學的渴望支撐著他再來一遍。教室里,他坐在我左手不遠處,宿舍里,他睡在我腳的右前方。多年過去,記憶斑駁,我和王寶在空間上的位置,我只能記得這樣的大概。但王寶的樣子,我是記得清晰的。
他的身形是精瘦精瘦的,目光是尖銳的。后來我讀蘇童的《妻妾成群》,看到蘇童形容陳佐千“形同仙鶴,干瘦細長”時,腦中立即浮現出王寶的身影。可惜王寶沒有陳佐千那樣的好福氣,不用說妻妾成群了,他連女人都沒有摸過。
王寶不僅瘦,皮膚也是黑黑的,臉上肌肉的線條分明,像是用筆從額頭一條一條畫到下巴。他走路有些駝背,笑起來時,臉上擠出和年齡不符的皺紋。他那種留守兒童式的神情,和他接觸的人難免有些心疼。
我和王寶熟悉起來,是因為他借了我一張光盤。錢鐘書在《圍城》里說過,借書是戀愛的初步,一借一還,一本書可以做兩次接觸的借口,而且不著痕跡。推而廣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會在借與還之間產生關聯。王寶借我光盤,我們在一借一還、道謝來回中,交流就多了起來。
2003年,卓依婷已過了她最紅的時期。王寶借我的光盤,錄的是卓依婷翻唱的歌曲,主打歌是《潮濕的心》。我把光盤帶回家,放入父親從深圳買回的VCD。畫面中,卓依婷穿著中式斜襟的翠綠小褂,撐著油紙傘,一邊在雨中徘徊一邊唱歌。母親看到畫面中的女子,直夸長得好看。就像小時候的某一天,母親、妹妹和我在吃早飯,電視里播放《搖太陽》的MV,一個年輕女子又唱又跳。母親對我說,這個女的長得真好看,你以后要是能取個這樣的媳婦就好了。我聽到母親這么說,羞愧地低下了頭。
青春期的我們,開始懵懵懂懂地感覺到,和異性接觸會讓我們無故的開心。我和王寶曾聊過關于異性的話題,但那也僅僅局限于哪個女孩子長得好看,誰和誰走得比較近。少年的愛慕是簡單而純粹的。據我所知,王寶并沒有談過戀愛。
學校教學資源有限,初一初二的學生在教學樓上課,初三學生在平房上課。三排平房布置了九個班級,后面是職工宿舍。語文袁老師有一間自己的小屋,屋里藏有很多經典名著,《祝福》《駱駝祥子》《紅樓夢》。我喜歡到小屋里去看書。那間房子,正是我文學啟蒙的搖籃。
有一段時間,初二一名漂亮的女孩常常從我們教室門前經過,因此成了一道流動的風景。每當她出現,我和王寶等人會趴在窗戶上看著她,看到她從東走到西,直到拐過墻角從視線中不見。她留著齊耳的短發,臉上干干凈凈的,五官小巧精致,倒像是南方的女子。多年以后,回想起一群少年趴在窗戶上的情景,我還是禁不住會心地一笑。那時,異性對我們來說,就像是一個巨大的謎,看不懂也猜不透,明明知道很美好,卻不知道該如何與之相處,帶著自以為是的不在乎,遠遠地欣賞。
鄉鎮中學升學率低,班主任管理嚴格,幾乎剝奪了我們所有的娛樂活動。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我們徹底釋放了少年的天性。那天下了很大的雪,雪越積越厚,整座學校被裹上了一條巨大的、厚厚的白色毯子。風一吹過,雪花紛紛揚揚從枝頭跌落,落到少年們的臉上、頸上和心上。
雪仗忽然就開始了。沒有征兆,已經無從考察是誰丟出了第一個雪球。第一個雪球勾引起第二個,然后是第三個第四個以至無數個。所有人在雪地上奔跑著、追逐著、喊叫著,不停地攢起雪球不斷地發射攻擊。我看到王寶雙手凍得通紅,他在衣服上擦一擦,將熱氣呼進兩手中間。感覺到溫暖后,他又興奮地投入戰斗。那是我們中學時代難得的一次嬉戲。
當戰斗進行到白熱化階段時,班主任從遠處走了過來。我們像一群逃兵一樣匆匆跑回教室。班主任戴著一貫的黑臉,憤怒地巡視著我們。我們坐在位子上不敢出聲,我看到王寶手里的雪球化了,水順著手指滴到了地上。
三
如果王寶還活著的話,今年該有31歲了。他應該已經結婚,甚至有兩個可愛的孩子。我想象著他結婚的樣子,他一定帶著那標志性的笑容,眼角的皺紋又深又長,黑瘦黑瘦的他,吃力地從車里抱下新娘,走向長長的紅地毯。
然而,那樣的畫面只能存在于想象中,那樣的情節,也只能生發于文字里。王寶的生命,終止于16歲的春夏之交。
中考之前,為了應付體育考試,學校安排課外活動讓我們鍛煉。那天下午,王寶和同學相約去操場拉單杠。王寶雖然瘦弱,拉單杠卻是一把好手,我們以前就見過他在單杠上的輕松瀟灑,仿佛不是他在用力,而是單杠在拉他。
就在那天下午,王寶還是像平常一樣走向了操場,就像無數個重復的白天無數個重復的黑夜一樣。他不知道,我們不知道,任誰也不知道,他走向的竟然是生命的最后一站。
天色尚明,操場上人來人往,王寶一躍而起抓住單杠,動作輕盈。王寶上下拉伸幾下之后,忽然像一只沒有抓住樹干的鳥,從枝頭跌落下來。同學們焦急地呼喚著他,他沒有任何反應。同學背起他就往鎮醫院跑去。
到了醫院的時候,醫生說人已經不行了。王寶在同學背上的時候,其實就已經離去了。同學氣喘吁吁的奔跑,也沒有救回他。
王寶就這么猝然地、輕易地、戲劇地、永遠地離開了。
王寶被安置在醫院躺椅上,等待父母來接他回家。王寶的父親先趕了過來,那個高大的男人怔怔地站在王寶的身邊,一言不發。王寶的母親來了以后,看到兒子躺在椅子上,責怪王寶父親,為什么不給孩子打點滴。她以為孩子只是睡著了。
在此之前,王寶曾在操場上暈倒過一次,因為王寶身體瘦弱,大家以為他是低血糖。他打了兩瓶點滴,休息了半天就繼續上課了。后來我們聽說,王寶曾暈倒過不止一次,一直都以為是血糖低。這一次,她的母親依然這么認為。
當王寶的母親知道自己的兒子不是睡著了,而是已經死掉了的時候,她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然后就昏倒在醫院的地面。
王寶去世的消息,是袁老師告知我們的。當天下午,同學們只知道王寶被送去了醫院,以為王寶與上次一樣,打過點滴就沒事了。晚間,袁老師動作緩慢地在黑板上寫了一首小詩。那首詩一共五句,可惜我只記住了后面三句,十幾年過去,那三句詩我仍牢牢記得:
風霜雨雪見真情,生命歸自然,陽光更燦爛。
我們看著袁老師在黑板上寫下這幾句詩,不明白他的意圖。袁老師兩手撐著講桌,沉重地宣布:王寶同學在今天下午因為腦溢血,已經離世了。袁老師說完,教師里經過短暫的靜寂,接著爆發出此起彼伏的哭聲。
十幾歲的我們,意氣風發的我們,未來充滿無限希望的我們,從未想過身邊的同學竟會死去。我們被以這樣一種方式去直面死亡。原來死亡不只是會發生在老年人身上,死亡會發生在任何年齡的人身上。與其說同學們是為王寶的離去而哭,不如說是被死亡所帶來的恐懼嚇哭的。
王寶的父親來到教室,收拾王寶的物品。王寶的抽屜里只有一份吃剩的辣皮,一種用大豆做成的,表面撒著大顆粒孜然的五毛錢一份的辣皮。那是我們中學時代最喜歡的食物,既可以當零食,也可以當菜。王寶的父親看到辣皮時,那個高大的男人一下子流下了眼淚,他用克制的、隱忍的哭泣,來哀悼自己的孩子。
那個男人流淚的表情,像是被人拍攝下來,永遠地鐫刻在我記憶的深處。
王寶出生于1987年,逝于2003年,他只有短短的16年生命。他的離去并沒有給這個世界造成什么影響,也沒有給歷史的進程帶來什么改變。2003年有太多需要記錄的事件,非典席卷全國,伊拉克戰爭爆發,張國榮和梅艷芳兩位巨星離世,那些事件看上去都比王寶的死亡要轟動得多。那一年我也只是一個少年,連記錄王寶一生的能力都沒有。
他的離去,只給幾個愛他的人,帶去了長久的傷痛。
王寶離開沒幾天,教室里又恢復了往日的熱鬧。課上,大家認真備戰中考,下課了,大家熱烈地聊天。王寶的床位空了出來,雖然宿舍擁擠,但沒有人睡到他原來的位置。
王寶的離去,在班里也沒有留下長久的傷痛,甚至還帶來了一點禁忌的味道。
王寶已經離開人世足足15年了,這個數字幾乎接近王寶去世時的年齡。他還能被我們那個班里的多少人記得,我不得而知。這些年我和初中同學聊天,沒有聽到誰會主動提起他。他沒能等到讀高中、讀大學,沒能和女孩子在大學里談一場戀愛,甚至連女孩的手都沒有牽過。
這些年里,我讀大學、讀研,輾轉多個城市,走過長長的路,經過無數的橋,在這個紛紛擾擾的社會,我努力找尋著一個屬于自己的坐標。我也很少會想起王寶。只是在聽到關于初中的事情,或是初中同學群又響起的時候,我就會想到王寶這位故人。我一想到他還沒有經歷什么就離開了,一想到他的生命未曾徹底綻放就凋落了,一想到我和其他同學已經比他多活了15年,我就感到無比的悲哀。
王寶的少年早逝,讓我對人和世界的不對等關系,有了痛苦的總結。
當說到“世界”這個詞匯時,我的意識里就會出現地球這個意象。世界這個詞匯在我的概念里,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不是紙面上的有限,而是無邊無際的。我就像一只小小的螞蟻,在一個巨大無比的球面上爬行。
我們生存的這顆星球,已經存在了40億年,而人類的歷史只有短短的170萬年。而我個人存在于這個球體的時間,在漫長的40億年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我望向過去,過去深不見底,我望向未來,未來深不可測。我太小太小,把我扔進那漫長的歲月,不用說水花了,連水霧都濺不起。
王寶16年的生命,在時間的坐標軸上,連一個微小的點都算不上。我的生命能夠延伸到哪一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雖然比王寶多走了一些路,但在那無限綿延的長軸上,同樣連一個點都算不上。人生往長遠了看,都免不了以孤獨和渺小收場。
作家史鐵生對他的地壇說過,要是有些事我沒說,你別以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沒忘,但是有些事只適合收藏。有些事不能變成語言,它們無法變成語言,一旦變成語言就不再是它們了。王寶16年的生命,我寫的有限,那些沒有寫的,就珍藏起來吧。如今,我站在30歲的渡口,能清晰地看到生命的流向,那遙遠未來的終點其實一直樹立在那。故人只能追憶,未來變數未知。有一天,我也會滿臉滄桑,也會步履蹣跚,但我不會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也不會溫順地任憑光明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