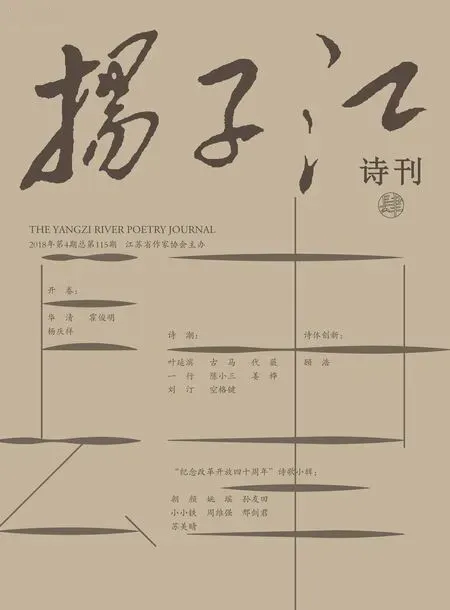[美]羅伯特·潘·沃倫詩選
李暉譯
羅伯特·潘·沃倫,1905年4月生于美國肯塔基州托德縣,1989年9月15日去世。美國桂冠詩人、小說家、文學評論家,三次普利策獎獲得者,“新批評派”創始人之一,被譽為“20世紀后半葉最重要的美國詩人”。
幻 象
我要建一座房子,在飛燕草開花的地方
一小塊赤楊林中的空地,落日的陰影
在那里投下紫羅蘭色的憂郁,
一只北美夜鷹發出怪異的鳴叫。
我要躺在一張水莎草做的床上,
傾聽那玻璃般透明的黑暗,
我的窗口有搖曳的燈光,
貓頭鷹投我以陰森的注視。
我要用初升的曙光點燃我的房子,
只留下灰燼和煙塵離去,
將那空地還給貓頭鷹和幼鹿,
當林子里灰色的煙霧飄逝。
浮世鳥類學
那只是一聲傍晚的鳥叫,聽不出是什么鳥;
當 我從泉邊取水回來,穿過屋后滿是石頭的牧場;
我靜靜站立,頭頂的天空與桶里的天空一樣靜。
多 少年過去,所有地方和面孔褪色,一些人已死去,
而我站在遠方的土地,傍晚依舊,我終于確定
比 起那些日后將淡忘的,我更懷念鳥鳴時那種寂靜。
媽媽做餅干
媽媽做餅干,
爸爸定規矩,
奶奶有時尿濕了床
貓咪用它的爪子。
媽媽掃廚房,
爸爸擠牛奶,
爺爺的褲子忘了系鈕扣,
小狗汪汪汪叫喚。
一切按上帝的心意,
太陽在西邊落下,
爸爸剃下巴的胡須,咔嚓——咔嚓
媽媽聽得最清楚。
拍拍手,孩子們,
拍拍手唱歌!
手拉手,孩子們,
圍成圈跳舞,
因為青蟲在葉子上唱歌,
黑甲蟲折起了手臂祈禱,
野地里的石頭洗凈了臉龐
迎接新一天的曙光。
但我們看見這些
只因我們整夜凝視
星星經過處黑暗的距離
直到那星光消逝。
致命極限
夕陽下,我看見鷹在懷俄明上空乘風翱翔。
它自松柏的黑暗中升起,掠過灰暗的
冷酷無情的缺口,越過蒼白,沖進雪山
悠然的純潔之上、夢幻般光譜的暮色中。
那里——西面——是特頓山脈。雪峰將很快成為
陰暗的輪廓,劃破星群。此刻,這塊黑點
懸浮于何等的高度?黃金眼是否將看到新的界域
上升至何種范圍來標記那最后一抹夕光?
或者,在體嘗到大氣的稀薄之后,它是否
懸停于瀕死之美景,在知曉
它將接受致命的極限,并蕩著
巨大的圓弧下降以重歸大地的呼吸
之前?或重歸巖石、腐朽、或其他此類事物,
以及我們緊握的任何夢想的黑暗之前?
真 愛
心在沉默中胡言亂語。發出沒有意義的
言詞,向來沒什么意義。
那時我十歲,瘦得皮包骨,紅發,
滿臉雀斑。在一輛黑色大別克車里,
開車的是個大男孩,打著領帶,她則坐在
那家雜貨店門前,從一根麥稈里
呷著什么東西。那美麗
無與倫比。令你的心跳停止。令
你的血液變濃。令你的呼吸中斷。讓你
覺得自己臟。你需要洗個熱水澡。
我靠在一根電線桿上,看著她。
我想我會死去,要是她看見我。
我怎么能跟那樣的明亮存在于一個世界?
兩年后她對我微笑。她
叫了我的名字。我想我又要死了。
她長大的哥哥們走起路來彎曲著膝蓋
帶著騎手式的狂妄自大。他們油頭粉面,
在理發館里面說笑話,無所事事。
他們的父親是那種被叫作醉鬼的家伙,
不管什么時候都呆在農場的三樓上
楓樹下那座白色大房子里,有二十五年了。
他從不下來。所有東西他們都拿上去給他。
我不知道他抵押了什么賭注。
他妻子人很好,是基督徒,祈禱。
他女兒結婚的時候,那老男人下來了,
穿一件舊燕尾服,帶褶的襯衫發黃。
兒子們攙扶著他。我看到婚禮。他們用
刻有花紋的請柬,非常時髦。我感覺
我就要哭了。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
想知道當某種事對她發生時她是否會哭。
抵押沒有被贖回。那要命的消息被私底下傳出。
她再也沒有回來。那個家
可說是東飄西散。如今再沒人穿那樣閃閃發亮的靴子。
但是我知道她永遠美麗,住著
一所漂亮的房子,在遠方。
她叫過一次我的名字,我沒想到她竟然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