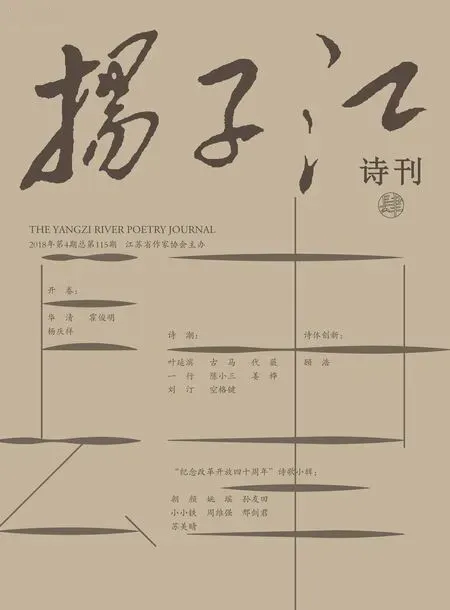蟬唱(組章)
賀林蟬
賀林蟬,1985年生,陜北人。
在長安
秦腔鑼鼓把油菜花敲成金黃,琴弦上七百年前的春天,依舊在枝頭搖搖晃晃。桃花、風聲,還有剛剛醒過來的蜂蝶鳴蟲,隨鼓點翻著跟頭,翻過驚蟄就變成驚雷。
那個騎驢走在林間小道上的老頭兒,背上馱著云朵,從《灞橋風雪圖》里出來以后,身體被露水洇潤出漣漪,一圈一圈走遠,消逝。
被安排在此折柳送別的那對遠古戀人,至今沒有勇氣說出離愁,淚濕衫袖,也打濕驛外梅花。使之過早吐露寂寞,河流也過早沾染了憂傷,藏起波瀾繞城而過,水的味道一天比一天咸。
三月從東城走到西城,踩疼了地下的骨頭和草根。銅馬車載著天圓地方經過章臺宮以后,一個朝代的遺民身似飛絮。
阿房宮與一場大火之間的關系并不值得探究,畫眉草把某個黃昏排布成千軍萬馬,穿過龍首原,與秦朝的那場大雨合兵一處,攻破了咸陽城。
大唐李白在長安酒肆一醉千年,偶爾醒來時,便在酒壺里裝滿月光。
仰天大笑仗劍江湖。抽刀斷水不如舉杯澆愁,對影邀月才知此身是客。
歸去、歸來,萬戶搗衣聲里自己變成了自己的陌生人。此刻天街無雨,從曲江池到大明宮,天空俯下身子,點亮行人臉上隔夜的迷惘。
就著傳說登上鐘樓,倚欄聽滄海,景云鐘一聲寂寥一聲滄桑,敲落檐下夜色濃稠,乳燕藏住呢喃,把天空、楊柳裁剪成無數個回眸。
從鼓樓上空緩緩飛過的鴿群,最后變成了風箏,這一夜春色圍城,陌上碧樹,以帝王的姿態俯瞰長安古道、酒旗高臺和錦殿羅帷。
叫住一列火車
古人以秋雨為引子,煮酒、賦詩,彈落燈花。潤筆、研墨,勾兌鄉愁,寫下胸中丘壑。
在拈斷胡須之前,任由雨腳在詩詞歌賦里驚擾空山、漲滿秋池,繞過回廊軒榭,閑打芭蕉。
今夜雨過西窗,我執意讓詩行空白,作為北雁南歸的途徑。墻角瘦竹是些一貧如洗的隱士,守不住身世里晴朗的一頁。
如果這場秋雨在子時的絕壁前懸崖勒馬,白楊樹過于耿直,拴不住春華秋實。
紅葉脫韁而去,敗給黑雪、流霜,越過神靈的高墻,被木魚擊中要害。
叫住一列火車,就挽留了所有的漂泊。
借青燈黃卷為它洗心革面,運輸花香和節奏。叫住站臺上掩面不語的人們,讓他們微笑、抬頭、側身,讓故事從容路過。
我回到窗前,回到夕陽濃稠的金黃里。這時,暮色的拼圖中多出了一只飛鳥,幾縷寒煙。
梨花辭
梨花和春雨之間的秘密,只有黯然神傷的女子能夠猜透。沒有被書寫過的一天里,人面桃花,比不得這十里香雪。
和古人一樣,我也把梨花當成冰姿玉骨的美人,在黃昏時分,著一襲素衣,隔窗聽雨。
東風乍起,把一地月光吹得搖搖晃晃,煙火人間依舊在陰晴圓缺中輪回。
玉階微冷。
未央宮中佳人遲暮,鶯歌燕舞還似當年,芳草萋萋都是離情別意。從今后,無人再憶王孫。
一只蜜蜂向我隱瞞了身份,她將把花蜜帶回某個朝代,讓唐詩宋詞略帶甜味,讓暖煙繞樹、玉笛橫吹,有人帶著醉意一再追問:一樹梨花一溪月,不知今夜屬何人?
夢里閑愁,隨梨花風雨飛過山溪野徑,四五家煙村隱約可見。柳葉隨歌、遠岫出山,楊花飛盡時,梨花已瘦,春色也憔悴。
此刻,需要借一抹殘陽與梨花告別,灑幾滴故人清淚。
背上行囊的人被昏鴉趕下山,酒醒處即是天涯,陰雨霏霏,將人心世事一瓣一瓣渡過清明。
山丹花,開在童年的某個角落
每當我用山南水北修辭春天的時候,山丹花就安靜地站在童年某個雞犬相聞的角落。
看故鄉被陽光一點點拔高、拉伸,一松手就滿臉惶惑地跌進黑夜。
月亮像一個哭花了臉的少女,坐在老榆樹的枝椏間,用內心僅存的喜悅,給予夜晚一點虛幻的光明。
這時,適合將那些稀疏的星子一遍又一遍默數成羊群,看它們在天河兩岸悠然踱步、打盹,啃食青草。
反芻出一朵白色云彩,無論向南向北,最后都飄散成貧瘠生活里一些似有似無的蛛絲馬跡。
苜蓿草在記憶里屢次破土而出,被小小刀鋒掐去一茬又長出一茬。
炊煙和晚風輪番占領過草垛之后,只剩下一條河,瘦骨嶙峋地從老皇歷上走遠……
這是我的故鄉。
這是山丹花的故鄉。
她像一個蕙質蘭心的女子,如果被山歌唱得羞答答欲說還休,就把她請進家門,讓她坐在墻頭。
日子從窯洞頂上升起、落下一次,開放一朵紅色火焰。
一曲蟬唱,足以注解整個秋天
在喧囂邊緣,還有一片高天深樹,適合坐聽蟬唱。
前一聲是喜悅,后一聲是鄉愁。
枝頭不是歸宿。在泥土里幾番輪回,生滅無常只在彈指剎那。
我用一曲蟬鳴注解橙黃橘綠。
這個姍姍來遲的季節適合遠行、獨處,也適合望穿秋水。適合用一滴露水喂養蟬鳴,適合用一枚熟透的果實召喚靈魂。
薄剪綃衣,披一身凄涼。
一雨一晴,聽三兩清音。
此刻,故鄉變成了遠方。那里槐花落盡,西風驟起,斜陽越窗而入的瞬間,蟬鳴正濃。
恰似深閨佳人,黛眉微蹙,和著琴音三疊,唱出故園情,相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