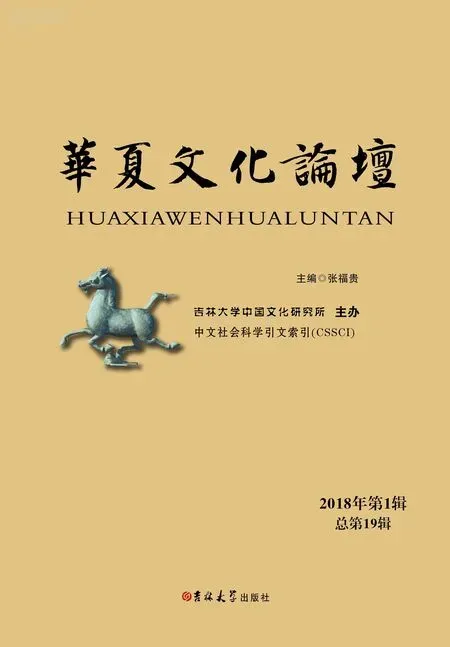生態批評視野下的中國文學:理論基礎與研究方向
劉 倡(Chang Liu) [德]蒂莫·穆勒(Timo Müller)
【內容提要】生態批評可以理解為一門旨在以生態環境為出發點對文學文化進行解讀的學術領域。在生態批評誕生至今的短短幾十年里,它已經從最初的一股小范圍的學術風潮發展成為一門在世界范圍內具有較大影響的文學文化批評理論與批評方法。通過梳理歐美生態批評運動的發展規律,本文試圖為中國的生態批評指明發展方向。根據對楊金才、李程、布依爾(Buell)三位學者就中國生態批評的現狀與未來所展開的論述,本文指出中國的生態批評的發展體現出兩大方向:其一,以歐美生態批評為參照,譯介西方生態批評理論與文學作品,從而與西方生態批評家展開對話;其二,基于中國本土的文學作品和哲學思想以及自身的歷史特性,開展有自身特色的理論創新。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許多來自歐洲和北美地區的人們意識到他們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正在以一種可能危及到人類未來生存的速度破壞著自然環境。空氣、土壤和水源的污染;動植物種群的滅絕;核能源潛在的危險;全球氣候變暖:這些問題逐漸出現在公開的辯論中,并促成了一場充滿活力的環保運動。盡管文學自始自終都是表征自然與解釋自然的核心工具,但文學研究者對文學研究可能對這些爭論作出重要貢獻這一點的認識卻是相對滯后的。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才形成了一種系統地研究文學與自然環境關系的方法。這種方法如今以“生態批評”這一名稱為人所知。
“生態批評”一詞是由學者William Rueckert在1978年首次提出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呼吁文學研究者將他們的研究視為聲援環保活動政治運動的一部分。這種觀點被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生態批評著作所認同。Lawrence Buell、Cheryll Glotfelty、Karl Kroeber和Glen Love等該領域的先驅性代表人物都堅信,文學能夠且應該讓人們更接近自然:這一點是通過提高人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而達到的,但更重要的是通過對自然環境的描述,使讀者對自然的美感和價值產生較為敏銳的感知。實現此目標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重新界定哪些文學作品可以歸為經典文學著作之列。早期的生態批評家推廣了那些符合環境文學標準的時期、體裁和作家,例如浪漫主義時期,對自然的非虛構性寫作,以及像John Clare、Henry David Thoreau和Wendell Berry這樣的作家。早期生態批評的目標不亞于在現代思想和行為中發起一場革命:從以人類為中心的生活方式向以自然為中心的生活方式進行轉變。
自21世紀伊始,早期生態批評的目標、論點和預設便開始不斷地被修正和擴展。在生態批評家之間,最先引起爭議的問題之一就是對“自然”的定義。自然一詞在西方傳統中被用來表達許多不同的概念。宇宙中物質生命的整體;地球上的有機生命;一切非人類的事物;所有非人工制造的事物;未受到人為影響的一切事物;平衡和諧的生活秩序;事物應有的狀態;事物真實存在的狀態;人性的本質:所有這一切都曾被稱為“自然”,盡管其中某些定義彼此相互矛盾。
早期的生態批評家談及自然時并不總是清楚他們所說的自然為何物。更重要的是,他們傾向于假設自然是每個人都直接以同樣的方式所體驗的事物。這種普遍的假設可能是由于這些批評家中的大多數人都有著相同的社會背景:他們來自現代的英語語系社會,是相對富裕的白人中產階級。21世紀初,隨著生態批評運動開始向這個小圈子的外延擴展,這兩種假設的謬誤便越發變得明顯了。Dana Phillips和Timothy Morton等學者指出,我們對自然的體驗是以我們在社會化過程中獲得的思想和期望為指導。來自其他族裔和國家背景的學者提高了人們對自然觀念的文化特殊性的認識。例如,美國原住民與自然的關系比起那些將美洲土地視為荒野并前來征服控制這片土地的白人定居者與自然的關系是截然不同的。
這種日益增長的就文化對自然環境的界定能力的強調所引起的兩種發展將有助于在中國語境下對生態批評與環境寫作進行思考。一方面,它將生態批評的范圍從文學擴展到了更加廣泛的文化。今天,學者們研究各種文化因素在環境問題的協商中所做出的貢獻,例如音樂、電影、電視,以及政治、經濟和宗教話語。所有這些都隱秘或明晰地包含著關于人類生命與其環境二者關系的信息。大多學者現在都同意,這些信息不僅影響了我們對環境問題的看法,也影響了我們對所居住的世界的看法。這種從文化協商的角度對自然展開的研究通常被稱為“環境研究”或“環境人文學”,這些術語試圖將生態批評的范圍擴展到文學批評之外。
其次,人們日益認識到這些看法背后的文化特殊性,這種日漸增長的覺悟把環境正義問題推向了生態批評的前沿。“環境正義”一詞是指人們在環境問題的范疇內針對侵犯平等與自決等基本原則的思考。環境污染的益處和風險的分配往往是不平均的,例如,那些在遭到污染的環境里受罪的人并不總是那些制造污染的人。即使那些看似親善環境的做法也會使這種不公正的現象長期存在。例如,假設政府試圖通過借助水力發電取代煤炭的方法來減少對空氣的污染,那么修建水壩和人工湖可能會導致相關地區的原住民顛沛流離地搬出他們的原居住地,然而空氣污染主要是由富裕的城市居民與他們不成比例的能源消耗所造成的。
這些例子表明,環境問題往往是與全球現象聯系在一起的。生態評論家需要相應地調整他們的視野。如果他們局限于頌揚地區性的風景,他們就會遺漏全球生態系統這一重要層面。如果他們局限于抽象地討論全球環境問題,那么他們就會遺漏這些問題在特定區域(和文化上)的具體表現。這種“地方意識”和“星球意識”之間的相互作用仍然是當今生態批評的核心問題。要提高對這種相互作用的認識,方法之一便是擴大生態批評的研究范圍。絕大多數生態批評家仍然來自西方國家,他們大部分的研究內容都集中在關于西方作家和西方世界的問題。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將為拓展生態批評的研究范疇并對生態批評的某些前提假設發起質疑提供一個寶貴的契機。
期待中國文學文化研究領域的專家在這一任務中發揮重要作用是合情合理的。在2004年的一次采訪中,Lawrence Buell表達了類似的期望,并堅信中國生態批評家在進入生態批評運動時將大有作為。Buell的信念來自對三個方向的觀察。第一,Buell強調通過在中國藝術與文化的內部尋找資源,人們可以發現值得通過生態批評視角進行研究的材料。第二,根據他在哈佛大學的同事杜維明關于新儒學與環境的研究,Buell指明了中國本土哲學對生態批評可能做出的潛在貢獻。第三,中國現代化的獨特經驗也保證了中國生態批評家可以為這一學術領域帶來獨到的見解。Buell為中國生態批評所設想的藍圖既是具有說服力的,又是令人值得期望的。然而,中國生態批評家的所作所為卻與這一藍圖有所不同。
Simon Estok與Won-Chung Kim合編的East Asian Ecocriticisms: A Critical Reader
(東亞生態批評:一部批判性導讀)在這一領域中稱得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在這本書中,Estok與Kim召集了中日韓三國學者,讓這些學者自己發聲,與更廣闊的國際性的英語讀者展開對話。該書關于中國文學的部分以楊金才的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當代中國文學與批評中的環境維度)一文開始,在該文中,楊金才指出中國生態批評的發展所經歷的四個階段:“(1)重述;(2)比較,跨文化理論化;(3)中國文化生態研究;(4)外國文學研究”。在一篇發表于一年后的論文里,李程指出了中國生態批評發展的兩大障礙,從而補充了楊金才的觀點,這些障礙是:第一,與生態批評相關的美國文學文本和學術論文沒有被及時地譯介到中國;第二,生態批評這一學術范疇內的一些分支領域尚未在中國的生態批評領域里得到發展。李程將責任歸咎于中國學者,并批評他們“保守”,批評他們代表了“城市中產階級漢人的偏見”。李程對中國學者的描述更像是一種未經批判的假設,而這種假設本身便是經不起推敲的。例如,中國后革命時期的男性知識分子所經歷的男性氣質危機以及女性知識分子在學術話語中的式微從性別研究的角度挑戰了李程的假設;而漢族、少數民族、國家政體三者間的復雜關系可以從批判性漢族研究的角度進一步復雜化李程的論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李程對性別和民族不加批判的假設再次證明了他所呼吁的中國生態批評需要提升性別意識和民族意識的迫切性,并為西方女性生態批評理論和環境正義批評進入漢語言文學研究鋪平了道路。楊金才和李程的研究表明,中國生態批評的發展與Buell的預測并不完全一致。與其通過從自身內部尋找解決中國環境問題的答案,中國的生態批評以美國的生態批評為原型,力爭達到理論上的復雜性,展開跨國對話,并急切地著眼于中國的外部,想要在西方生態批評的話語中為自己爭取一席之地。
出于不同的原因,來自世界文學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者們所做出的貢獻也是值得注意的。Theo D’haen, David Damrosch, 與Djelal Kadir三位學者主編的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收錄了Ursula Heise撰寫的一篇題為《世界文學與環境(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的論文,這篇論文把中國作家姜戎的作品《狼圖騰》送進了形成中的世界環境文學經典作品之列。盡管Heise的論文在這本厚厚的世界文學參考書當中只占據了薄薄的幾頁,其意義確實非常重大的,因為Heise和幾位編輯把中國環境文學帶進了世界文學的討論范疇之中,并強調了對何為文學經典這一問題進行反思。兩年以后,來自拜羅伊特大學的美國文學文化研究學者Sylvia Mayer為該校美國研究以及跨文化英語語系文學文化研究等專業的學生開設了一門名為“生態與文化多樣性:世界文學與環境”的討論課。這門討論課的內容涵蓋了具有代表性的批評理論以及對文學文本的分析討論,其中所涉及到的文學文本便包含了姜戎的《狼圖騰》。這些學者并不是經過專門學術訓練的漢學家,他們對中國環境文學的研究方法與視角也各不相同,但是他們對中國生態批評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卻有一點相通之處,那就是他們幫助中國文學走出了原有的學科領域的限制,把中國文學帶進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之列,使中國文學觸及到了傳統的中國文學專家之外的更為廣闊的讀者群體。上述兩大類學者及其研究對中國生態批評的學科發展領域具有重要的意義,其原因有三。首先,像楊金才與李程這一類中國文學專家試圖通過回應由西方學者所構建的龐雜的生態批評理論與方法論來為中國生態批評尋找自己的位置。其次,通過探討何為經典以及文化多樣性等問題,Ursula Heise、Sylvia Mayer、Simon Estok等學者將中國文學文本置于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之外的學術范疇,比方說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然而這兩組學者也代表了兩種局限。例如那一類熱衷于向中國譯介西方生態批評理論與方法論著作的學者們,不論他們的譯介速度有多迅速,他們終將處于步西方學者之后塵的尷尬地位。再次,通過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視角來研究中國環境文學的學者們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賴中國文學作品的英譯本來展開各自的研究,而這將嚴重地局限這一類學者對文學文本的選擇空間。由此看來,Lawrence Buell為中國生態批評所構想的藍圖就重新擁有了現實意義:對中國的生態批評家而言,通過探索中國自身特性來尋求解決環境問題的途徑有可能幫助中國生態批評家們實現潛在的突破。
Buell的建議有三層含義。首先便是考察中國歷史的特殊性。正如許多環境史學家所論證的那樣,中國與環境問題的糾葛絕不簡單是現代化進程所衍生出的一個問題。然而關于中國與現代化的關系以及隨之而來的環境問題,中國確實有自己的故事要說。比方說,在中國各大媒體上廣為流傳的一則故事提到了1950年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與時任北京市長彭真一番關于煙囪的對話。毛澤東說:“從天安門望出去,應該處處都有煙囪”。這則軼事的可信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懷疑的,但它確切地表明,煙囪與霧霾曾以正面形象出現在中國的歷史當中,被視為中國現代化與工業化的象征與衡量標準。考慮到環境惡化的巨大影響,即便是在當下,中國的環境意識也是明顯缺失的。當楊金才指出“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生態意識過于有限”時,他也正確地表達了類似的擔憂。然而這在未來的幾年里將有所改變,中國的環境問題也會得到解決,如果中國人民可以足夠重視習近平主席所提倡的生態文明思想。鑒于中國在現代化、工業化以及環境惡化等方面的獨特經歷,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中國為何缺少足夠的生態意識,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會給國際生態批評話語提供獨到的貢獻。
Buell的第二點建議是利用中國哲學思想這一資源。除去李程對西方生態批評理論漢譯遲緩這一問題的批判之外,楊金才還指出了另一個與翻譯有關的挑戰。楊金才寫道:“翻譯質量低劣、誤讀,以及時有發生的過于牽強的解讀在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中是一種普遍的做法”。更快更好地提供高質量的漢譯確實是可行的一個解決方案,但這也有它自有的局限性。知名生態批評家Simon Estok所代表的這一類的學者所希望看到的是講漢語的學者們擁有自己的話語權,并與他們那些來自西方學界的同行們展開對話。然而這對話的質量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如果中國學者所做的僅僅是癡迷于制造西方理論的相似品或變異品。對這一局限的有效回應便是重新重視Buell所提出的從中國本土哲學思想內部尋求理論話語與突破。這一回應將促使中國學者利用中國本土哲學思想對環境問題進行理論化。杜維民的論文《新儒家人文主義的生態轉向:對中國和世界的啟示》便是用新儒學解決中國環境問題的一種堪稱典范的創新運用。陳廣琛的論文《個人的環境:沈從文和高行健的自傳體作品》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例子來證明如何在道教話語的范疇之內理論化環境問題。由此可見,杜維明與陳廣琛所代表的此一類由中國本土哲學思想所發展起來的理論性論著是中國生態批評領域中所急切需要的。
最后,Buell呼吁學者們積極尋找相關的中國文學作品,并幫助這些作品在由生態批評所塑造的文學經典以及批評話語中確立應有的地位。通過王德威、唐麗園、Ursula Heise、Sylvia Mayer等學者的努力,中國的自然寫作和環境文學在中國文學史和世界環境文學等領域得到了相應的認可,姜戎的《狼圖騰》也成為了當代文學的經典作品并在環境人文學領域中被頻繁地討論。但是中國的另一些文學作品呢?那些在生態批評話語中同樣重要卻還不曾得到足夠的認可與研究的中國文學作品呢?例如,賈平凹的《懷念狼》是一部比姜戎的《狼圖騰》早四年出版的小說,兩部作品所處理的內容都是極為相似的,如果說這兩本書中的某一部比另一部更優秀,那這樣的論述注定是難以令人信服的,然而這樣一部重要的作品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尚無明晰的定位。《懷念狼》同樣也沒有得到世界環境文學領域的關注,這或許是由于該書目前仍然沒有英譯本問世造成的。因此,更多的中國文學作品迫切地需要從生態批評的視角進行系統化的研究,翻譯成其他語言,并為之在中國文學史以及世界環境文學經典作品之中尋找合適的地位。這也是中國生態批評家們不容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