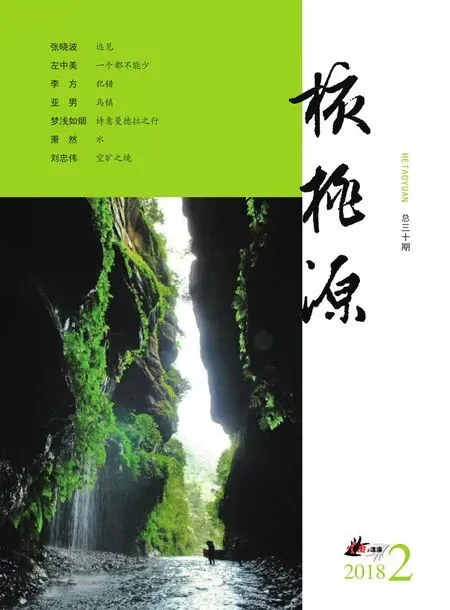過街天橋(外二章)
十字路口,天橋如弓。
又一個脊梁彎曲下來,眾生皆艱難。
生活的壓迫,我已習慣彎著腰行走。
要過橋,我必須選擇攀登。
一個姓名被隨手丟棄的人,站在天橋上,也不可能高人一等。
爬上這座人形支撐的天路,幾乎掏盡了我畢生精力。
腳下眾生喧嘩如蟻。像蒙太奇,更像傳送帶上流水作業。
一頭獅子在體內狂奔,口中噴出火焰。
天橋上,出口密集如夢。我卻因色盲、或近視,久困其中。
我有上升時的眩暈,更有下降時的恐懼。
這個春日正午,幾片樹葉從我頭頂掠過,讓我身上陡生寒意。
我不知道,它們那一片升上天堂,那一片墜落塵埃。
經歷過風雨,也經歷過寒暑。天橋無言,站在自己影子里。
你過,它在那里。你不過,它還在那里。
高處風寒。
水西門
水從這里進來,也從這里出去。
通往天堂,也通向地獄。
一把劍銹跡斑斑,懸在門楣上。那位前朝鑄劍人,早已隨河水走遠。
日夜出進城門的人,誰也沒有在意,頭頂上湍急的洪水。
門內是淪陷區,門外是淹沒區。
一些悲壯場景,上帝還在虛構。
春天的細雨,并不構成威脅。可是淋在身上,仍讓人們恐懼。
35年后的8月。我站水西門口,一只腳邁出門外,一只腳尚在門內。
我有些恍惚。往事如水上飄浮的葉子,讓人理不清天災還是人禍。
汛期將至。關與不關,這扇門顯然還在猶豫。
這是一個生之門,也是一個亡之門。
誰是主宰者。上帝,還是自己。
夜晚,我聽到天上有水聲流過,把一城人靈魂剖開。
在東堤上
筑起大堤,水自然就遠了。水無可奈何。
環堤公園里的樹木、花草、雕塑和鳥鳴,如同我身上脫落的關節,或毛發。
它們被生活封住了穴位,終日沉默,但對我構不成任何威協。
而那些冰冷的方言,卻讓人時刻提起誡心。
春日里,這些荒草一樣蔓延的想法,真是一種罪過。
你看那些老人、情侶和孩童,或相擁、或親妮、或玩耍,各得其所,盡情沐浴著這水流一樣的陽光。
唯我懷揣孤獨,攏起雙手,選擇與他們背道而馳。
河風尚存寒意。我不怨恨,眼前萬象,無不讓我心生暖意。
我不掩飾。我把一生的破綻,一一寫在臉上,故意暴露給人間。
東堤上那些風,吹了一陣就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