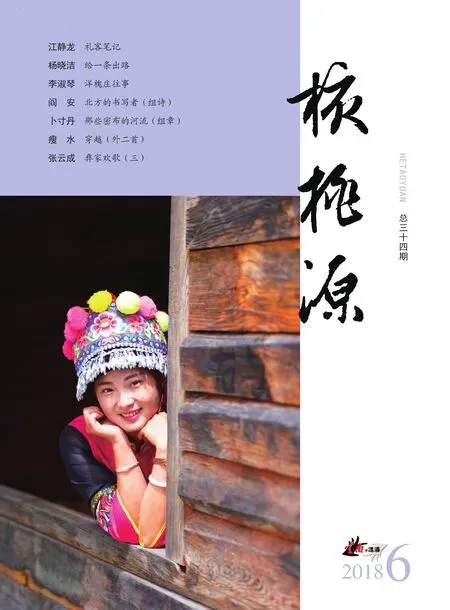紙上的萬里江山(組詩)
吳永強
所有水是清澈的,只有我渾濁
所有路是平坦的,只有我崎嶇
所有動物是歡快的,只有我暴躁不安
所有女人是有情調的,只有我不堪一擊
所有風是溫柔的,只有我做暴君
所有等待是徒勞的,只有我提供片刻歡愉
所有魚是愉悅的,只有我是一滴多余的水
一個人,一支筆,一個書寫的理由
寫困乏,寫孤絕,寫紙上的萬里江山
再次想起一個遠方的女人
比如現在,一個人整理千里地圖
看到秋天的山野,格子衣服問候草木
一朵花呈現出不同的詮釋
丘陵伴隨丘陵,長江越流越柔軟
醉了多少次,每一次都和她無關
偶爾想起,轉瞬就忘記了
大腦不是記憶的閥門,我不是我的字典
清空的影像隨時爆發出新的大片
帶著所有的眼睛,去尋找眼睛
帶著所有的同類,去尋找同類
帶著一個遠方的身影,去告別那個身影
為一個人描畫一點兒什么,傾斜一點兒什么
更多季節在我們的眼睛里
走過荒草的橋梁。作為季節最后的哀鳴
荒草提供山坡臃腫的形狀
橋上兩雙腳,越走,就從土里拔了出來
你看,那條綠色的大圍巾,通向東邊和西邊
圍巾里包裹一條黃色的大水
和荒草一樣,時間的河流陷入季節的憂傷
更多的是高樓,荒草自高樓里長出
你和我,自山里長出
下午和擋住天空的云彩,自我們心里長出
西邊是華山,我們已征服過了
它也征服了我們。深陷在時間的山坡上
更多的山,更多的季節,準備重塑我們的身體
夢囈者
困厄者,如我,在夜里穿越整個山區
需要一列火車,填充我堅實的身體和思想
一個醉酒者,躺在臥鋪上鼾聲如雷
一個憐惜者以鋼鐵之軀行進
背后是海濱的沙子,車站的開始,如我
撕開胸膛的剎那被更多人蹂躪
哐啷哐啷……寂寞
如我,只是一個自我消解的惡人
窗外那些熟悉的村莊,夜里一無所有
那個在野地里尋找寶石的孩子
那個帶著寶石遠走的孩子。那個戀愛中的犀牛
那個重達十斤的嘆息,唉,有我在
火車就有靈光乍現的可能
速度就有青春的機會。人間還是人間
在臨沂街頭聽《沂蒙山小調》
不可復制,固有的命運已永別。
直到此刻,一輛灑水車沿著坦蕩的速度
帶來一種過去的旋律
歌聲把整個山區塞進城市
把山羊塞給柏油路,把青草塞給鐵和水泥
在這里,我還是那個農民的孩子
是一群羊的主人,或奴隸
——也許永遠視而不見
片刻之后,灑水車遠去了
我走到沂河邊,想起許多年前這樣寫詩:
沿著沂河往上走,走到一條小支流
再往上,翻過山,穿過一片樹林
會遇見一個立體的我,翻看電影膠片
太陽底下,我的倒影在時間里游蕩
所有往事在河里洗了又洗
所有年輪,在山坡上圈了一圈又一圈
直到一聲槍響,我倒在明晃晃的夜色里
午后大明湖
柳樹,如我,彎腰駝背站了十年
海棠,如我,開花需要新的陪伴
荷花,如我,愛荷花的人早已遠去
湖水,如我,越寬廣越瘦弱
歷下亭,如我,杜甫和蒲松齡都走了
一座孤獨的島,一個孤獨的亭子
一個孤獨的年輕人,在湖邊
一個孤獨的中午。四散而去的空氣
如我,是什么味道?我的味道
北方的城市,如我,需要拯救
姓杜的游人,如我
眉頭緊鎖,而酒量卻在迷醉中大了起來
記 性
他是一場無人參觀的游戲
是一條獨自奔流的河
是棗樹結果時被掐掉的那朵花
是雨中無處躲藏的一滴水
他偏執,任性,一次次丟掉自己
人類泛濫的地球上
一個瘋掉的人,不足為奇,可以忽略
祁連山
只有一個牧民
只有一個我
在這里,只想做皇帝
生命短暫
讓我長生不老
和此山一次次恩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