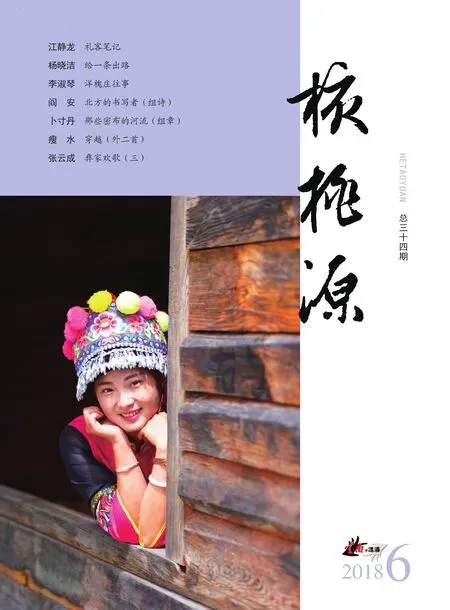在甘南,在舟曲
趙正文
1.今夜,請允許我暢想舟曲
時光的喻體上,歲月的胎痕早已脫落。
乘天風而來,抖落時光的塵埃,抖落昨夜黯淡的夢寐,像一只優雅的水鳥,靜靜棲落。
青藏高原之側,西秦嶺岷迭山系,誰水靈靈的眼眸,盯著這生動的人間?
光把一切呈現給審美的心靈。長天水闊,翩飛的雁影正消隱于縹緲的桑煙。我必須借助一縷皎潔的月光,把舟曲想象成一粒飄香的茶花。
長天水闊,三月的舟曲明凈、清遠。一切澄明得像剛剛做過一場法事。由身到心,伴隨著一絲澄明的意念,一個人的心靈在抵達的一刻趨于高貴。
2.泉城
把悠然的云腳從藍藍的天空一把拉到懷中的,是清清亮亮的白龍河。
泉城。為水一帶,為城一域。我驚奇于一切簡潔到極具天然與神性。
一尺水,十丈波。于是有了這遼闊的兩岸,草原和村落。
有了這九十九眼泉水,有了龍廟和城池;有了這悠然的白云,和這戳破白云的日腳。
有了光;有了你,有了我;有了這至空至明的藍天和心路。
有了這隴上的小江南,有了這懸掛的彩燈和楹聯;有了這連翠的松棚,和這滿街服裝各異的才子佳人。
今夜,誰的馬蹄會誤入時光的河道,驚醒我體內沉睡的蝌蚪?
巴寨溝
“一夜之后,木魚醒了
佛的額頭晨鐘敲響,
經文沐浴著褐色的山林。”
而一棵領春木是孤獨的風景,兩棵云杉是甜蜜的故事,三棵赤樺是苦澀的糾纏。
先于草木。先于花朵。先于先天之欲。先于邏輯修辭。先于概念和屬性。
恰與一縷月光同年。
我的巴寨溝啊!林木交錯,草甸豐美,裸巖和積雪如千年的睡美人,在季節的轉換里翻身,唏噓。
大地打開經卷,聽時光老人為善良的人們虔誠禱告。
無潮涌而來的喧鬧,無奔騰而去的虛妄。
一縷風把驚醒的喜悅,奔走相告。
3.在拉尕山
一只蒼鷹擎起一方神性的天空,擎起紅塵白浪的角逐中日漸疲憊的心靈。
而明媚的水,早淡出江湖。 走進來,塵埃落定;走出去,波瀾不驚。
湖洼,一個比一個簡潔;溪流,一處比一處生動。
像一串清雅的小令,從白龍江的上游搖來,讓乘興而至的游客,聞子規啼,看鳳棲梧。
不必追問誰是誰的江湖,誰是誰的魚。
“我和你是兩岸,永隔一江水。”
而黃昏即將熄滅。唯一的火種,
被拉尕山抱在懷里。
黑夜掩住疲憊的心靈,唯一躁動的是山寨修禊的鼓角。
幾簇篝火把神圣的光亮嵌進黑夜。我看見格薩爾王正化雪為墨,為珠牡王妃描畫眉心和唇角。
山光浮翠,樹嵐倒映。而花非花。霧非霧。朦朧中,勾起一陣明媚的欲望。
羚羊掛角,香象渡河。今夜,
一個人同天堂的距離,就是他同拉尕山的距離。
5.白龍河
我愿意接受這樣的結局:讓你做蓮花,在轉身時盛開,
美麗如初,用你的潔白或鮮艷,對接陽春三月的煦煦日光。
而我,在一座大山拋下的陰影里,獨自反芻你遺留給我的
所有罪名。
我無疑已陷入這俗世的泥淖!并逐漸習慣這深處的黑
和腐爛。重重泥水之下,沒有救贖之道,我已學會閉上眼睛,屏住呼吸,不與任何魚交換眼神和詞語。
并試著學你,一轉身,就是眾生懷里閃光的露珠。
白龍河!你有時溫順,有時桀驁。像歷史里仗劍直行的劍客,
時或為一句話的真理亮出劍芒。
而今天,我在你明媚的臂彎里,吹簫,彈琴,就著炒米
和梨花的芬芳,唱著倉央嘉措的情歌。
白龍河!我愿是你的一朵浪花,并希望最后由你的一滴水,渡我
——到生之彼岸!
6.賽爾布
白云纏頭,黑云裹腳。靈身守著時間的大門。
聚攏人間無邊的愛,大地之上,一種吉祥普照人間。
東望坪定,南眺拉尕。掩住小小的峪口,我會不會在今夜
找到愛情的火種?
這是黃昏七點鐘,黑峪寨已奏響請神的鼓角,燃起祈愿的桑煙。
無法不動情啊!這處子的喻體最沉吟的修辭,在雪原亮出雕花的慈光。玉碎的欲望,抬高村寨和湖水。
而湖水靜止,抑或接近靜止。湖水掩起唱歌的喉嚨,讓內心的情感趨于曖昧,甘愿為每一位游客斷流,或沉香。
月亮已在昨夜失足,融成浮香的青稞酒。懷抱大愛的賽爾布啊!請接納敲窗的東風,接納一首詩的草稿或構思。今夜,你一定要掬我為盞,但不要獨酌,不要相思成病。
我只要你明明郎朗。
7.尕海湖:甘南的明眸
一切如此明了,又如此曖昧。
格薩爾盤坐湖邊,左手捧著五千年的月光,右手捧著三千年的雪。
中間是一個人敞開的胸膛,和珠牡王妃清澈的眼眸。
巴噶瓦發,我黑頭發的君王!
今天,我借著尕海湖的睛光,讀你。
18宗,再18宗。我人神合一的英雄啊!
今天,我不要哈達,我只求一件——豹紋的皮氅!
一定有鷹,或者雕,在海子的上空盤旋。
藍天澄明,湖水澄明。朵朵白云像潔白的羔羊正踏著天梯重返人間。
群鳥落地成花,無韁的野馬像閃電掠過我內心的草原。
今夜,我注定會在岸邊遇見夢中那位手持牧鞭的少女,遇見
我的源頭活水,遇見
我命里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