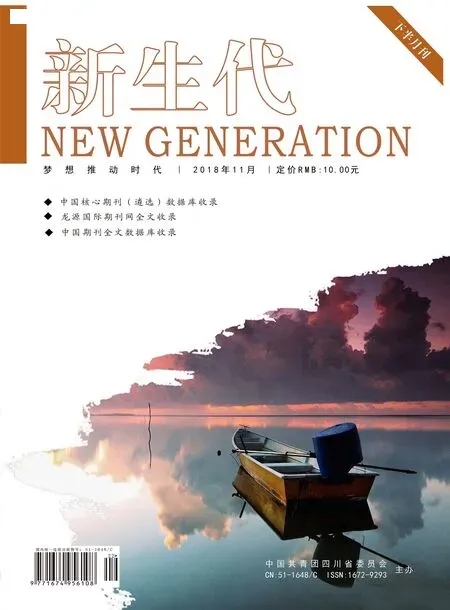居室對于現代生活的意義
佟嘯 海南大學 海南海口 570228
一、現代生活中的居室
正如本雅明在《路易·菲利普與居室》中所說:“在路易菲利普統治時期,作為私人的個體走上了歷史舞臺...對于私人而言,居所第一次與工作場所對立了起來。”很顯然,“公”與“私”的對立,也屬于資本主義的一項發明,因此,私有的居住環境,在現代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本雅明看來,由于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城市生活的整一化以及機械復制對人的感覺、記憶和下意識的侵占和控制,人為了保持住一點點自我的經驗內容,不得不日益從‘公共場所縮回到室內,把‘外部世界’還原為‘內部世界’。
既然居室在現代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與現代性問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首先,由于城市化的演進,造成公共領域的衰落,此時,城市居民的私人領域的意義不僅僅是排除工作之外能夠得到休憩的場所,更是面對社會生活客體并使之發現主體意義的另一維度的封閉空間。其次,資本主義生產的工作方式使得私人空間與時間日漸收縮 ,標準化與勞動工作的重復性,迫使勞動者尋求個人空間,由于工作種類的“角色化”對于個體性的壓抑,“自我真實”只能從內部發掘,因此,居室對于個人的意義是對外部保持一定的距離。此外“信息爆炸與網絡媒介”促使著人們交往行為的變遷,都市中的人們經常表現出來的對政治以及公共事物的無關心,反而傾向于寓于居室角落與更加廣闊的外部世界產生聯系,更多地更多地信息可以做到“足不出戶”就能攝取。“居室”其結構恰好類似于一種“航海式和封閉式”的空間,作為相對靜止的空間,而這種封閉靜止空間使得社會生活全景敞視的權力結構得到暫時的“停滯”,使得觀看方式發生了改變,從而決定了居室的隱蔽性對商業作為社會價值的反抗。這種隱蔽性恰好為向內尋找精神世界提供適當的場所,精神世界的幻影就在這里誕生:“在居室通過幻覺獲得滋養...居室的幻境就是整個世界。”
二、居室——作為時間藏匿者的休閑性
在討論居家生活的意義時,我認為最為核心的議題是到底是“工作有意義,才使得居家生活有意義?”,“還是工作的無意義,才使得居家生活有意義?”,對于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兩種說法是根據不同的角度來回答的“公民生活的真正框架越來越需要到辦公室和商業中心去尋找,而個人生活的虛擬框架則建構在私人居室里。比如,與購物中心里那些人聲鼎沸的餐館和影院不同,“住房”和“居家”狀況清楚地提示了都市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被動位置。這一被動不僅來自實際的情形:雇傭勞動強度的普遍增加,愈益強悍地制約他們的作息時間,這是一種身體政治,對于資本主義生產的重要性勞動力和生產能力,物質勞動與非物質勞動都使得今天的資本主義生產時長的增加。在這個體系當中 ,靈魂與身體進行權力的生產,暴露于居室之外的人成為 被“凝視”的對象,但是在居室這的相對封閉的空間中,人可以成為“凝視者”,且身體與靈魂可以得到釋放,這樣,主客體就在居室中發生了變化。
居室的時間性是非常弱的。消磨時間這個“滋養”是非常具有“虛無性”的,比如《小說的興起》正是由于資產階級生產的便利性使得婦女擁有更多的閱讀時間。在《小說的興起》中,作為女性的閱讀“由于經濟的重大變化,女性的閑暇時間大量增加已經成為可能...日益增多的女性閑暇與經濟專業化的發展之間的聯系...使她們擺脫了做這些事情的必要。
三、歸屬感的構建
可以這么來概括“居家”的主要涵義:一是都市的,公寓、轎車、“中產”式的消費能力和趣味,追隨時尚的休閑和娛樂習性,諸如此類;二是非公共的,不僅遠離公共政治,也盡量屏蔽對工作場所的勞資關系的感受的干擾;三是以積極消費為媒介的,把新物件買回家,生活才有新鮮感;四是空間上是擴散的,去購物中心吃喝玩樂等,都是“居家”的一部分。這樣的“居家”正日益普遍地充當今日中國人孜孜奮斗的終極目標。“家”的概念作為“神話”的意義在資本主義社會被無限放大,在中國,這個“家”的文化意義通常被轉化成為一個經濟問題,即“住房問題”,這是一種具有文化指涉的空間政治。比如紗簾在居室布置中的作用,使得光的方向發生了變化,也就使得凝視的權力關系發生了變化。其次,在居室中的行為方式以及觀看方式也是通過 “屏幕窺視”的方式得以實現。在以矩形的微視域范圍在觀察世界,能夠獲得更為主動的“主體”感受經驗......
現代社會意義上的居室與中國更為傳統的“家”的形象區別是非常大的:例如巴金的《家》中所描述的那種“庭院式”的住宅與網絡小說以及偵探小說中故事情節所展開的“公寓式”住宅形成鮮明的對比,現代社會中的居所更為封閉與個人化。
【1】[德]瓦爾特·本雅明,劉北成譯,《巴黎,19世紀的首都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