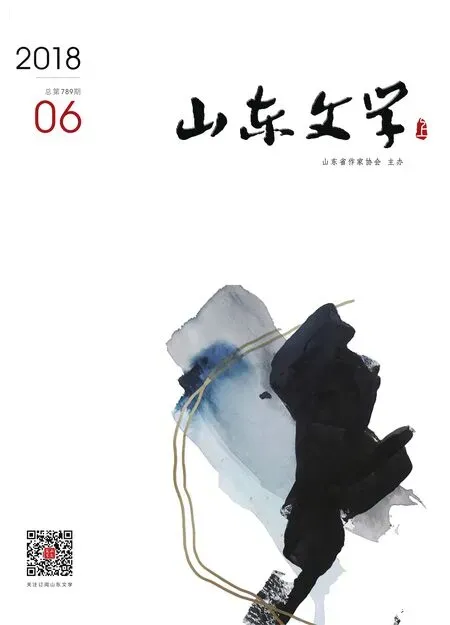網絡時代兒童文學的生存與發展
董國超
新舊世紀交替之際,兩部重要的兒童學著作面世,一部是美國著名媒體文化研究家尼爾·波茲曼的《童年的消逝》(1982年),另一部是英國學者大衛·帕金翰的《童年之死》(2000年)。兩部著作所關注的都是大眾傳媒對童年生活的影響。波茲曼在著作結尾,分析了童年被發現、童年文化的衰落、道德組織保護童年生態的能力、新媒體是否具備保護童年生態的潛能、家庭和學校對于保護童年所發揮的作用等問題后,得出童年必定會被大眾傳媒所“淹沒”的悲觀結論。但是,也有令人欣慰的事情,波茲曼認為,會有極個別的社會成員,他們作為家長,可以通過“限制子女暴露在媒介前的時間”和“仔細監督子女接觸的媒介的內容”,來“幫助他們的孩子擁有一個童年,而且同時是在創造某種知識精英”。波茲曼稱之為“寺院效應”(the Monastery Effect)。在稍后問世的學術著作《童年之死》中,帕金翰盡管在開篇就提到《童年的消逝》,表現出對波茲曼的極大尊重,但是對“寺院效應”帕金翰并不認可,他認為:“我們再也不能讓兒童回到童年的秘密花園里了,或者我們能夠找到那把魔幻鑰匙將他們永遠關閉在花園里。兒童溜入了廣闊的成人世界——一個充滿了危險與機會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電子媒體正在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我們希望能夠保護兒童免于接觸這樣世界的年代是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必須有勇氣準備讓他們來對付這個世界,來理解這個世界,并且按照自身的特點積極地參與這個世界。”
波茲曼和帕金翰所處的還是“前網絡”和網絡初始階段,近10年來網絡的發展出乎人們的預料,網絡對童年的影響比波茲曼和帕金翰所提到的以電視為主體的大眾傳媒,究竟會大到多少倍,恐怕現在還沒有人會說得準。但是,兩位學者提出的問題,仍然具有現實意義,我們還要嚴肅認真地思考這些問題:童年是否真的會消逝?如果童年消逝,兒童文學如何找到立身之地?畢竟“兒童研究是兒童文學研究的前提,是建立兒童文學理論大廈的基石”(朱自強)。
當下國內的兒童文學研究者開始給予更大的理論熱情關注網絡對兒童文學的影響,我們能夠在報刊雜志上讀到《新媒介時代的兒童文學生產與傳播》(胡麗娜)、《網絡媒體時代兒童文學發展的問題及對策分析》(許諾晨)、《網絡兒童文學的正負文化價值透視》(侯穎)等研究論文,以及研究網絡時代兒童文學應對措施的學術專著(《童年再現與兒童文學重構》譚旭東)等。在這些學術論文和著作中,我們可以歸納出兩個主要的學術觀點:其一,網絡文化對追求詩意、追求完美的兒童文學產生了嚴重沖擊,其平面化、碎片化、商業化已經導致兒童文學本質的扭曲,網絡文化中暴力、色情、低俗等惡劣因素,甚至已經污染了兒童文學的藝術空間,毒害了兒童的心靈。因此,兒童文學需要“重構”與“突圍”。其二,網絡文化盡管存在弊端,但它豐富了兒童文學的表現手段,擴大了兒童文學的影響,“網絡兒童文學”是值得理論家認真研究的新領域。
把這兩個觀點與波茲曼和帕金翰著作的中心論點加以比較,不難發現,當下兒童文學理論家所持的第一個學術觀點,比較接近波茲曼的看法,其理論旨趣為,兒童文學面對網絡文化的沖擊,應該堅持操守,維護傳統,在泥沙俱下的網絡文化氛圍中,營造出一個具有超越性的、“寺院”特質的兒童文學純凈世界;第二個觀點類似于帕金翰的主張,論者認為兒童文學作家不能、也不應該自我封閉,要勇于在新的文化環境中探索,利用網絡文化提供的新的表現元素,“按照自身的特點積極地參與”具有時代特點的兒童文學審美世界的建構。概而言之,兒童文學作家是在“寺院”內營造純美,還是走出“寺院”到塵世中冒險,是兩種觀點的主要區別之處。
守在“寺院”內也好,走到“寺院”外也罷,兒童文學還是兒童文學,在這一點上,持不同看法的雙方其實是高度一致的。那么,問題來了,在網絡時代兒童文學還是原來那個“兒童文學”嗎?如果兒童文學的本質特征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再簡單地談“堅守”或“冒險”,是不是太表象化了呢?
關于兒童文學本質特征是否發生變化,答案應該是明確而肯定的。
我們發現,近10年來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網絡空間的迅速擴張,正在廣泛而深刻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一部智能手機,幾乎可以解決所有的生活問題,以前我們必須在商場、書店、學校做的事情,現在都可以在虛擬的網絡空間中完成。網絡中的文字所包含的信息量,遠比文學提供的要多得多,譬如文學藝術中的主打門類小說,其傳奇性和紀實性,與網絡所蘊含的大量新聞信息相比,就顯得相形見絀,只剩下了令傳媒讀者陌生的敘事技巧。人們閱讀傳統的紙質敘事文學作品的時間越來越少,而閱讀手機微信的時間卻越來越多。以往在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文學,正在被邊緣化。
與文學整體的邊緣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作為整體文學一部分的兒童文學事業卻在快速發展。上個世紀90年代之前,全國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家專業兒童文學出版社,現在專業兒童文學出版社已有28家,而且幾乎所有省級和計劃單列城市出版社都有專門出版童書的少兒出版中心,兒童讀物成為出版社的主要盈利手段。表面上看,兒童文學出版業的火熱與整體文學的冷落形成對比,但是本質地講,作為文學分支的兒童文學也存在邊緣化現象,不過兒童文學的邊緣化,表現為兒童文學更加明顯、更加徹底地商業化、非文學化,是一種“藝術性質的邊緣化”罷了。盡管中國的兒童文學已經取得了斬獲國際安徒生兒童文學大獎的輝煌成績,但是,從整體上看,兒童文學已不再是純粹的文學活動,它日益融入到兒童教育之中,成為包羅萬象的“童書”之一種,與家庭教育、學校教學、社會教育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更被納入到全然功利性、徹頭徹尾實用主義的兒童經濟產業鏈之中。
這就是當下兒童文學在網絡文化背景下的生存狀況。在這種生存狀況中,兒童文學的本質特征已經發生了變化,忽視這種變化,泛泛地談什么兒童文學應對網絡文化的對策,或是前景展望,我們認為很可能會是隔靴搔癢。
對已經變化了的兒童文學本質內涵如何界定,并非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我們不想做形而上的理論研判和推導,而是采用現象學的本質“懸置”方法,具體談一談網絡時代兒童文學發展可能采取的策略。
一、拋棄精英意識,與通俗文學聯姻
中國的兒童文學是一門年輕的藝術形式,發生于五四時期,到現在也不過百年的歷史。而在這百年的歷史中,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兒童文學被認為是“小兒科”,不被文學研究者所重視。就以高校的文學專業課程設置來說,在上個世紀90年代之前,全國中文專業開設兒童文學課程的學校寥寥無幾。90年代以后,隨著朱自強、方衛平、王泉根、曹文軒、梅子涵等一批兒童文學理論家逐漸成為中堅力量,中國的兒童文學理論研究才在高校中越來越推廣普及開來。
可能是由于這樣的學術背景吧,中國的兒童文學作家和理論家普遍存在著精英情結,總是希望以一種“純文學”的姿態,讓文學界對兒童文學給予足夠的重視。如果把兒童文學歸入到通俗文學之中,可能會讓有些兒童文學業內人士覺得是對兒童文學的貶低。其實在歐美學者的理論視野中,兒童文學就被視為通俗文學(見英國學者約翰·斯道雷《文化理倫與通俗文化導論》)。而且正如前面談到的那樣,兒童文學已然成為兒童經濟、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此時還要再堅守“精英”的陣地,其實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把兒童文學定位為通俗文學,并不意味著對其藝術性質的貶低,恐怕沒人否認J.K.羅琳的《哈利·波特》是通俗文學,但這并不影響羅琳獲得國際安徒生兒童文學獎。作為通俗文學的兒童文學,要求作家要更有意識地關注讀者(不僅僅是兒童讀者)的閱讀需求,更加緊密地配合市場運作,創作出更加貼近兒童讀者和社會公眾日常生活的文學作品。
二、觀念更新,豐富兒童文學的表現手段
很多學者都已注意到,網絡時代是一個“讀圖”的時代,智能手機使每人都有機會嘗試以往專業攝影師所做的工作,“有圖有真相”是網絡敘事的一個顯著特點。兒童文學完全可以、而且已經實現了文字符號與圖像符號的融會貫通。“圖畫書”(繪本)近來在圖書市場的熱銷,就是這種融會貫通的明證。
圖畫書不僅適合兒童閱讀,同時也被很多成人所喜愛,圖畫書的思想內容既可以做兒童文學的解讀,也可以做現代、后現代視野中的通俗文學解讀。比如美國著名圖畫書作者莫里斯·桑達克的經典作品《野獸國》,作為兒童文學我們讀到的是幻想、游戲以及童心童趣;而澳大利亞著名兒童文學理論家克萊爾·布萊德福德卻把它視為通俗文學文本,并在其中發現了往昔海外殖民冒險的后殖民意識(賽義德的后殖民理論),以及具有叛逆特征的狂歡精神(巴赫金狂歡理論)。
通俗文化中的主要藝術門類影視藝術,也與兒童文學發生了密切的聯系。羅琳的《哈利·波特》在全球影響如此之大,與通俗文化的大本營好萊塢的電影制作不無關系。電視改編、各種兒童文學網站的推介,也對普及兒童文學知識、擴大兒童文學影響發揮了和正在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回歸人類童年,復活神話精神
兒童文學是陪伴個體生命童年期的藝術,神話是人類童年期的藝術,二者具有同質同構的特征,在網絡時代兒童文學復活神話精神,是兒童文學可以采取的策略之一。
神話具有兩個最鮮明的特征:幻想性和生命意識,這兩點在神話中水乳交融,是神話具有永恒魅力的重要原因。“幻想文學”(Fantasy)作為一種兒童文學的藝術形式,20世紀90年代初,才從日本兒童文學界翻譯、借鑒過來,現在這種新的兒童文學藝術樣式,已經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世紀交替之際,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還出版過中國兒童文學作家創作的“大幻想”叢書。幾乎與此同時,《哈利·波特》在全球的熱銷,更促進了幻想文學的發展。近十幾年,幻想文學成為中國兒童文學創作的重要一翼,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是,當下很多幻想文學作品還缺乏深度,甚至一味的幻想而流于淺薄與荒誕。兒童文學應該借鑒神話創作的經驗,在幻想中感悟人生、感悟生命的真諦。神話是民族文化的根,在飛速發展的網絡時代,引導讀者領悟本民族的文化傳統,感受生命的真諦,既是兒童文學的神圣使命,也是其不斷發展的動力源之一。
四、關注家庭、關注親情,以溫暖擁抱童年
網絡空間為人們的社交活動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使遠在千里之外的兩個社會成員,能夠即時地、面對面地交談。但是,網絡畢竟是虛擬的,一塊屏幕隔離了生命個體有溫度的親近,過度依賴網絡,反而會使朋友和親人之間產生疏離感。尤其是對未成年人,過度沉迷于網絡之中,會引發很多社會問題。
在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中,兒童文學應該以更大的熱情關注家庭、關注親情。倡導“溫暖”的兒童文學主題。所謂“溫暖”也即親情與友情,這是維系家庭和社會的情感紐帶,是我們這個社會最應該提倡的倫理主題。
表現“溫暖”是兒童文學最擅長、最具恒久性的主題,在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中,我們感悟最多的莫過于溫暖。當下兒童文學作家,應該細心觀察兒童生活,為他們創作有感情溫度的作品。兒童文學作家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要有為下一代提供精品精神食糧的抱負。到目前為止,唯一一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兒童文學作品是《尼爾斯騎鵝旅行記》,作品中的淘氣男孩尼爾斯,在騎鵝旅行中感受到瑞典國土自然風光的美麗,了解了民族的歷史和神話傳說,歷險經歷也使尼爾斯從小淘氣,長成為一個勤勞、溫柔、善良、樂于助人的好孩子。這部作品是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根據瑞典教育部的要求,作為一部學校地理教育讀物而寫的,正是這樣一部“命題作文”式的兒童文學作品,卻成就了一部兒童文學經典。原因何在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作家的責任感,以及作品中溫暖的倫理主題。
在結束本文之前,讓我們再回到開頭波茲曼和帕金翰所提出的問題:童年消逝或童年之死。從生理意義上說,童年永遠不會消逝;從文化意義上講,童年已經和正在發生著本質性的變化,這種變化究竟會對兒童、對兒童文學產生怎樣的影響,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但是從目前來看,網絡文化為兒童文學提供了更多機遇,有抱負的兒童文學作家應該抓住機遇,堅定地站在孩子身邊,與他們一起成長,迎接時代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