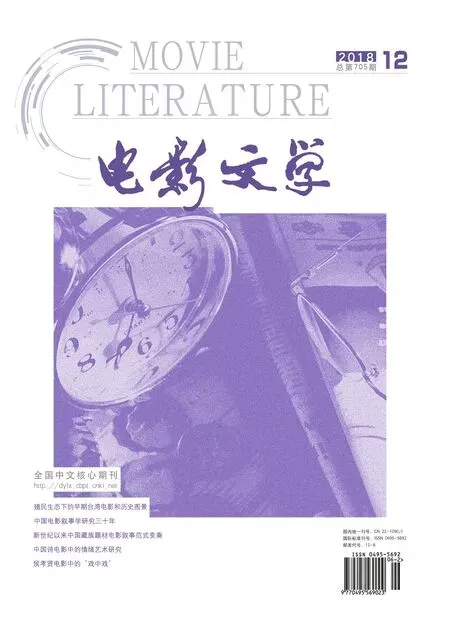《荒野獵人》的精神生態主題探析
徐 杰
(齊齊哈爾大學 公共外語教研部,黑龍江 齊齊哈爾 161006)
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里多執導的《荒野獵人》(The
Revenant
,2015),根據邁克爾·彭克的長篇小說《還魂者》改編而成。電影在給觀眾展示了主人公休·格拉斯所面臨的生存困境時,也暴露出了格拉斯及周圍人并不健全的精神世界。這也正是《荒野獵人》不可被忽視的藝術價值。正如著名學者歐文·拉茲洛所指出的:“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人類最大的局限不在外部,而在內部。不是地球的有限,而是人類意志和悟性的局限,阻礙著我們向更好的未來進化。”只有從精神生態的角度解讀《荒野獵人》,才能對電影想表達的生態觀有較為完整的認識。一、生態批評下的《荒野獵人》
在當今世界的經濟以及全球化進程不斷發展的同時,人類也開始面臨著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氣候異常等問題,并且在人一度的無視之下,這類生態問題還有愈演愈烈之勢。人類也開始逐漸意識到,地球是人類目前賴以生存的、無可替代的家園,人類有必要挽回生態危機深重的局面。藝術領域內的生態批評也就應運而生。如《瓦爾登湖》《白鯨》等文學作品都被納入生態批評的領域之中。這類作品的作者和批評者都倡導著一種人類和諧甚至詩意地在大自然中的生存方式。
《荒野獵人》也是一部理應在生態批評的角度下得到解讀的電影。電影與《魯濱孫漂流記》有著一定的類似之處,主人公陷落于荒野絕境之中,失去了人類工業文明的庇護,此時人類不得不與自然相處,二者的關系空前密切。如主人公皮草獵人休·格拉斯因為遭受母熊的撕咬而身負重傷,他為了生存不得不直接生吃活魚以及動物的肉和內臟。為了逃避人類的追殺,格拉斯不得不跳入冰冷的激流中求生。而在極度寒冷之際,格拉斯掏空了身邊被摔死的馬的內臟,然后裸體鉆進馬肚子里取暖等。而作為主人公同類的人類對自然的摧殘和戕害則顯然是對人類自己的戕害。如果將思索的范圍繼續擴大,人們則不難發現,電影的背景是19世紀初,美國剛剛獨立后的窘困局面,而在美國獨立前后,美國先賢,乃至法國人、西班牙人等殖民者,甚至包括作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都對北美大陸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傷害。在電影故事發生的時期,也正是美國和法國圍繞路易斯安那購地案對北美大陸展開爭奪的時期,在美國不斷擴展疆域,為人民爭奪更明朗廣闊的生存空間的同時,必然會影響西部的生態環境。
而《荒野獵人》與《魯濱孫漂流記》有所不同的是,電影有一條非常明確的復仇線索。先是格拉斯的兒子霍克被貪圖格拉斯財產的約翰·菲茨杰拉德當著格拉斯的面殺死,隨后格拉斯本人在身負重傷、奄奄一息的情況下被菲茨杰拉德拋棄,獨自在冰天雪地中等死。而在經歷了九死一生的磨難后,格拉斯不僅活了過來,還最終在一場戰斗后復仇成功。在這段恩怨之中,不同人的精神生態被展現出來,其中就不乏精神生態被異化、污染者。在生態批評的概念中,生態災難是多方面的,它不僅包括了自然生態危機,也包括了人和社會的沖突帶來的社會生態危機,以及人和自我以及他人相處時暴露出來的精神生態危機。正如魯樞元在《生態批評的空間》指出的,生態學共有三種:“以相對獨立的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生態學’,以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生態學’,以人的內在情感生活與精神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精神生態學’。”而這三者之間往往是互相滲透、彼此影響的關系。
二、《荒野獵人》中的精神生態危機
作品中精神生態方面的危機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讀:首先是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帶來的自私心態。電影中的白人在面對印第安人時主要有三種態度:一種以格拉斯為代表,格拉斯能平等地看待與自己種族不同的印第安人,他不僅娶了印第安女子,還在自己要奪走法國人的馬匹逃命之際,不顧自己的安危營救了被法國人凌辱的蘇族人的女兒珀瓦卡,而懷抱這種理念的人是極少數的。也正是這種相對較為理想的精神生態使得格拉斯沒有在喪妻喪子后蛻變為一個狂熱陰暗的復仇主義者。第二類人則秉承與原住民共存的態度,只是還會對原住民擁有一定的優越感,這一類人以電影中出現的白人軍官為代表,他們通過和印第安人做馬匹生意來盈利,但鄙視印第安人的野蠻。與格拉斯共事的皮毛經營者也可歸入此類,他們采集、銷售皮毛,掌握火器、馬匹以及皮毛硝制技術,但生存狀態有如野人,且離不開當地人做向導。這一類人也是有可能與原住民發生沖突的。如珀瓦卡的父親就曾在做交易時對白人怒吼道:“你跟我談榮譽?不,是你們偷走了我的一切!一切!土地!牲畜!兩個白人潛入我們的村莊,搶走了我的女兒,珀瓦卡。我用這些皮子和你換馬是為了找回我女兒。我現在就帶走你的馬,你阻止我試試!”第三類人則以菲茨杰拉德為代表,他們趨之若鶩地來到北美,不擇手段地染指原住民的土地,砍伐森林、獵殺野獸以獲取皮草,是為了掠奪當地的資源倒賣以大發橫財,在他們的貪欲下,蘇族人的生存受到威脅而奮起反抗,達科他戰爭、紅云戰爭、黑山戰爭等戰役相繼爆發,北美大地血流成河。對于這一類人來說,原住民是與北美當地的其他動物沒有區別的,人類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獵殺這種“非人類”。而對于身為白人的同胞,菲茨杰拉德依然會因為自私而加害。他主動要求護送重傷在身的格拉斯完全是因為金錢的誘惑,而為了貪圖省事,他又想殺死格拉斯,在被霍克發現后,菲茨杰拉德索性先殺死霍克。而對于默認了他的惡行,但良心未泯的同伴吉姆·布里杰,菲茨杰拉德也產生了加害的念頭。博愛的心態對于他們來說是缺失的。
其次,理性缺席導致的暴力行徑。在《荒野獵人》中,曾有一個鹿尼族男人救了格拉斯一命,兩人分手后這位鹿尼族好人還要前往南方尋找自己的族人,這種對族群的靠攏是為了獲得更多的生存機會,因為蘇族人屠戮了他的家人。然而就在向著生存遷徙的半路上,鹿尼族好人被路過的法國人殺死,他的尸體被吊在樹上,還被法國人掛了一個牌子,上面用法語寫道:“我們都是野蠻人。”這一場景對格拉斯的打擊是深重的。與之類似的還有法國人對珀瓦卡的擄掠。毫無疑問,法國殖民者此時才是野蠻人,印第安人在弱肉強食的交鋒中付出了生命和尊嚴的代價。與單純的逐利行為不同,法國人對這位鹿尼族男人的殺戮是沒有必要的。這種瘋狂行徑意味著他們已經為恐懼等心理所支配,陷入嚴重的病態中。因此,在電影中,菲茨杰拉德和法國殖民者也就成為邪惡、偏執的代表,他們失去了對大自然和原住民的敬畏、尊敬之情,也必將為自己的自私付出代價。
三、從精神危機中走出
在對人面臨的精神生態危機進行揭露后,伊納里多又為人們從精神危機中走出來尋找了途徑。
首先,宗教信仰是伊納里多給予精神異變者開出的一劑處方。《荒野獵人》從表面上來看講述的是一個關于人在絕境下生存和復仇的故事,其表層文本并不復雜,但是其深層的精神內涵卻是極為深刻的。和近年來同樣是主人公獨自求生的電影,即李安執導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
,2012)類似,《荒野獵人》也討論了人的信仰問題,只是包裹這一思索的多了一層快意恩仇的外殼。在電影中,格拉斯的經歷多次與宗教有關。在愛子死后,格拉斯眼前出現了幻覺,他擁抱一棵樹,認為自己是在擁抱兒子,他看見了教堂、教堂里的鐘和圣象,并且這些意象都極為破敗荒蕪。這里象征的是格拉斯的信仰即將坍塌,他必須將自己從“文明人”變為不擇手段生存下去的“獸”。占據格拉斯精神的是血腥復仇而不是崇尚寬恕、愛和希望的宗教。而格拉斯的兒子是白人和原住民的混血兒,格拉斯作為白人承擔了家破人亡的代價,這是電影對白人殖民者的一種委婉的批判。
在電影的最后,格拉斯在和菲茨杰拉德的對決中占據了上風,此時他只要再補一刀就能為兒子報仇,并且在誤會河對岸的波尼族人將要不利于自己的時候,盡快在死之前手刃仇敵才是符合常理的。然而格拉斯卻選擇了將復仇的決定權交到上帝的手中,將費茨杰拉德推入水中,讓對岸的波尼族人選擇是不是要殺他,結果對方干凈利落地殺死了菲茨杰拉德。這里格拉斯所踐行的正是《圣經》的羅馬書十二章十九節中的:“讓主審判,如其所言‘伸冤在我,我必報應’。”這是因為在和大自然進行了一系列的搏斗之后,格拉斯意識到了人的力量的弱小。他曾經幾乎崩潰的信仰隨著對復仇重負的放下而回歸到他的內心之中,他本人從“獸”變為“人”,而作為人的格拉斯也得到了主的“報應”,他所以為的虎視眈眈的波尼族人并不想殺他,相反,將他視為拯救了珀瓦卡的恩人。
其次,伊納里多強調對大自然的“復魅”。人的精神生態危機與人類錯誤的生態觀是密不可分的,基于此,人類有必要重新審視自己對大自然的態度。因此,伊納里多希望人類能回歸到自然之中,實現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伊納里多對大自然進行“復魅”的過程并不是通過凸顯大自然的神力實現的,這將削弱電影的真實性,伊納里多選擇了削弱人類的力量,讓人類以一種更接近于動物的方式存活在大自然中。其中語言的失去便是一個重要的象征。語言是人類文明的體現,它能表達復雜的思維,幫助人類進行龐大的改造大自然的集體活動。語言越精妙,人類的進化程度也就越高。而當人類失去了語言時,人也就被極大地弱化和原始化了,這一點在阿方索·卡隆的《地心引力》(Gravity
,2013)中也有所體現。而與《地心引力》女主人公無人交流的狀況還略有不同的是,格拉斯的失語還源自被熊抓傷了喉嚨導致聲帶受損。因此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失去了用語言求救、求助的能力,而只能喘息和呻吟。這種失語狀態直接指向的就是格拉斯此刻對動物本性的回歸,他和動物一樣此時最優先考慮的就是生存。在動物面臨危險時,它們往往也只能發出單音節喊叫和喘息。另外,這也是對電影開頭,格拉斯的妻子念的“只要一息尚存,就一定要戰斗下去。只有這樣才能活下去,活下去”的一種呼應。為了突出人在大自然中的這種氣息,伊納里多采用了一個逐漸模糊的畫面,此時觀眾看到的格拉斯仿佛走在太陽穿透不了的濃密云層之中,而在聽覺上,格拉斯的呼吸則隨著天地的寂靜語法清晰。人仿佛進入了一種天地初創的境界當中,徹底成為大自然的一部分。伊納里多在一個艱苦卓絕的復仇故事中表達了希望人類的精神生態能夠實現和諧的愿望。對于依然面臨三重生態危機,甚至出現精神異變的當代人來說,《荒野獵人》以格拉斯從險情不斷到否極泰來的經歷提醒著人們實現精神生活的平衡,克服“精神污染”的必要和迫切。